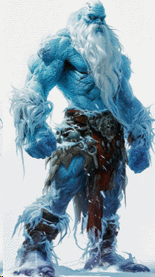§ 山中傳奇(3)/精怪
§ 山中傳奇(3)/精怪
§ 晨起
公元前520年春天的一個清晨,到山上隱修八年了,最近修為總是停頓不前,今天畢達哥拉斯決定到高山帶接受大自然的挑戰,希望可以突破到新的境界。
奧林匹斯山南麓的積雪開始退卻,融水在山石間鑿出銀亮的細脈,匯集為溪流,在清晨的寂靜中發出類似琴弦的泠泠聲響。
此刻他踏著未消的殘雪走向慣常冥想的岩石時,注意到去年枯死的百里香叢下,已鑽出灰綠色的新芽。
風從色薩利平原方向吹來,帶來潮濕土壤與朽木菌絲混合的氣味。
低處山坡的橡樹林仍保持著冬日的深褐色輪廓,但若凝神細看,枝梢已膨起無數細微的、紫紅色的芽苞。
岩羊的新鮮蹄印在濕潤的腐殖土上格外清晰,蜿蜒指向更高處的草甸——
那裡終年籠罩的雲霧正被晨光染成蜂蜜般的色澤。
這時他停下腳步,目光掠過逐漸甦醒的山體。
遠處斯塔吉拉港的方向,海平面像一塊微微彎曲的青銅板,反射著初春特有的清冷天光。
三隻鷹隼正在上升氣流中畫出幾何軌跡——
正是他近日在沙地上推演過的三角形變體。
當山風忽然轉強,搖動整片杉樹林時,林濤聲與溪流聲在某個瞬間形成了精確的八度共鳴。
畢達哥拉斯拉緊羊毛披肩,袖口已被融雪浸出深色水痕。
他想起昨夜星圖中金星與木星的交匯角度,與山腳下牧羊人笛聲的振動頻率存在著某種隱秘的對應。
在這個萬物重新計算生長節奏的季節裡,奧林匹斯山的每一塊岩石、每一道融雪逕流,似乎都在向他驗證那個真理——
宇宙的秩序終將以數的形式顯現,就像這些剛剛掙脫霜凍的嫩芽,終將按照神聖比例舒展成葉。
§ 暴風與雷電
畢達哥拉斯提起真氣往高山帶奔馳而上,地面殘雪尚未完全融化,裸露出灰白色的岩層,地衣、苔蘚偶而點綴著路邊的矮灌木,這裡已是人煙罕至。
到了海拔2400公尺,最先迎接他的,是風。
不是山腳那種帶著松脂氣味的流動,而是被地形擠壓後的狂烈之息。
風從山脊背後撲來,像無形的獸,先推擠他的肩,再扯動他的衣襟,最後直擊胸腹。
畢達哥拉斯停下腳步,雙足分開,腳趾嵌入碎石之間。
他不急著前行,而是讓呼吸沉入丹腹——
不是為了馴服風,而是讓自身不被拔走。
真炁在體內緩緩流轉,貼著筋骨行走,如水貼石。
他感覺到風在試探他的空隙,只要一絲動搖,身體便會被整個奪走。
風越來越強,聲音像裂帛,又像遠古的號角。
他彎下身,讓背脊順著風勢傾斜,意志卻不退。
這不是對抗,而是承受——承受到極限,卻不崩解。
風過之處,他的肌肉顫抖,血液加速,身體在痛楚中學會站立。
隨後,天空改變了顏色。
雲層在高空迅速聚攏,光線被壓低,像被一隻巨手覆住。
第一道雷聲並非炸裂,而是低沉地滾過山腹,震得岩壁回鳴。
畢達哥拉斯抬頭,沒有尋找庇護之所。
他知道,雷電來時,退避已無意義。
閃電撕開天空的瞬間,世界被照得雪白。
雷聲隨即落下,直擊耳膜與內臟,彷彿要把人的存在從山中震出。
他跪在岩地上,雙手按地,讓震動沿著手臂與脊椎流入大地。
先天真炁在體內被逼到極致,如熱流般衝擊五臟六腑,既是防禦,也是暴露——
肉體的脆弱在雷光中無所遁形。
第二道雷更近。
空氣帶著焦灼的氣味,頭髮因靜電微微立起。
他感到恐懼,真實而赤裸,卻沒有逃離。
意志此刻不再是命令,而是一種不動——
不動於恐懼,不動於生死的假設。
雷電落下,他的喉嚨發出低吼,不是祈禱,而是對存在本身的回應。
當風勢漸歇,雷聲遠去,山重歸低沉的靜默。
畢達哥拉斯仍伏在地上,渾身濕冷,四肢酸痛。
他沒有勝利的感覺,也沒有被征服的屈辱。
只有一個清晰的事實:
人的肉體可以承受,意志可以不退,而自然始終不需回應人的任何期望。
在奧林匹斯的高山帶,他以自身作為容器,讓風與雷通過。
當痛苦慢慢退去,真炁從丹田升起,漸漸運走全身,畢達哥拉斯呼嘯一聲,飛身到一塊岩石平台上,盤坐閉目。
§ 山怪
雷後的空氣仍帶著焦鐵與雪水的氣味。
畢達哥拉斯盤坐於岩石平台,真炁緩緩歸入丹田,山風已不再試探,只在遠處低吟。
入定到了黃昏,突然感覺山動了起來,不是聲音,也不是震動,而是重量改變了。
山沒有動。 是某個比山更古老的存在,正在移動。
他睜開眼。
遠方霧氣之中,一道輪廓從岩脊後站起來。
那不是巨石,也不是樹影,而是一具直立的形體,肩寬如門,背脊覆著歲月風化的裂紋。
它一步踏下,岩層低鳴,卻沒有崩落,彷彿山本就預留了它的行走之處。
巨人停在風線之外。
這巨人身高約4佩克斯( 肘尺,1肘≈50公分,4肘=200公分),下身著獸皮,白色長鬚垂落至胸前,肌肉如未經雕鑿的花崗岩,雙眼泛著深綠色的光,像苔蘚在古墓中自行生長。
巨人先開口,聲音低沉,卻沒有敵意:
「你不必起身。能在雷後仍坐得住的凡人,不多。」
畢達哥拉斯沒有答禮,只平靜回應:
「我未呼喚你。但你來了。」
巨人微微點頭,像是在承認一個正確的觀察。
「我是奧林匹斯之脊的看守者,在眾神尚未立名之前,便被留在此處。」
他停了一瞬,又補上一句,語氣更像陳述,而非自誇:
「凡人稱我為『負嶺者.塔勒歐斯』(Talaios, Bearer of the Ridge)。」
畢達哥拉斯抬眼直視那雙綠光之瞳。
「那你所守的,是山?還是神?」
巨人低聲笑了,那笑聲像遠處冰層的摩擦。
「我守的不是山。山會自己存在。我守的,是界線。」
他抬起一隻手,指向雲仍未散盡的天穹。
「雷與風不是試煉,而是通告。
當『雲上之王、持霆者』(The Cloud-Bearer, Lord of Thunder)在此顯現時,不是為了懲罰你,而是要知道——」
巨人的目光再次落回畢達哥拉斯身上:「你會不會退。」
短暫的沉默。
畢達哥拉斯回答得很慢:
「我退過。在人群之中。在這裡,我只能站,或倒下。」
巨人注視他許久,彷彿在測量什麼不屬於肉體的尺度。
終於,他點頭。
「那你還未越界。但記住,凡人能承受神的顯現,不代表有資格替神發言。」
說完這句話,巨人轉身,重新走入雲霧與岩脊之間。
山風再次流動,彷彿什麼從未來過。
只留下畢達哥拉斯一人,與一個清楚得近乎殘酷的認知:
他被允許存在於此,但從未被承諾任何答案。
§ 狐狸精
回到隱居處天色已暗,畢達哥拉斯躺在床上沉沉睡去。
夜色在洞穴裡變得溫軟,火光像困倦的心跳,一下、一下。
畢達哥拉斯沉在半夢之中,身體還記得白日雷霆的重量,肌肉鬆弛,卻仍殘留熱度。
他感到有什麼鑽進懷裡。 不是突兀的靠近,而是熟門熟路的貼上。
雪狐把鼻尖塞進他的頸窩,白毛蹭得人發癢。
他迷迷糊糊地伸手,指尖陷進那團柔軟裡,還沒來得及分辨,霧氣已悄悄升起。
那團溫軟在他胸前化開,變成絕美少女的身形,整個人黏在他身上,像不肯離開的夢。
她貼得很緊。 腿蜷著、手臂環著,連呼吸都要分一半給他。
肌膚微涼,卻在貼合中迅速暖起來。
她抬頭看他,眼睛亮得不像夜裡的生物,唇角帶著小小的笑,彷彿得意自己被允許這樣靠近。
她用額頭蹭他的下巴,又低下頭,在他胸口輕輕磨蹭,動作黏人又不安分。
「醒著嗎?」她低聲問,語氣卻像早已知道答案。
他還來不及回應,她已經貼上來,整個人壓得更近,柔軟的重量讓他忍不住吸氣。
她似乎很滿意他的反應,笑了一聲,聲音貼著他的喉嚨滑過。
她的手不規矩地游移,時而收緊,時而放鬆,像在試探哪裡最讓人心軟。
她慢慢坐到他身上,卻沒有急切,只是黏著不放。
她靠前一點,又退回來一點,像貓找最舒服的位置。
每一次貼合都讓他更清醒,也更沉溺。
她低頭靠在他肩上,小聲地喘著,呼吸亂得毫不掩飾,彷彿這份親密本身就值得被炫耀。
火光映著她的輪廓起伏,她的長髮垂下來,遮住他的視線。
她抬手把頭髮撥開,又故意貼近他的臉,鼻尖幾乎相碰,卻只笑著磨蹭,不肯真正離開。
那份拖延本身,就讓情慾在胸口越積越滿。
當節奏終於慢慢一致,她整個人伏下來,抱得更緊,像怕一鬆手就會消失。
世界只剩下溫度、貼合與彼此的心跳。
那一刻沒有急促,只有長久的黏連,像雪在夜裡不斷落下,覆蓋所有邊界。
黎明前,她終於安靜下來,在他懷裡蜷成一團。
霧氣輕輕升起,又輕輕散去。
雪狐回到洞穴角落,尾巴蓋住臉,只留下一點滿足的鼻息。
畢達哥拉斯醒來時,懷裡是空的。
但那份被緊緊抱過的感覺,仍黏在身上,怎麼也甩不掉。
限會員,要發表迴響,請先登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