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東遊記(14)/塔克西拉(Taxila)(7)生命的出口
§ 東遊記(14)/塔克西拉(Taxila)(7)生命的出口
生命之無奈在於走過方知來時路…齊克果。
513BC 塔克希拉的沙門泛指一整群離家修行者、苦行者、哲學外道。
他們是反婆羅門、重實修、不一定相信神、以解脫為目標的遊行修行者。
分為(1)苦行沙門 (2)禪定沙門 (3)理性外道沙門 (4)邊緣激進派
§ 沙門
印度河支流在午後顯得寬緩。
水面不像愛琴海那樣閃耀,而是呈現一種帶泥的黯光,彷彿將群山、天空與時間一併攪拌後,默默流走。
畢達哥拉斯站在河岸的礫石上,鞋已脫下,腳踝浸在水中。
長途跋涉使他的身體仍然強健,但神經尚未適應這片土地的節律——這裡的空氣不急不躁,卻帶著一種持續的壓力,像呼吸本身在要求被重新學習。
他正觀察水流的速度與寬度,心中下意識估算著比例:
石子滾動的頻率、浪紋的間距、聲音回返的延遲。
就在這時,他注意到河對岸的樹蔭下,有一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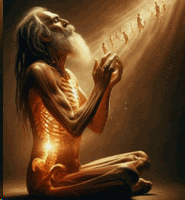
那人坐得極低,幾乎貼著地面。
不像埃及的祭司,也不像巴比倫的智者。
他沒有任何標誌自己身分的器物。沒有法杖,沒有符號,甚至沒有固定的衣著。
只是一塊舊布披在肩上,露出曬黑而乾瘦的手臂。
最引人注目的不是外表,而是呼吸。
畢達哥拉斯停下腳步。
那人的胸腔起伏極慢,每一次吸氣都深得異常,彷彿不是在汲取空氣,而是在將整條河的節律納入體內。
他沒有發聲,沒有誦咒,甚至沒有閉眼。
只是坐著,看著水。
畢達哥拉斯並未立刻上前。
他知道,在異地,倉促接近往往被視為一種侵入。
他站在原地,讓自己的呼吸自然放慢,試圖與那陌生的節律對齊。
過了不知多久,那人開口了。
「你不是來取水的。」 聲音低沉而平直,像石頭落入水中,沒有多餘的波紋。
畢達哥拉斯微微一愣,隨即點頭。
「我在觀察。」
那人轉過頭來,第一次正眼看他。
那雙眼睛沒有評判,也沒有好奇,只是確認了一個事實。
「觀察水,」他說,「還是觀察自己?」
這句話讓畢達哥拉斯沉默了一瞬。
在埃及,他學會測量;在巴比倫,他學會計算;但沒有人這樣直接地,把問題拋回給他本身。
「一開始是水。」畢達哥拉斯如實回答,「但我發現,最後總是回到自己。」
那人輕輕點頭,像是聽見了一個並不意外的答案。
「那你已經在修行了,」他說,「只是你還在為它取名字。」
畢達哥拉斯走近幾步,在對岸坐下,與那人隔著一段不遠不近的距離。
「你是沙門嗎?」他問。
那人沒有立刻回答。
「如果你是問,」他慢慢說,「我是否屬於某個教派,那答案是否定的。」
「如果你是問,我是否離開了原本的生活,為了尋找不會腐壞的東西——那你可以這樣稱呼我。」
畢達哥拉斯注意到,他在說「不會腐壞」時,手指輕觸了一下自己的胸口,而不是指向天空。
「你們相信神嗎?」畢達哥拉斯問。
那人露出一個幾乎不可察覺的笑意。
「有些人相信。有些人懷疑。而我,只關心一件事——」
他抬起手,指向河流。 「當你停止干擾它,它是否仍然流動。」
畢達哥拉斯順著他的手看去,水依舊前行,繞過石頭,吞沒落葉,不因任何觀看而改變。
那一刻,他突然明白了某件事—— 這裡的修行,不是為了控制世界,而是為了不再強迫世界符合自己的形式。
夕陽開始下沉,河面泛起銅色的光。
兩人沒有再說話,只是並肩坐著,各自呼吸。
畢達哥拉斯第一次感到,數與比例之外,還有另一種秩序—— 不需要被證明,卻同樣嚴密。
而這條河,正無聲地教導著它。
§ 技藝師
離開河岸後,畢達哥拉斯沿著通往城內的小路前行。
日色尚亮,風裡開始混入煙火與金屬的氣味——這是城市的呼吸,與河岸截然不同。
不久,他聽見節律分明的聲音。
鏗。鏗。
不是自然的回響,而是刻意維持的節拍。

他轉過彎,看見一間半開的作坊。
屋前立著幾根木樁,上面纏著測量用的繩索;地上攤著尚未完成的銅件與石模。火爐旁,一名中年男子正俯身敲擊,一錘一停,毫不多餘。
那人抬頭,看見畢達哥拉斯,沒有驚訝,只是快速掃了一眼他的裝束與步伐。
「外來者?」技藝師問。
「是。」畢達哥拉斯回答。
技藝師點了點頭,繼續手上的工作,語氣平穩得像是在回答一個早已預期的問題。
「站在那裡別動。這裡有熱銅。」
畢達哥拉斯依言停下。
他注意到,那人的每一次敲擊,都不是憑感覺,而是對照旁邊木板上刻好的比例線。
銅片在火光下逐漸成形,沒有多餘的修飾,卻精準得令人安心。
「你做的是什麼?」他問。
「水門的齒輪。」 技藝師終於停下來,把工具放好,擦了擦手。
「城北灌溉用的。若差一分,整個季節的水都會亂。」
畢達哥拉斯的眼神亮了一瞬。
「你用的是比例?」
「當然。」 技藝師皺了皺眉,像是在看一個問題太顯而易見的人。
「不用比例,靠祈禱嗎?」 他語氣不輕蔑,卻帶著一種對不精確的天然不信任。
畢達哥拉斯笑了笑。 「你的手很穩。」
「不是手穩,」技藝師糾正他,「是方法穩。」
「手會老,眼會花,但方法如果對,徒弟也能接得上。」
他轉身,指向作坊內部——那裡掛著幾件成品,每一件都標註了尺寸與用途。
「我靠這個吃飯,養家,交稅。城裡的人信我,是因為我做出來的東西會工作。」
這句話說得很重。
畢達哥拉斯忽然想起河岸邊那位沙門—— 沒有工具,沒有成品,甚至沒有留下任何痕跡。
「你怎麼看那些離群索居、不事生產的人?」他問。
技藝師沉默了一下,並非不耐煩,而是在思考怎麼回答。
「他們有他們的位置。但如果全城都是那樣的人,水門會壞,橋會塌,孩子會渴。」
他抬起頭,看著畢達哥拉斯,眼神直接而清楚。
「世界不是靠看懂運轉的,」他說,「是靠被正確地使用。」
這句話讓畢達哥拉斯一時無言。
他忽然意識到沙門追求的是不干擾世界;而技藝師,正好相反,他一生的榮耀,在於精準地介入世界,而不讓它崩壞。
夕陽的光落在銅件上,發出沉穩而實在的光澤。
畢達哥拉斯向技藝師致意,準備離開。
走出作坊時,他心中第一次出現了一個尚未能回答的問題:
如果真理只存在於遠離世界之處,那麼這些讓世界得以運轉的手,又是在為什麼服務?
他帶著這個重量,踏上回家的路。
§ 另一種人生
傍晚的市集仍未散去。 牲畜的氣味、香料的甜膩、汗水與塵土混雜在一起,人聲此起彼落,像一張不斷收緊又放鬆的網。
畢達哥拉斯行走其中,腳步放慢——不是因為疲倦,而是因為他開始意識到,這座城市並非只有思想與技藝,還有更赤裸的生存。
就在一處布棚與酒肆交界的陰影裡,他看見了她。

她並不年輕,也不刻意張揚。
衣料並不華貴,卻刻意露出鎖骨與手腕,像是精準地計算過,露出多少才不會顯得廉價。
她站得很穩,沒有倚靠任何人,目光在來往的男人之間游移,既不追逐,也不退縮。
那是一種被反覆使用後學會的冷靜。
她注意到了畢達哥拉斯的視線,卻沒有立刻露出笑容。
只是微微抬了抬下巴,像是在確認: 你是來買東西的,還是來看人的?
畢達哥拉斯停下腳步,並非出於慾望,而是一種不知該如何移開目光的遲疑。
「外地人。」她先開口,語氣平淡,「你不熟這裡。」
「看得出來?」他問。 「看得出來你還在看人,」她回答,「本地人只看價錢。」
這句話沒有怨懟,也沒有自嘲,只是事實。
畢達哥拉斯一時不知道該如何接話。
他忽然意識到,自己曾與沙門談「不干擾世界」,與技藝師談「正確使用世界」,而眼前這個女人,卻是被世界使用的人之一。
「你在等什麼?」他問。
她看了他一眼,眼神短暫而清晰。
「等有人需要忘記自己一會兒。也等今晚能不能換到明天的食物。」 她說得太直接了,反而讓人無法移開視線。
「你選這樣的生活?」畢達哥拉斯低聲問。
她輕輕笑了一下,那笑容轉瞬即逝。
「你們總是這樣問。沒有人問水為什麼往低處流。」
她指了指市集另一頭,幾個孩子正圍著攤販爭搶掉落的果皮。
「我年輕時,也想過別的路。但有些路,一旦錯過,就只剩下一條可以走得下去的。」
畢達哥拉斯感到胸口一緊。
他忽然明白,這不是墮落,也不是放縱,而是一種被迫持續的交易,用身體換取時間,用尊嚴換取明日。
「那你的價值是什麼?」他幾乎是無意識地問出口。
女人看著他,這一次的目光比剛才深得多。
「我活著。」她說。「這本身就有價值,只是你們不習慣用這種方式計算。」
市集的燈火一盞盞亮起,人群再次湧動。
她向前走了一步,又停下,像是出於某種尚未完全泯滅的禮貌。
「你不是我的客人,」她說,「但你看見了我,這已經比很多人多。」
說完,她轉身融入人流,沒有留下名字,也沒有留下任何承諾。
畢達哥拉斯站在原地良久。
他忽然意識到—— 沙門選擇離開世界,技藝師選擇塑造世界,而她,與無數像她一樣的人,只是在世界夾縫中努力不被壓碎。
那一刻,他第一次清楚地感到:
生命的價值,並不總是來自於選擇的高貴,而往往來自於在無選擇中,仍然活下去。
夜色降臨,他默默離開市集。
這一次,腳步比來時更沉。
後記:
完成這個章節我心情突然沉重起來,我想到上一章節前的吉他曲Estas Tonne的[Eemental /Who am I?]
限會員,要發表迴響,請先登入
- 1樓. onhappy2026/01/24 20:26多謝 希波克拉底 於 2026/01/25 06:42回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