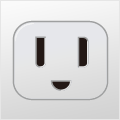旅遊日期:2017/1/14
坐落在壬生川通與松原通的長圓寺,距離我前一次的住宿並不是非常遠,但很神奇的,直到回到台灣才發現這件事情。或許是地圖的錯導所致,一直以為長圓寺距離西本願寺有一段距離,那時住在西本願寺附近的我並沒有特別想要前往長圓寺的念頭。
直到第二次來尋訪京都時,居住的地方又離長圓寺有些距離時,才真正去接觸這裡。

那一天天空飄著雪,據說那天是京都少見的大雪,時陰時雪的天氣讓人難免煩躁起來,雪沾在衣服上,似乎拍都拍不掉,一抬頭,距離長圓寺似乎還有一點距離。
卻也那麼巧的,抵達長圓寺時,雪又停了下來,放下雨傘,才終於調整完心境,緩步走入長圓寺。

長圓寺完全無人,像是別處仙境一般,當步入長圓寺時只感到寧靜,別無其他感覺,佛足石靜靜的在本堂旁邊屹立,像是歡迎著所有瞻禮者來到此處,對佛足石虔誠合掌。不過可惜的是,本堂的阿彌陀三尊前有著玻璃隔閡,讓人無法看清阿彌陀三尊的樣貌,只能看到隱約的輪廓。而延命山的匾額,像是說明這裡經歷的歷史,如此悠久且漫長。

對著本堂的阿彌陀三尊合十,並逐漸往一旁的觀音堂前進。觀音堂門扉微微敞開,像是歡迎信眾瞻禮他的面容,一手持蓮的聖觀音菩薩,雖然身軀已然灰暗,但是隱約間似乎能見到如滿月的笑容,逐漸在圓光之中開展。右手垂下,表達給予所有的救濟與願望,如此平和慈悲,依偎在觀音身邊,似乎就能解決所有痛苦似的。
或許這也是這尊觀音像雕刻的緣故所致。

傳說在一条天皇的時候天花流行,當時天花致死率非常非常的高,因此很多時候就只能求助於高僧祝禱。當時是擔任大納言的藤原親衡求助惠心僧都。惠心僧都親手雕了尊聖觀音菩薩,進行二十一日的法會後,天花居然就停止了。
以流行病學者的角度來說,或許是每個人都有天花抗體,因此就有集體免疫力而不怕天花了。但若沒有如此安定人心的法會,難道天花就會無聲無息的停止嗎?或許在某方面來說,因為民眾的恐慌而更加嚴重,可能導致無法收拾。又或者,惠心僧都的慈悲與觀音本願,的確抑制了天花病毒的傳播,真的讓天花逐漸息絕了。
因此這尊觀音菩薩,就被專責護佑孩子遠離疾病的觀音。

不過在應仁之亂時,這尊觀音菩薩曾經下落不明,直到後來清嚴大和尚來到比叡山再度與觀音相遇,再因為在京都任職的板倉勝重的護持,因此興建本堂迎請慈覺大師所雕刻的彌陀三尊、在觀音堂內供養此尊聖觀音。
瞻仰此尊觀音,或許今日傳染病等疾病已經不怎麼會威脅到我們,但這尊觀音仍然在此,像是接受所有人的苦痛一般,靜靜地聽聞納受。那是否是惠心僧都的本心所顯現的觀音樣貌呢?看著笑容如滿月的觀音,似乎能看見迎抗天花的孩童,仍如此慈悲微笑,來勉勵對抗惡疫的孩童。
參拜觀音後前往納經所,按了電鈴,納經所的執事阿姨迎面而來,盛了熱茶給我,恰巧因為大雪的關係,我需要一些熱茶,因此我對他表達深切的感謝。
雙手奉上納經帳,請求執事阿姨為我納經,她隨口問了我從哪裡來,並看到我理了光頭,問我是不是坊主(僧人)呢?

問我從哪裡來,我仍能回答得出來,但是問我是否為僧人這點,我有點困惑了。論起來從受戒開始才能正式稱自己為比丘僧,至今仍非比丘僧的我,是不是能自稱為僧人、還是只是一般的居士呢?且理光頭是為了往後受戒不被家人所驚訝而先理光頭,但這樣是不是會造成其他人困惑?以及如果我自稱為僧人,我是否擁有僧人應該俱足的威儀呢?
這個問題如同問難,我不知如何用最簡單的說法說明這麼複雜的情況,雖有受持十善但未受持比丘戒,是否能稱呼自己是僧侶?我以行者的修行方式是否可以說自己是僧人嗎?
想了想,也只能如此回應:「還沒成為僧人(Not Yet)」了。
執事阿姨笑了笑,似乎有點理解我的複雜情況,還我納經帳同時順手塞了幾顆糖,才送我離開。
把糖含在嘴中,糖果甜甜的,像是勉勵我繼續向前,不要為現實所繫絆的趣求佛門。
只是這問難,至今我仍繼續琢磨,自己是否夠有資格,稱自己為僧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