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層「斬殺線」,頂層「蘿莉島」。
最近發生的一系列大跌眼鏡的事件,讓中國人對美利堅「燈塔國」的濾鏡碎了一地。這一波艾普斯坦文件的大規模解密更是告訴了我們,蘿莉島絕對不是「有錢人玩得很花」這麼簡單。
富豪沉迷於玩樂或許是人性中幽暗的底色,但當一個富豪能讓諾貝爾獎得主、美國總統、中情局(CIA)局長和英國王室成員圍著他轉,心甘情願地登上那架「洛麗塔快線」時,這就不再是人性,而是政治。

當我們像剝洋蔥一樣剝開這一層層被精心包裹的所謂「真相」,你會發現,讓你辣眼睛的絕不僅是加勒比海島嶼上的荒淫,而是一個讓人背脊發涼、足以改寫西方政治學教科書的事實:那個以為自己生活在一個以契約、法治和選舉為基礎的西方社會,早已在科技與資本的加持下,全速回到了中世紀。
只不過,這次的領主不穿笨重的板甲,而是身著定制西裝;他們不騎高頭大馬,而是坐灣流 G650 公務機;他們收的不再是實體的糧食稅,而是你的數據租金。歡迎來到「美利堅新封建主義聯合酋長國」。
在這裡,法律是平民的枷鎖,卻是精英的廁紙;在這裡,選舉是一場精心編排的真人秀。在這裡,公共權力早已私有化,國家機關成了門麵點綴。真正的決策,是在那些裝了針孔攝像頭的豪宅裡、在不留航跡的私人航線上完成的。這就是「黑箱政治」的最高境界:台上演《紙牌屋》,台下玩《甄嬛傳》,背後搞《金瓶梅》。
●艾普斯坦不是皮條客,他是系統的「路由器」
以前我們總以為艾普斯坦是個有著變態嗜好的暴發戶,是一個權貴之中的皮條客。但隨著300萬頁文件的曝光,這種認知便被推翻了。艾普斯坦不是系統的bug,他是系統的feature(功能)。
社會學有個理論叫「結構洞」。意思是,社會被分成一個個互不通氣的小圈子,誰能佔據這些圈子中間的空白地帶,充當橋樑,誰就掌握了最大的權力。艾普斯坦就是那個佔據了「終極結構洞」的人。
看他的朋友圈:
左手牽著「教士階層」: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MIT)的頂級學者,諾貝爾獎得主。這幫人有腦子、有名望,但缺錢,且有著巨大的智力虛榮心。
右手挽著「寡頭階層」:維克斯納(維多利亞的秘密老闆)、黑石集團的大佬。這幫人有錢,但缺道德背書,需要洗白。
兜裡揣著「政客階層」:克林頓、安德魯王子。這幫人有權,但缺享樂的渠道和私密的交易空間。
影子藏著「情報階層」:以色列摩薩德、美國CIA。這幫人需要黑料,需要控制權。
艾普斯坦正是這些不同階層需求和利益的整合者。
如果說艾普斯坦是那個拿著線的操偶師,那麼誰是木偶?
2025年解密的文件裡,最讓我大呼「好傢伙」的,是美屬維爾京群島的國會代表普拉斯基特。場景是這樣的:
2019年,眾議院舉行聽證會,審問川普的前律師邁克爾·科恩。這是一場全國直播的嚴肅政治活動,旨在捍衛法律尊嚴。但解密短信顯示,艾普斯坦當時正坐在電視機前,一邊看直播,一邊給正在提問的普拉斯基特發短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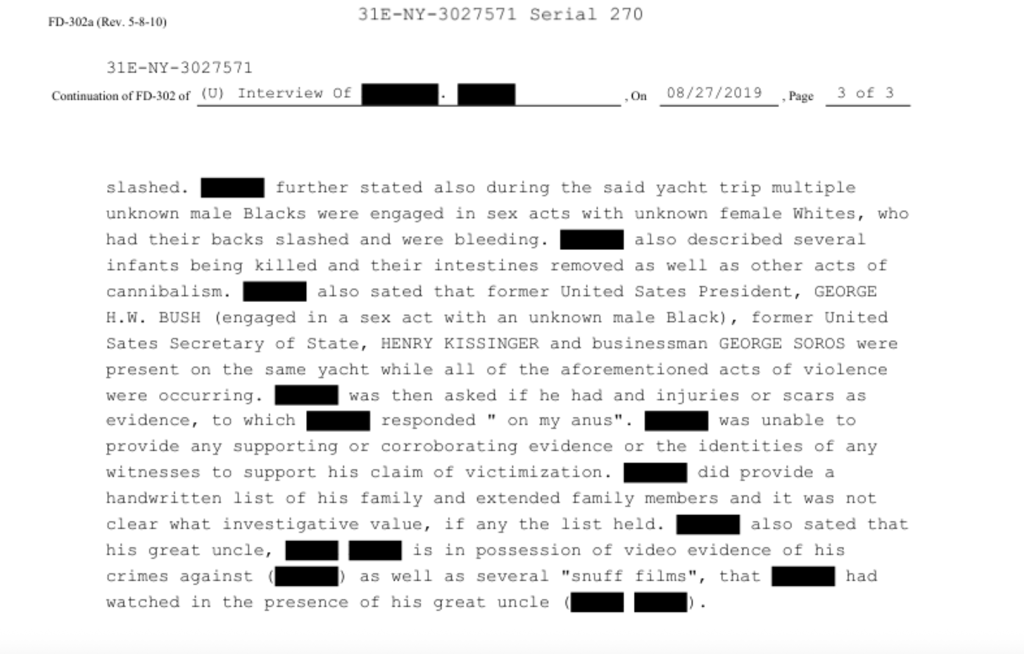
艾普斯坦:「問他關於那個誰的事……」
普拉斯基特:「好的老闆,馬上問。」
艾普斯坦:「幹得漂亮。」
這哪裡是國會議員?這分明是開了藍牙耳機的「代練」啊!這一幕簡直是「代議制民主」的墳墓。你以為你選出的議員代表的是你的意志?不,她的聲帶、她的大腦、她的投票權,早就被遠程托管了。
再看看斯蒂芬·班農。這位老哥平時一副「反建制鬥士」「為藍領工人代言」的糙漢形象。結果呢?文件顯示他和艾普斯坦在私下裡都是「如膠似漆」。兩人在討論什麼?不是怎麼幫工人漲工資,而是如何密謀地緣政治:怎麼在北約(NATO)安插自己人?怎麼利用香港局勢搞事情?怎麼在梵蒂岡把教皇方濟各搞下去?當然,還有班農數次向艾普斯坦借用他那架私人飛機。
兩個沒有任何外交官身份的美國平民(其中一個還是性犯罪者),在曼哈頓的豪宅裡,像切蛋糕一樣通過私人關係切割世界局勢。公共權力被徹底私有化了。 國家的外交部、國防部成了擺設,真正的決策流淌在私人飛機的香檳和加密聊天軟件的字節裡。

●教士階層的偽善與道德特許
在這個新封建體系中,維持系統穩定的關鍵在於一場盛大的「化妝舞會」。教士階層(學者、媒體、非政府組織)與寡頭聯手,通過一種心理學機制——「道德特許」,為殘酷的掠奪披上了進步的外衣。
所謂「道德特許」,心理學研究表明,當一個人做了一件被認為是「好」的事後,往往會允許自己在隨後的行為中放縱。這幫精英覺得:「哎呀,我天天呼籲環保,我支持跨性別廁所,我為黑人下跪,我簡直是聖人啊!既然我積了這麼多陰德,那我私底下坐坐私人飛機,去島上享受一下未成年少女的服務,這點『小惡』也是可以被原諒的吧?」
這套邏輯的核心在於「將一部分人開除人籍」。他們一邊寫著「人生來平等」的漂亮話,一邊像討論牲口一樣討論如何虐待供他們享樂的女孩。這種「日常化的邪惡」是西方精英社會的系統性病態。
麻省理工學院(MIT)媒體實驗室與艾普斯坦的關係,是教士階層墮落的活體標本。其前主任伊藤穰一明知艾普斯坦是性犯罪者,但在內部郵件中將其稱為「伏地魔」,並專門設計了一套複雜的匿名捐贈系統來收他的黑錢。

為什麼?因為教士階層雖然有名望,但他們不是資本擁有者,且極度渴望金錢來維持其「改變世界」的幻覺。艾普斯坦深諳此道。他把自己包裝成「科學慈善家」,給哈佛捐錢搞「進化動力學」,給MIT捐錢搞「反學科研究」。
對於那些自命不凡的知識分子來說,沒有什麼比「一個億萬富翁不僅給我錢,還居然聽得懂(或者裝作聽得懂)我的理論」更讓他們高潮的了。領主出錢,教士出賣靈魂和名譽,雙方在學術的殿堂裡完成了權力的苟合。在支票本面前,所有的學術獨立都像清晨的薄霧一樣稀薄。
如果說伊藤穰一隻是個技術官僚,那麼喬姆斯基的涉入則是對全球左翼精神圖騰的毀滅性打擊。
這位標榜反帝、反資本主義的宗師,不僅與艾普斯坦有頻繁的金錢往來,更在私人郵件中展現出令人咋舌的親密。最諷刺的是,在2019年艾普斯坦再次面臨風暴時,喬姆斯基竟然在郵件中支招:「最好的辦法就是無視它」。
在那一刻,道德的防線比紙還薄。這也證明了在新封建秩序中,只要你是「教士階層」的頂層,你就自認為擁有了免受世俗道德審判的特權。當反叛者變成了領主的座上賓,所謂的抗爭就成了一場昂貴的行為藝術。
摩根大通天天在網站上掛綵虹旗,搞多元化宣傳。背地裡呢?他們的合規部門明知艾普斯坦在洗錢、在販運人口,卻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因為他是「大客戶」。
只要你在推特上發一句「黑命貴」,你彷彿就獲得了一張免死金牌。你可以繼續壓搾員工、逃避稅收。這是一種極其高明的障眼法,它將大眾的注意力從階級矛盾(經濟掠奪)轉移到了身份政治(文化戰爭)上。領主們在城堡裡開香檳,農奴們在下面為了「衛生間該分幾種顏色」打得頭破血流。
在這個新封建秩序裡,法律不是正義的化身,而是精英的看門狗。艾普斯坦在罪行纍纍的情況下,無數次通過操縱司法逍遙法外。
來看看「暗金」是怎麼運作的。以前買通政客還得偷偷摸摸塞信封,現在?那是合法的藝術。通過慈善基金會等非營利組織,億萬富翁可以捐無限多的錢,還不用披露名字。比如那個倫納德·裡奧,一個人就操盤了16億美元的黑金網絡。他幹嘛?他像買菜一樣「買」法官。美國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大法官,好幾個都是通過他的網絡篩選、輸送上去的。這意味著,即便你在選舉中贏了,我也能通過控制法院,把你的法律給廢了。
再看看「旋轉門」。美國FDA(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局長,卸任後100%都去了醫藥公司當高管——你在位時幫我批藥,退休後我給你百萬年薪。最新調查發現,FDA甚至明目張膽地告訴離職員工:「雖然有法律規定你們不能立刻遊說老東家,但你們可以在幕後指揮啊!」這哪是監管機構?這是醫藥公司的崗前培訓班。
這就是為什麼美國的醫療費那麼貴,為什麼基建那麼爛,為什麼軍費那麼高。因為每一項政策的背後,都有一根管子直接插在國庫上,通向某個領主的私人泳池。
●「美國夢」的破滅與階層的種姓化
如果不理解「新封建主義」這個概念,你就看不懂今天的美國,甚至看不懂今天的世界。
社會學家科特金在《新封建主義的來臨》中敏銳地指出,我們所熟知的那個通過努力工作就能實現階級躍遷的「美國夢」已經腦死亡。資本主義曾經引以為傲的社會流動性已經終結,社會正在不可逆地退回一種等級森嚴的結構。在這個2.0版本的封建社會裡,人類不再被劃分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而是被清晰地鎖定在四個種姓之中。
第一等級:「寡頭領主」。
這就是貝佐斯、馬斯克、祖克伯、蓋茨這群人。在中世紀,領主擁有土地和武裝;在今天,領主擁有「雲封地」。你想賣東西?得交亞馬遜的過路費。你想說話?得交推特(X)的認證費。你想社交?得給Facebook交數據稅。他們不僅有錢,他們甚至擁有了超越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主權」。在他們眼裡,白宮不過是其全球業務的「華盛頓辦事處」。
第二等級:「教士階層」。
這群人由大學教授、媒體大 V、非營利組織高管、好萊塢明星組成。在中世紀,教士負責解釋《聖經》,定義善惡,以此維護領主的統治合法性。今天,教士階層負責解釋「政治正確」。他們發明各種複雜的詞彙——DEI(多元、公平、包容)、黑命貴、碳足跡——建立起一道凡人無法逾越的「意識形態護城河」。他們的生態位非常尷尬且虛偽:他們需要寡頭的錢來維持體面,寡頭需要教士的嘴來購買道德贖罪券。
第三等級:正在消亡的「自耕農」。
這曾經是美國引以為傲的中產階級、小企業主。這幫人最慘,他們是舊民主制度的基石,現在正被寡頭(壟斷資本)和教士(環保/監管法規)聯手絞殺。他們正在快速破產,滑向底層,成為川普民粹主義的基本盤。
第四等級:龐大的「新農奴」。
那就是大多數普通人。沒有資產,買不起房,背著永遠還不完的學貸和信用卡債。他們不擁有生產資料,只是在算法的指揮下送外賣、開網約車,或者在格子間裡敲代碼。他們提供的不是糧食,而是數據。他們在刷短視頻時的每一次點擊,都是在給領主收割的莊稼施肥。在這個系統裡,貧窮是一種罪,而服從是一種生理本能。
艾普斯坦之所以能構建起如此龐大的網絡,除了依托於科特金描述的新種姓社會,更是因為他依附於一個正在癌變的經濟體。希臘前財長亞尼斯·瓦魯法基斯曾提出一個驚世駭俗的論斷:資本主義已經死了,因為它已經變異成了「技術封建主義」。
在傳統資本主義中,資本家賺取的是「利潤」,這需要他在市場上通過競爭、創新和銷售商品來獲得。但在今天,科技巨頭賺取的不再是利潤,而是「地租」——具體來說是「雲端地租」。
當你進亞馬遜買東西,你以為那是自由市場?不,那是貝佐斯的「雲端莊園」。那些第三方賣家就是依附於領主的「附庸資本家」。最新的數據顯示,亞馬遜通過廣告費、物流費和佣金,從賣家每一美元的收入中抽取高達51%。這不是生意,這是徵稅。貝佐斯不需要改進產品,他只要點點鼠標,就能把你這個「附庸」的流量掐斷,讓你在商業上物理亞尼斯性死亡。
對於普通人來說,亞尼斯說得更直白:「雲端資本不僅剝離了我們的物質資產,還在剝離我們的精神資產。」普通人變成了「雲端農奴」,用免費的勞動(數據)供養著算法,而算法反過來控制我們的慾望和行為,將我們囚禁在信息繭房之中。在這種環境下,所謂的「選擇自由」不過是囚徒在監獄食堂裡挑選菜譜。
艾普斯坦正是這種「雲端領主」與舊世界權貴之間的潤滑劑。在這個體系裡,法律是平民的枷鎖,卻是精英的廁紙;主權不再屬於國家,而被馬斯克這樣的私人領主通過「星鏈」等基礎設施私有化——他甚至可以憑個人意志決定是否要在克里米亞開啟衛星服務,從而左右一場戰爭的走向 。
既然這幫精英已經控制了世界,為什麼現在美國政壇內部打得跟烏眼雞似的?圖爾欽的「歷史動力學」給出了最精準的預言:這是「精英過剩」導致的必然結果。圖爾欽指出,美國這幾十年來,「財富泵」全速運轉,將底層和中產的財富通過醫療、教育、金融泡沫源源不斷地抽向頂層。結果就產生了一個副作用——「精英過剩」。
簡單說就是:想當官的人太多,椅子太少。有錢人越來越多,受過高等教育、野心勃勃想要掌握權力的人(預備精英)成倍增加。但是,參議員只有100個,總統只有一個,哈佛終身教授就那麼幾個坑。坑少蘿蔔多,咋辦?內卷。
這幫精英不再團結,開始搞「魷魚遊戲」。像川普、班農這種被主流排擠的「反精英」,決定掀桌子,利用底層民眾(農奴)的憤怒去攻擊「深層政府」;而像希拉芯、拜登這樣的「建制派」,則利用司法、媒體和情報機構來清洗對手。
艾普斯坦就是在這場精英內戰中被祭旗的。只要大家都相安無事,他就是大家的好朋友;一旦精英開始互撕,他手裡掌握的那些黑料,就成了原子彈。所以他必須死,或者說,他必須閉嘴。在美利堅,能保守秘密的只有死人,或者變成死人的秘密。
最後,我們應該看到,艾普斯坦只是這個系統裡的小角色。真正的主角是馬斯克、彼得蒂爾那種真正的「寡頭領主」。我們必須審視「黑箱」權力的最高形態:不僅是控制機構,而是控制國家主權本身。
21世紀初,彼得·蒂爾與馬斯克等人一起創辦了支付軟件Paypal。從Paypal早期創業團隊走出的一群創業者和投資人最後成為了硅谷最具影響力的科技領袖,這群人被稱作「Paypal Mafia(Paypal黑手黨)」,他們在政治上大力支持川普陣營,深刻形塑了美國的政治與經濟格局。
2022年,當烏克蘭軍隊準備利用無人艇對克里米亞的俄羅斯艦隊發動突襲時,他們發現通信中斷了。這不是因為俄羅斯的干擾,而是因為馬斯克單方面拒絕激活「星鏈」服務。
這一事件的意義是深遠的:一個私人公民,基於個人的判斷,否決了一個主權國家盟友所支持的另一主權國家的軍事行動。在過去,戰爭權是國家主權的核心。但在技術封建時代,關鍵的基礎設施成為了私人領主的封地。美國國防部不得不像中世紀請求領主出兵的國王一樣,去和馬斯克談判。
在經濟領域,主權同樣在轉移。亞馬遜實際上向平台上的商業活動徵收了51%的重稅。這不僅僅是壟斷,這是私有政府的崛起。亞馬遜制定規則、裁決糾紛、徵收稅款,而沒有任何民主機制可以制衡它。實體經濟在「雲端地租」的壓搾下窒息,由此產生的通脹最終都轉嫁給了我們這些新農奴。我們以為自己在消費,其實是在履行作為農奴的納貢義務。
●看清黑箱,方能照見前路
這一波「艾普斯坦文件」的解密,對我們來說是一次深刻的歷史鏡鑒。它赤裸裸地展示了當資本權力由於缺乏約束而高度集中時,社會將如何不可避免地滑向黑暗的深淵。這不再是某種主義的勝負,而是人類文明形態的一次重大變異。我們要從中看清的,不是「美國藥丸」,而是「資本邏輯」與「技術暴政」結合後的恐怖圖景:
政治家族化:權力的流轉不再依賴選票,而是依賴血緣、姻親與秘密盟約。
國家空心化:公共服務被外包給領主,主權被切割成一個個數字采邑。
民眾原子化:我們被困在算法織就的絲繭裡,以為在表達自我,其實只是在生產領主需要的「原始數據」。
這是一個舊秩序正在崩塌、新秩序尚未確立的時代。圖爾欽所預言,這種財富泵無限運轉的系統是不穩定的。民粹主義的崛起、社會的劇烈撕裂,其實都是農奴們在長期壓抑後的原始吶喊——雖然醒來的姿勢不太優雅,甚至帶著破壞欲,但這確實是系統崩壞的前兆。
當這場化裝舞會的音樂最終停止,當所有的面具掉落,那個真實的、赤裸的權力世界將會展現在每一個人面前。我們要確保的是,無論外界如何變幻,我們始終能掌握那把開啟「黑箱」的鑰匙,不讓技術異化為枷鎖,不讓資本演變為領主。(作者為前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孔子學院教師、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博士)
(本文來源:觀察者網,授權中時新聞網刊登)
※ 以上言論不代表旺中媒體集團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