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選
Excerpt:夏多布里昂的《墓畔回憶錄》(中冊)之 [雷卡米耶夫人]
2025/11/16 04:46
瀏覽23
迴響0
推薦1
引用0
Excerpt:夏多布里昂的《墓畔回憶錄》(中冊)之 [雷卡米耶夫人]
……不過,如果說在永恆的忘川邊上,一切真實和夢幻都是枉然;在人生的盡頭,一切都是荒廢的時光。
(…mais si près de loubli éternel, vérités et songes sont également vains: au bout de la vie tout est jour perdu.)
——《墓畔回憶錄》.〈篇章二十八〉
繼續閱讀及分享夏多布里昂的《墓畔回憶錄》(中冊)。
進入到中冊的下半部,夏多布里昂終於開始寫到雷卡米耶夫人(Madame Récamier),這一位當時的社交名媛主辦林間修院(abbaye-aux-Bois)沙龍,並成為歐洲最知名以及最大的沙龍之一。往來的賓客除了政商名流,還包含拉馬丁、聖伯夫、巴爾扎克等當代文豪……(詳維基百科)
以下摘要分享。
書名:墓畔回憶錄(全三冊)
Mémoires d’outre-tombe
作者:夏多布里昂(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
譯者:程依榮、管筱明、王南
出版社:四川文藝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5/04
【Excerpt】
〈篇章二十八〉
[雷卡米耶夫人]
我們去羅馬使館赴任,去我晝思夜想的那個意大利。在接下去敘述之前,我應該提一提一位婦女。直到本回憶錄結尾,讀者都可以見到她:從羅馬到巴黎,在我和她之間將展開一段通信聯繫:因此,讀者應該知道我是在給一個什麼樣的女人寫信,我是在什麼時候,又是怎樣認識雷卡米耶夫人的。
在社會各個階層,雷卡米耶夫人都遇到一些在世界舞台上或多或少有些名氣的人物。大家都對她表示崇拜。她的美貌把她的理想生活與我們歷史的具體事實結合在一起:寧靜的光照著一幅暴風雨的畫面。
讓我們還是回到已逝的時代,借著我夕陽的餘暉,努力在天幕上描繪一幅肖像。我的黑夜臨近,不久就會在天上撒滿陰影。
一八〇〇年我回國後,《信使報》刊發了我一封信,引起德·斯塔爾夫人注意。當時我的名字還在流亡貴族的名單上;《阿達拉》使我走出了默默無聞的狀態。在德·封塔納先生請求下,巴茲奧西夫人(波拿巴的妹妹埃莉莎·波拿巴)替我申請並獲得批准,把我的名字從流亡貴族名單上一筆勾銷。經辦此事的便是德·斯塔爾夫人。我去向她致謝。我記不起是克里斯蒂安·德·拉穆尼瓦翁還是《科琳娜》的作者(德·斯塔爾夫人)把我介紹給雷卡米耶夫人的。她當時住在勃朗峰街她家的府邸裡。我剛從樹林裡出來,剛剛走出生活中的陰暗地帶,仍然很孤僻,勉強才敢抬眼注視一位身邊圍滿崇拜者的女人。
大約一個月以後,有一天早上,我去德·斯塔爾夫人家,她在梳妝台前接待我。她一邊由奧利韋小姐侍候著穿衣,一邊跟我說話,手指間還捏著一根小青樹枝。雷卡米耶夫人穿著一襲白袍,突然走進來,在一張藍綢沙發中間坐下。德·斯塔爾夫人仍然站著,正在談話的興頭上,就繼續滔滔不絕地說下去。我望著雷卡米耶夫人,勉強才答上幾句。我從未想到有這樣漂亮的人兒,我也從沒有這樣洩氣:我對她的仰慕變成了對自己的不滿。雷卡米耶夫人走出房間。我再見到她,是十二年以後的事了。
十二年!是什麼敵對力量這樣切割糟蹋我們的年華,諷刺地把它慷慨送給被稱為愛慕的冷漠,外號叫幸福的不幸!接下來,當年華最珍貴的部分凋零、消耗之後,它又嘲諷地把你帶回起點。而且,它是怎樣把你帶回來的呀?一些古怪念頭、一些討厭的幽靈、一些上當的落空的感覺折磨著你的頭腦,攔在你前面,阻礙你得到那本來還可以品嘗的幸福。你悶悶不樂地回來,內心充滿痛苦和遺憾,想起那純潔的年華,便為如此艱難的青春時期的過錯而懊悔。我遊歷羅馬、敘利亞,目睹帝國興亡,成為風雲人物,不再做沈默之人以後,回來時就是這樣一種心情。雷卡米耶夫人又幹了什麼事呢?她過的又是什麼樣的生活呢?
(Douze ans ! Quelle puissance ennemie coupe et gaspille ainsi nos jours, les prodigue ironiquement à toutes les indifférences appelées attachements, à toutes les misères surnommées félicités ! Puis par une autre dérision, quand elle en a flétri et dépensé la partie la plus précieuse, elle nous ramène au point du départ de nos courses. Et comment nous y ramène−t−elle ? Lesprit obsédé des idées étrangères, des fantômes importuns, des sentiments trompés ou incomplets dun monde qui ne nous a laissé rien dheureux. Ces idées, ces fantômes, ces sentiments sinterposent entre nous et le bonheur que nous pourrions encore goûter. Nous revenons le coeur souffrant de regrets, désolés de ces erreurs de jeunesse, si pénibles au souvenir dans la pudeur des années. Voilà comme je revins après être allé à Rome, en Syrie ; après avoir vu passer lEmpire, après être devenu lhomme du bruit, après avoir cessé dêtre lhomme du silence et de loubli, tel que je létais encore, quand je vis pour la première fois Madame Récamier. Quavait−elle fait ? Quelle avait été sa vie ?)
下面我將給你們敘說她的生活。她的日子過得既光輝燦爛,又默默無聞,其中大部分為我所不瞭解,因此我不得不求助於一些權威,它們雖與我的權威不同,卻是不可置疑的。首先,雷卡米耶夫人向我講述過她目睹的一些事情,並且給我寫過一些珍貴的書信。她將所見所聞,都寫了筆記,她不但允許我查閱,而且允許我引述,這是十分難得的。其次,德·斯塔爾夫人在已經印出來的通信集裡,邦雅曼·龔斯唐在他還是手稿的回憶文章裡,巴朗謝先生在我們共同的女性朋友的小傳裡,德·阿布朗泰公爵夫人和德·冉利夫人在她們的文章草稿中,都給我的敘述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我只是把那些美麗的姓名串接起來。若是哪個事件的環節斷了或者扯開了,就用我的敘述填補空白。
蒙田說,人類張開懷抱迎接未來的事物,而我卻有個怪毛病,張開懷擁抱過去的事物。尤其當人們回顧親愛的人早年的生活時,一切都是快樂:人們是在延長所愛的生命,是在把愛情擴展到原來並不瞭解現在回憶起來的日子,是在美化現在人過去的生活,是在給青春做補償。
一八三九年,於巴黎
[雷卡米耶夫人的童年]
在里昂我參觀過植物園。它就建在古圓形劇場的廢墟上,位於古荒漠修道院的花園裡。那座修道院現在已經倒塌了。羅訥河和薩奧納河就在腳下;遠處聳立著歐洲最高峰。那是意大利的第一個里程碑,它那白色的告示牌直插雲霄。雷卡米耶夫人曾被送進這家修道院,在一道柵門後面度過了童年。只有在舉行彌撒的日子柵門才向外面的教堂打開。那時,人們便可以在修道院的內部小教堂見到匍匐禱告的姑娘們。女修道院長的聖名瞻禮日就是修道院的主要節日;由女寄宿生中最漂亮的一個向院長致例行的祝賀:同伴們給她整戴好首飾,扎好辮子,戴上頭巾,披上面紗。這一切都是靜靜地做好的,因為揭開面紗的時刻是修道院裡所稱“鴉雀無聲”的時刻之一。接下來朱麗葉得到了當天的榮譽。她父母在巴黎安了家,便把孩子召回身邊。在雷卡米耶夫人寫的一些草稿中,我收集了這則筆記:
“姨媽來接我的前一天,有人把我領到院長嬤嬤的房間,接受她的祝福。第二天,我跨出修道院大門。大門打開讓我進去的情形我記不起來了。我滿臉淚水,和姨媽坐上一輛馬車去巴黎。
“我依依不捨地離開了一個那樣純潔,那樣平靜的年代,走進了動蕩不安的歲月。有時我像做一個朦朧而溫柔的夢,又想起那個時候的事,想起那裊裊的香煙,想起那沒完沒了的儀式,想起在花園裡的迎神遊行,想起那時唱的歌和那時的花。”
從一個虔誠的僻靜的地方出來的歲月,如今在另一處虔誠的清靜的地方休息,它們的清純與和諧沒有損失半分。
[雷卡米耶夫人的少年時期]
伏爾泰之後,最有頭腦的男人是邦雅曼·龔斯唐。他力圖使人們對雷卡米耶夫人的少年時期有所瞭解:他打算描繪出模特的輪廓,在她身上提取出一種並非與生俱來的優雅。
“在當代因為面孔、才智或者品性的優勢而出名的女人中間,”他寫道,“有一個我願意描繪。先是她的美貌讓人仰慕她,接下來她的靈魂讓人瞭解她。她的靈魂看上去比她的外貌還要美。社會風習給她提供了施展才智的辦法。她的才智並不在她的靈魂與容貌之下。
“才滿十三歲她就嫁了人。男人一心忙於大事,不能指導這個極為幼稚的孩子。於是在一個仍是一片混亂的國家裡,雷卡米耶夫人幾乎全靠自己來打理生活。
“同時代有許多婦女名滿歐洲。她們中的大部分都向時代進了貢,有些人的貢品是她們那毫無溫情可言的愛情,另一些人的貢品則是向相繼而來的暴政做有罪的屈服。
“人處在這種環境,不是被它腐蝕,便是被它敗壞。可是我描寫的這個女子,卻是光彩奪目、純潔無瑕地從這種環境出來了。首先童稚是她的一種保障,因為這個美妙作品的創造者使一切都變得對她有利,她住在一個由藝術裝點的僻靜處所,遠離塵世,學習詩歌與其他有趣的功課,把這些仍屬另一種年齡的樂趣當作自己的日常消遣。
“她有一些少年夥伴,也常常和她們一起玩一些鬧鬧嚷嚷的遊戲。她身材苗條,體態輕盈,每次跑步,總是跑在前面。她把眼睛蒙上布條。有朝一日,她將看穿所有人的靈魂。她的目光如今是那樣生動,那樣深邃,似乎在向我們揭示一些她本人也不清楚的秘密,但那時卻只閃爍出歡樂和頑皮的光芒。她那一頭秀髮每次散開來都要惹得我們心慌意亂。她那時把頭髮披落在白皙的肩膀上,當然這對任何人都沒有危險。她那稚氣的談話常常為長久的清脆的笑聲打斷;不過人們在那時就已經注意到她那敏銳捕捉笑料的觀察力,那尋找快樂卻從不傷人的調皮,尤其是那份優雅、單純和趣味純正的感覺。那是真正的天生高貴,其資格是烙在享有天賦的人身上。
“當時的上流社會與她的本性太不相容,以至於她只能偏愛隱居。當任何封閉的圈子都會招來懷疑時,把房子對所有人開放便是唯一可行的聚會辦法。各階層的人都來到這些房子,因為在這裡可以說話卻不招惹是非。可以見人卻不會受到連累;在這裡流腔痞調替代了風趣,亂七八糟換下了歡樂。但是在這裡從來見不到她的身影。在督政府大院裡,權力顯得既凶狠又親切,讓人既生出恐懼又免不了輕蔑。在這裡也見不到她的身影。
“然而雷卡米耶夫人間或也走出偏僻的居所,去劇院看戲,或者去公園走走。因此,在眾人常去的這些地方,她少有的幾次出頭露面成了真正的事件。這些大型聚會的其他目的都被人忘記了,每個人只是朝她經過的地方衝過去。幸運地給她領路的男子必須戰勝像障礙一樣攔在他面前的仰慕者。她的腳步時刻被擁擠著圍觀的人所阻延。她帶著兒童的快樂和少女的羞怯享受著這份成功。但那份莊重與優雅,在家裡使她超出其他年輕女友,在外面,則鎮住了衝動的人群。似乎她光是以自己的出場,就支配了座中的朋友和外頭的公眾。雷卡米耶夫人婚後頭幾年就是這樣過的:不是在偏僻的居所寫詩吟詩,玩遊戲,就是驚鴻一現地光彩奪目地在交際場所露一露面。”
……
[我再次見到雷卡米耶夫人——德·斯塔爾夫人之死]
我再次見到雷卡米耶夫人,是在法國名流感到痛苦的年代,德·斯塔爾夫人就是那個時期死的。《苔爾芬》的作者在百日王朝後回到巴黎時已有疾病纏身。我在她家和德·迪拉公爵夫人府上都見到過她。漸漸地她的身體每況愈下,不得不臥病在床。……
……
沒過幾天,德·斯塔爾夫人換了房子,請我去馬圖蘭新街她的新家吃晚飯。我去了。她不在客廳裡,甚至也不能出來吃飯。但她尚不知道大限已是如此逼近。我們入了席。我坐在雷卡米耶夫人旁邊。我有十二年沒有遇見她,就是那一回見到,也只是片刻之間的事。我沒有望她,她也不望我。席間兩人沒有說一句話。只是到了散席的時候,她才靦腆地跟我談了幾句德·斯塔爾夫人的病情。我稍稍偏過頭抬起眼睛。今天我擔心上了年紀的嘴巴會說出褻瀆一種感情的話。這種感情在我的記憶中保留了它的全部青春,而且隨著我日漸衰老,它的魅力也日益增大。我撇開晚年的日子,要發現那後面天國的幻影,要聽見深淵下方一個更幸福的地區的和諧聲音。
……
我常去城牆下街看望雷卡米耶夫人,後來她搬到昂儒街,我又常去那兒。人一旦與命運重新會合,就以為從不曾與它分離過:照畢達哥拉斯的說法,生活只是不朽的靈魂對理念的回憶。在生命的歷程中,有誰不回想起一些細枝末節的,與任何別人無關的事情?昂儒街的住所有一個花園,花園裡有一條椴樹組成的綠廊。我在那裡等候雷卡米耶夫人時,從枝葉間瞥見一縷月光:難道我不覺得這縷月光是屬於我的,只要去那些樹下就能再見到它?我曾看見陽光照耀著許多人的面孔,可就是想不起陽光。
(Jallai voir Madame Récamier rue Basse−du−Rempart et ensuite rue dAnjou. Quand on sest rejoint à sa destinée, on croit ne lavoir jamais quittée : la vie selon lopinion de Pythagore, nest quune réminiscence. Qui, dans le cours de ses jours, ne se remémore quelques petites circonstances indifférentes à tous, hors à celui qui se les rappelle ? A la maison de la rue dAnjou il y avait un jardin ; dans ce jardin un berceau de tilleuls entre les feuilles desquels japercevais un rayon de lune, lorsque jattendais Madame Récamier : ne me semble−t−il pas que ce rayon est à moi et que si jallais sous les mêmes abris, je le retrouverais ? Je ne me souviens guère du soleil que jai vu briller sur bien des fronts.)
[林中修道院]
……
朋友們的不幸常常傾落到我身上,而我也從不躲避神聖的重負:酬勞的時刻已經到了;一種真誠的愛慕願意幫助我承受眾多朋友給我衰老之年增加的壓力。在走近末日的時候,我覺得我曾經珍愛的任何東西,都是與雷卡米耶夫人分不開的,她是我愛情的隱秘之源。我把各個年齡的回憶,關於夢想與現實的回憶都糅合在一起,做成一個由魅力與淡淡的痛苦組成的複合體,而她就成了這個複合體看得見的外形。她支配了我的感情,一如天上的權力把幸福、秩序與和平放進我的本分之中。
(Le malheur de mes amis a souvent penché sur moi et je ne me suis jamais dérobé au fardeau sacré : le moment de la rémunération est arrivé : un attachement sérieux daigne maider à supporter ce que leur multitude, ajoute de pesanteur à des jours mauvais. En approchant de ma fin, il me semble que tout ce que jai aimé, je lai aimé dans Madame Récamier, et quelle était la source cachée de mes affections. Mes souvenirs de divers âges, ceux de mes songes, comme ceux de mes réalités, se sont pétris, mêlés, confondus pour faire un composé de charmes et de douces souffrances, dont elle est devenue la forme visible. Elle règle mes sentiments, de même que lautorité du ciel a mis le bonheur, lordre et la paix dans mes devoirs.)
我在她剛剛踏上的小徑隨她而行,那個行路的女人,不久,在另一個國度,我會趕在她前面。如果她來本回憶錄漫步,在我匆匆建成的大教堂拐角上,會見到我在此奉獻給她的小教堂;她或許樂意去裡面休息:我在裡面掛上了她的畫像。
……不過,如果說在永恆的忘川邊上,一切真實和夢幻都是枉然;在人生的盡頭,一切都是荒廢的時光。
(…mais si près de loubli éternel, vérités et songes sont également vains: au bout de la vie tout est jour perdu.)
——《墓畔回憶錄》.〈篇章二十八〉
繼續閱讀及分享夏多布里昂的《墓畔回憶錄》(中冊)。
進入到中冊的下半部,夏多布里昂終於開始寫到雷卡米耶夫人(Madame Récamier),這一位當時的社交名媛主辦林間修院(abbaye-aux-Bois)沙龍,並成為歐洲最知名以及最大的沙龍之一。往來的賓客除了政商名流,還包含拉馬丁、聖伯夫、巴爾扎克等當代文豪……(詳維基百科)
以下摘要分享。
書名:墓畔回憶錄(全三冊)
Mémoires d’outre-tombe
作者:夏多布里昂(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
譯者:程依榮、管筱明、王南
出版社:四川文藝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5/04
【Excerpt】
〈篇章二十八〉
[雷卡米耶夫人]
我們去羅馬使館赴任,去我晝思夜想的那個意大利。在接下去敘述之前,我應該提一提一位婦女。直到本回憶錄結尾,讀者都可以見到她:從羅馬到巴黎,在我和她之間將展開一段通信聯繫:因此,讀者應該知道我是在給一個什麼樣的女人寫信,我是在什麼時候,又是怎樣認識雷卡米耶夫人的。
在社會各個階層,雷卡米耶夫人都遇到一些在世界舞台上或多或少有些名氣的人物。大家都對她表示崇拜。她的美貌把她的理想生活與我們歷史的具體事實結合在一起:寧靜的光照著一幅暴風雨的畫面。
讓我們還是回到已逝的時代,借著我夕陽的餘暉,努力在天幕上描繪一幅肖像。我的黑夜臨近,不久就會在天上撒滿陰影。
一八〇〇年我回國後,《信使報》刊發了我一封信,引起德·斯塔爾夫人注意。當時我的名字還在流亡貴族的名單上;《阿達拉》使我走出了默默無聞的狀態。在德·封塔納先生請求下,巴茲奧西夫人(波拿巴的妹妹埃莉莎·波拿巴)替我申請並獲得批准,把我的名字從流亡貴族名單上一筆勾銷。經辦此事的便是德·斯塔爾夫人。我去向她致謝。我記不起是克里斯蒂安·德·拉穆尼瓦翁還是《科琳娜》的作者(德·斯塔爾夫人)把我介紹給雷卡米耶夫人的。她當時住在勃朗峰街她家的府邸裡。我剛從樹林裡出來,剛剛走出生活中的陰暗地帶,仍然很孤僻,勉強才敢抬眼注視一位身邊圍滿崇拜者的女人。
大約一個月以後,有一天早上,我去德·斯塔爾夫人家,她在梳妝台前接待我。她一邊由奧利韋小姐侍候著穿衣,一邊跟我說話,手指間還捏著一根小青樹枝。雷卡米耶夫人穿著一襲白袍,突然走進來,在一張藍綢沙發中間坐下。德·斯塔爾夫人仍然站著,正在談話的興頭上,就繼續滔滔不絕地說下去。我望著雷卡米耶夫人,勉強才答上幾句。我從未想到有這樣漂亮的人兒,我也從沒有這樣洩氣:我對她的仰慕變成了對自己的不滿。雷卡米耶夫人走出房間。我再見到她,是十二年以後的事了。
十二年!是什麼敵對力量這樣切割糟蹋我們的年華,諷刺地把它慷慨送給被稱為愛慕的冷漠,外號叫幸福的不幸!接下來,當年華最珍貴的部分凋零、消耗之後,它又嘲諷地把你帶回起點。而且,它是怎樣把你帶回來的呀?一些古怪念頭、一些討厭的幽靈、一些上當的落空的感覺折磨著你的頭腦,攔在你前面,阻礙你得到那本來還可以品嘗的幸福。你悶悶不樂地回來,內心充滿痛苦和遺憾,想起那純潔的年華,便為如此艱難的青春時期的過錯而懊悔。我遊歷羅馬、敘利亞,目睹帝國興亡,成為風雲人物,不再做沈默之人以後,回來時就是這樣一種心情。雷卡米耶夫人又幹了什麼事呢?她過的又是什麼樣的生活呢?
(Douze ans ! Quelle puissance ennemie coupe et gaspille ainsi nos jours, les prodigue ironiquement à toutes les indifférences appelées attachements, à toutes les misères surnommées félicités ! Puis par une autre dérision, quand elle en a flétri et dépensé la partie la plus précieuse, elle nous ramène au point du départ de nos courses. Et comment nous y ramène−t−elle ? Lesprit obsédé des idées étrangères, des fantômes importuns, des sentiments trompés ou incomplets dun monde qui ne nous a laissé rien dheureux. Ces idées, ces fantômes, ces sentiments sinterposent entre nous et le bonheur que nous pourrions encore goûter. Nous revenons le coeur souffrant de regrets, désolés de ces erreurs de jeunesse, si pénibles au souvenir dans la pudeur des années. Voilà comme je revins après être allé à Rome, en Syrie ; après avoir vu passer lEmpire, après être devenu lhomme du bruit, après avoir cessé dêtre lhomme du silence et de loubli, tel que je létais encore, quand je vis pour la première fois Madame Récamier. Quavait−elle fait ? Quelle avait été sa vie ?)
下面我將給你們敘說她的生活。她的日子過得既光輝燦爛,又默默無聞,其中大部分為我所不瞭解,因此我不得不求助於一些權威,它們雖與我的權威不同,卻是不可置疑的。首先,雷卡米耶夫人向我講述過她目睹的一些事情,並且給我寫過一些珍貴的書信。她將所見所聞,都寫了筆記,她不但允許我查閱,而且允許我引述,這是十分難得的。其次,德·斯塔爾夫人在已經印出來的通信集裡,邦雅曼·龔斯唐在他還是手稿的回憶文章裡,巴朗謝先生在我們共同的女性朋友的小傳裡,德·阿布朗泰公爵夫人和德·冉利夫人在她們的文章草稿中,都給我的敘述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我只是把那些美麗的姓名串接起來。若是哪個事件的環節斷了或者扯開了,就用我的敘述填補空白。
蒙田說,人類張開懷抱迎接未來的事物,而我卻有個怪毛病,張開懷擁抱過去的事物。尤其當人們回顧親愛的人早年的生活時,一切都是快樂:人們是在延長所愛的生命,是在把愛情擴展到原來並不瞭解現在回憶起來的日子,是在美化現在人過去的生活,是在給青春做補償。
一八三九年,於巴黎
[雷卡米耶夫人的童年]
在里昂我參觀過植物園。它就建在古圓形劇場的廢墟上,位於古荒漠修道院的花園裡。那座修道院現在已經倒塌了。羅訥河和薩奧納河就在腳下;遠處聳立著歐洲最高峰。那是意大利的第一個里程碑,它那白色的告示牌直插雲霄。雷卡米耶夫人曾被送進這家修道院,在一道柵門後面度過了童年。只有在舉行彌撒的日子柵門才向外面的教堂打開。那時,人們便可以在修道院的內部小教堂見到匍匐禱告的姑娘們。女修道院長的聖名瞻禮日就是修道院的主要節日;由女寄宿生中最漂亮的一個向院長致例行的祝賀:同伴們給她整戴好首飾,扎好辮子,戴上頭巾,披上面紗。這一切都是靜靜地做好的,因為揭開面紗的時刻是修道院裡所稱“鴉雀無聲”的時刻之一。接下來朱麗葉得到了當天的榮譽。她父母在巴黎安了家,便把孩子召回身邊。在雷卡米耶夫人寫的一些草稿中,我收集了這則筆記:
“姨媽來接我的前一天,有人把我領到院長嬤嬤的房間,接受她的祝福。第二天,我跨出修道院大門。大門打開讓我進去的情形我記不起來了。我滿臉淚水,和姨媽坐上一輛馬車去巴黎。
“我依依不捨地離開了一個那樣純潔,那樣平靜的年代,走進了動蕩不安的歲月。有時我像做一個朦朧而溫柔的夢,又想起那個時候的事,想起那裊裊的香煙,想起那沒完沒了的儀式,想起在花園裡的迎神遊行,想起那時唱的歌和那時的花。”
從一個虔誠的僻靜的地方出來的歲月,如今在另一處虔誠的清靜的地方休息,它們的清純與和諧沒有損失半分。
[雷卡米耶夫人的少年時期]
伏爾泰之後,最有頭腦的男人是邦雅曼·龔斯唐。他力圖使人們對雷卡米耶夫人的少年時期有所瞭解:他打算描繪出模特的輪廓,在她身上提取出一種並非與生俱來的優雅。
“在當代因為面孔、才智或者品性的優勢而出名的女人中間,”他寫道,“有一個我願意描繪。先是她的美貌讓人仰慕她,接下來她的靈魂讓人瞭解她。她的靈魂看上去比她的外貌還要美。社會風習給她提供了施展才智的辦法。她的才智並不在她的靈魂與容貌之下。
“才滿十三歲她就嫁了人。男人一心忙於大事,不能指導這個極為幼稚的孩子。於是在一個仍是一片混亂的國家裡,雷卡米耶夫人幾乎全靠自己來打理生活。
“同時代有許多婦女名滿歐洲。她們中的大部分都向時代進了貢,有些人的貢品是她們那毫無溫情可言的愛情,另一些人的貢品則是向相繼而來的暴政做有罪的屈服。
“人處在這種環境,不是被它腐蝕,便是被它敗壞。可是我描寫的這個女子,卻是光彩奪目、純潔無瑕地從這種環境出來了。首先童稚是她的一種保障,因為這個美妙作品的創造者使一切都變得對她有利,她住在一個由藝術裝點的僻靜處所,遠離塵世,學習詩歌與其他有趣的功課,把這些仍屬另一種年齡的樂趣當作自己的日常消遣。
“她有一些少年夥伴,也常常和她們一起玩一些鬧鬧嚷嚷的遊戲。她身材苗條,體態輕盈,每次跑步,總是跑在前面。她把眼睛蒙上布條。有朝一日,她將看穿所有人的靈魂。她的目光如今是那樣生動,那樣深邃,似乎在向我們揭示一些她本人也不清楚的秘密,但那時卻只閃爍出歡樂和頑皮的光芒。她那一頭秀髮每次散開來都要惹得我們心慌意亂。她那時把頭髮披落在白皙的肩膀上,當然這對任何人都沒有危險。她那稚氣的談話常常為長久的清脆的笑聲打斷;不過人們在那時就已經注意到她那敏銳捕捉笑料的觀察力,那尋找快樂卻從不傷人的調皮,尤其是那份優雅、單純和趣味純正的感覺。那是真正的天生高貴,其資格是烙在享有天賦的人身上。
“當時的上流社會與她的本性太不相容,以至於她只能偏愛隱居。當任何封閉的圈子都會招來懷疑時,把房子對所有人開放便是唯一可行的聚會辦法。各階層的人都來到這些房子,因為在這裡可以說話卻不招惹是非。可以見人卻不會受到連累;在這裡流腔痞調替代了風趣,亂七八糟換下了歡樂。但是在這裡從來見不到她的身影。在督政府大院裡,權力顯得既凶狠又親切,讓人既生出恐懼又免不了輕蔑。在這裡也見不到她的身影。
“然而雷卡米耶夫人間或也走出偏僻的居所,去劇院看戲,或者去公園走走。因此,在眾人常去的這些地方,她少有的幾次出頭露面成了真正的事件。這些大型聚會的其他目的都被人忘記了,每個人只是朝她經過的地方衝過去。幸運地給她領路的男子必須戰勝像障礙一樣攔在他面前的仰慕者。她的腳步時刻被擁擠著圍觀的人所阻延。她帶著兒童的快樂和少女的羞怯享受著這份成功。但那份莊重與優雅,在家裡使她超出其他年輕女友,在外面,則鎮住了衝動的人群。似乎她光是以自己的出場,就支配了座中的朋友和外頭的公眾。雷卡米耶夫人婚後頭幾年就是這樣過的:不是在偏僻的居所寫詩吟詩,玩遊戲,就是驚鴻一現地光彩奪目地在交際場所露一露面。”
……
[我再次見到雷卡米耶夫人——德·斯塔爾夫人之死]
我再次見到雷卡米耶夫人,是在法國名流感到痛苦的年代,德·斯塔爾夫人就是那個時期死的。《苔爾芬》的作者在百日王朝後回到巴黎時已有疾病纏身。我在她家和德·迪拉公爵夫人府上都見到過她。漸漸地她的身體每況愈下,不得不臥病在床。……
……
沒過幾天,德·斯塔爾夫人換了房子,請我去馬圖蘭新街她的新家吃晚飯。我去了。她不在客廳裡,甚至也不能出來吃飯。但她尚不知道大限已是如此逼近。我們入了席。我坐在雷卡米耶夫人旁邊。我有十二年沒有遇見她,就是那一回見到,也只是片刻之間的事。我沒有望她,她也不望我。席間兩人沒有說一句話。只是到了散席的時候,她才靦腆地跟我談了幾句德·斯塔爾夫人的病情。我稍稍偏過頭抬起眼睛。今天我擔心上了年紀的嘴巴會說出褻瀆一種感情的話。這種感情在我的記憶中保留了它的全部青春,而且隨著我日漸衰老,它的魅力也日益增大。我撇開晚年的日子,要發現那後面天國的幻影,要聽見深淵下方一個更幸福的地區的和諧聲音。
……
我常去城牆下街看望雷卡米耶夫人,後來她搬到昂儒街,我又常去那兒。人一旦與命運重新會合,就以為從不曾與它分離過:照畢達哥拉斯的說法,生活只是不朽的靈魂對理念的回憶。在生命的歷程中,有誰不回想起一些細枝末節的,與任何別人無關的事情?昂儒街的住所有一個花園,花園裡有一條椴樹組成的綠廊。我在那裡等候雷卡米耶夫人時,從枝葉間瞥見一縷月光:難道我不覺得這縷月光是屬於我的,只要去那些樹下就能再見到它?我曾看見陽光照耀著許多人的面孔,可就是想不起陽光。
(Jallai voir Madame Récamier rue Basse−du−Rempart et ensuite rue dAnjou. Quand on sest rejoint à sa destinée, on croit ne lavoir jamais quittée : la vie selon lopinion de Pythagore, nest quune réminiscence. Qui, dans le cours de ses jours, ne se remémore quelques petites circonstances indifférentes à tous, hors à celui qui se les rappelle ? A la maison de la rue dAnjou il y avait un jardin ; dans ce jardin un berceau de tilleuls entre les feuilles desquels japercevais un rayon de lune, lorsque jattendais Madame Récamier : ne me semble−t−il pas que ce rayon est à moi et que si jallais sous les mêmes abris, je le retrouverais ? Je ne me souviens guère du soleil que jai vu briller sur bien des fronts.)
[林中修道院]
……
朋友們的不幸常常傾落到我身上,而我也從不躲避神聖的重負:酬勞的時刻已經到了;一種真誠的愛慕願意幫助我承受眾多朋友給我衰老之年增加的壓力。在走近末日的時候,我覺得我曾經珍愛的任何東西,都是與雷卡米耶夫人分不開的,她是我愛情的隱秘之源。我把各個年齡的回憶,關於夢想與現實的回憶都糅合在一起,做成一個由魅力與淡淡的痛苦組成的複合體,而她就成了這個複合體看得見的外形。她支配了我的感情,一如天上的權力把幸福、秩序與和平放進我的本分之中。
(Le malheur de mes amis a souvent penché sur moi et je ne me suis jamais dérobé au fardeau sacré : le moment de la rémunération est arrivé : un attachement sérieux daigne maider à supporter ce que leur multitude, ajoute de pesanteur à des jours mauvais. En approchant de ma fin, il me semble que tout ce que jai aimé, je lai aimé dans Madame Récamier, et quelle était la source cachée de mes affections. Mes souvenirs de divers âges, ceux de mes songes, comme ceux de mes réalités, se sont pétris, mêlés, confondus pour faire un composé de charmes et de douces souffrances, dont elle est devenue la forme visible. Elle règle mes sentiments, de même que lautorité du ciel a mis le bonheur, lordre et la paix dans mes devoirs.)
我在她剛剛踏上的小徑隨她而行,那個行路的女人,不久,在另一個國度,我會趕在她前面。如果她來本回憶錄漫步,在我匆匆建成的大教堂拐角上,會見到我在此奉獻給她的小教堂;她或許樂意去裡面休息:我在裡面掛上了她的畫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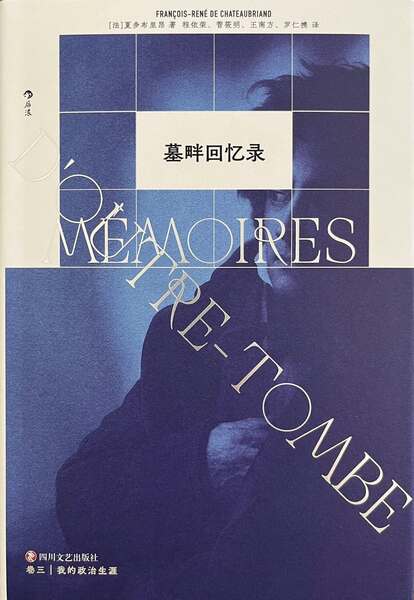


你可能會有興趣的文章:
限會員,要發表迴響,請先登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