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看一個人,是只看他的立場、陣營、過錯,還是承認他是一個有尊嚴、有複雜情感的生命?願自有永有者引導我們以行動作答。
近日,河南周口的一個新聞,讓無數人唏噓不已——一名婦產科醫生,從樓上墜下,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她的家屬說,長期的網路暴力,是壓垮她的最後一根稻草。三起醫療糾紛引發的輿論漩渦,把她推到公眾的審判台上。有人在網上指責,有人惡語相向,還有人把侮辱性的詞彙反覆掛在她名字後面。
在短視頻平台,她的工作場景被剪輯、拼接成情緒化的內容,評論區成了集體宣洩的出口。她的朋友圈和社交平台成了輿論的靶心,熟人和陌生人混雜在同一個罵聲合唱裡。調查組已經介入,具體責任還在查。但無論結果如何,我們都無法迴避:一個人,在數不清的指責與辱罵聲中,孤立無援地走向了人生的終點。

這不是第一起網暴死亡事件。過去幾年,從娛樂圈演員到普通的老師、護士,甚至中學生,類似悲劇屢屢出現。每一次,我們都震驚、憤慨、呼籲改變,但熱度過去,一切又回到原點。下一次悲劇來時,人們仍說:怎麼又發生了?
但現實是,這個問題並不會自己消失。網路是我們共同生活的空間,我們每個人都可能既是潛在受害者,也可能是無意中的施暴者。按下回車鍵的手指,能救人,也能殺人。
為什麼網路時代更容易網暴?
網路時代的信息流動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快,我們的注意力卻被分割得支離破碎。大多數人不會為了一個陌生人的遭遇停下來瞭解全貌,只會在短暫時間內做出判斷。心理學上有一個概念「去個體化效應」。人在群體中容易喪失自我約束感,而網路正是一個巨大的匿名人群。當你覺得「大家都在罵」,你就更容易參與其中,因為有一種「正義群眾」的錯覺。
更糟的是,演算法機制會推送同類觀點,讓你以為「全世界都和我一樣憤怒」,從而進一步加劇攻擊性。這就像在封閉的回音室裡,你只聽到自己喜歡聽的聲音,直到它變成咆哮。於是,網暴就這樣形成了:一則未經完全核實的信息,配上誇張的標題和斷章取義的視頻,再加上評論區的情緒引導,很快,一個人就會被推到輿論的絞刑架上,任人投擲石頭。
網暴的根本是看不見「人」
很多人以為,網路暴力就是罵人。但它的根本,不只是罵,而是語言的暴力化。語言的暴力,有幾個顯著特徵:第一,誇張化。為了吸引注意力,情緒和措辭都會被推到極端。一次醫療差錯,被說成「草菅人命」;一次服務不到位,直接升級為「喪盡天良」。誇張一旦成了語言上的暴力,它就會用情緒壓過事實,讓理性退到角落。
第二,標籤化。給人貼上一個負面標籤,然後用標籤替代整個人。比如「黑心醫生」「騙子」「人渣」,這些詞一旦落下,就像刻印,任你怎麼解釋都難以抹掉。
第三,去人化。當我們攻擊一個陌生人時,我們往往不再把他當「人」看,而是當作一個靶子,一個虛擬的符號。這樣一來,語言就不再有分寸,因為我們已經把對方從「有血有肉的生命」降格為「發泄對象」。
法國記者讓·哈茨菲爾德(Jean Hatzfeld)在《砍刀的季節》(Machete Season)一書中,記錄了多位參與盧安達大屠殺者的口述。其中有一名男子,親手殺死了與自己為鄰多年的朋友。他回憶說:「在那致命的一刻,我沒有看見他曾經的模樣。」就在砍刀落下的前一秒,鄰居的面孔在他眼裡變得模糊,「五官的輪廓確實與我認識的那個人相似,但我的腦海中,沒有任何清晰的念頭告訴我,我們曾相鄰而居那麼多年。」那一瞬間,鄰居在最真實的意義上,「看不見」了。那是一種心理上的失明。當你不再把對方當人看,任何傷害都變得理所當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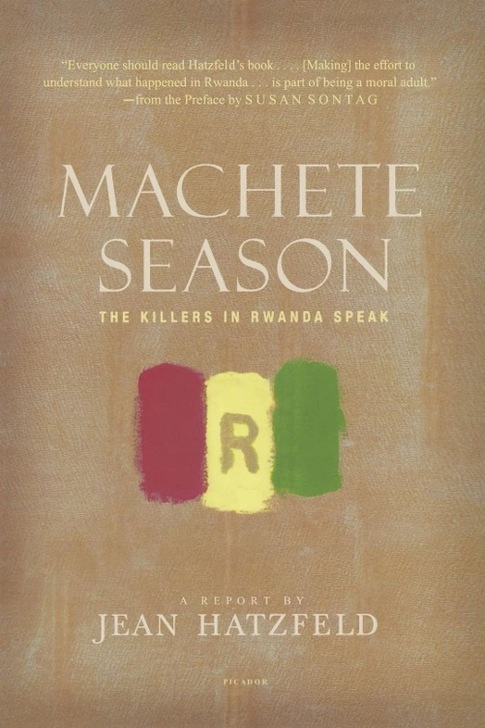
<Machete Season>, Macmillan USA
我越來越覺得,網路暴力的真正問題,是我們失去了「看見人」的能力。哲學家伊裡斯·默多克曾說,道德生活的核心,不在重大抉擇的時刻,而在日常細節中你如何去「看」別人。當我們真正看見一個人時,不是只看到他的標籤、身份、過錯,而是承認他是一個有尊嚴、有複雜情感的生命。
但現實是,我們更容易看見的,是「立場」、「陣營」、「群體身份」。當人被簡化為一種身份或標籤,他就不再是完整的「人」,只是一個「代表」,一個可以被攻擊的符號。於是,當我們對著頭像開火時,不會感到愧疚,因為那好像不是一個會受傷的人。這種「看不見」,不只發生在網絡上,也發生在地鐵裡、餐館裡、辦公室裡。當我們對清潔工、快遞員、服務員冷眼相對時,我們也是在忽略他們作為人的尊嚴。
愛人如己,不是浪漫的口號,而是一個極其現實的操練,當你在生活中真正遇到另一個人時,你要放下成見,用耐心和分辨力去看他。這種「看見」,可以很細微:在上網評論前,先問自己:「我看到的是全部事實嗎?」當身邊人情緒失落時,留意到他的沉默,輕聲問一句:「你還好嗎?」在公共爭論裡,試著先去理解對方的處境,而不是急著反駁。
看見他們,就憐憫他們
這種看見,需要刻意練習。治療師兼作家瑪麗·派弗(Mary Pipher)受過專業訓練,但她在心理治療中的「訣竅」恰恰是——沒有訣竅,只是與來訪者真誠地展開對話。她認為,作為治療師,最重要的不是急於給出解決方案,而是那份「關注的方式——這正是愛最純粹的形式」。正如她在《給年輕心理師的27封信》中所寫:「在治療中,正如在生活中,視角就是一切。」
派弗在實踐中展現出一種愉悅而清醒的現實主義。在她的領域裡,許多心理學家如弗洛德,往往相信人類被黑暗的本能、壓抑與競爭欲驅動;而瑪麗這位曾當過餐廳服務員的治療師,看到的卻是另一番景象:那些脆弱、渴望被愛的個體,只是偶爾被困在糟糕的處境中。她總是努力走進每個人的視角,以充滿憐憫的目光去看待他們,把他們當作正在竭盡全力生活的人。她的根本立場很簡單,也很堅定:對所有人懷有憐憫之心。
聖經裡有一句話:「祂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祂在人群中,總是先看見他們真實的需要:饑餓的得飽足,病痛的得醫治,迷失的被引回正路。祂的憐憫不僅是情感的觸動,更是化為行動的愛。有一位牧者,在看見任何一個人時,會想到那是按著創造者形象被造的生命。在他眼中,每一張面孔,都多少映著創造者的形象;每一個人,都是擁有永恆靈魂的受造物,是具備無限價值與尊嚴的存在。每當迎接一個人,他都在努力回應信仰的呼召:用主的眼光去看人。那是一種憐憫、溫柔、尊重的目光,尤其會停留在那些卑微的、被忽略的、受傷的生命身上。對他而言,世上沒有一個人微不足道——每一位他遇見的人,都寶貴到值得主為之捨命。
指尖上的選擇
無論是舌頭的暴力,還是指尖上的暴力,都是由心發出。如箴言所說:「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因此,我們每天都需要保守自己的心——尤其是在指尖做出選擇的那一刻。

C.S.路易斯說:「不存在普通人,我們嬉笑、公事、結婚、冷落、剝削的對象都是不朽的人,要麼不朽地恐怖,要麼永恆地輝耀。」在網络時代,我們的手指每天都在做選擇:是用它去理解、安慰、説明,還是去攻擊、譏諷、推別人走向絕境?這一擊,可以是一個「讚」,也可以是一句詛咒;可以是伸出去的手,也可以是推下去的力。指尖上的暴力,會讓人墜樓;但指尖上的善意,也能讓人重新站起來。
在信息的洪流裡,我們無法一次救所有人,但我們可以一次少傷害一個人。這就是一個文明社會的底線,也是每個鍵盤前的人必須守住的良心。
-END-
作者簡介
劉嘉
曾為老師,多年前深受《在永世裡拋擲一個身影》一書的影響,開始思考講台與書桌的服侍。目前委身教會牧養和文字服侍。
圖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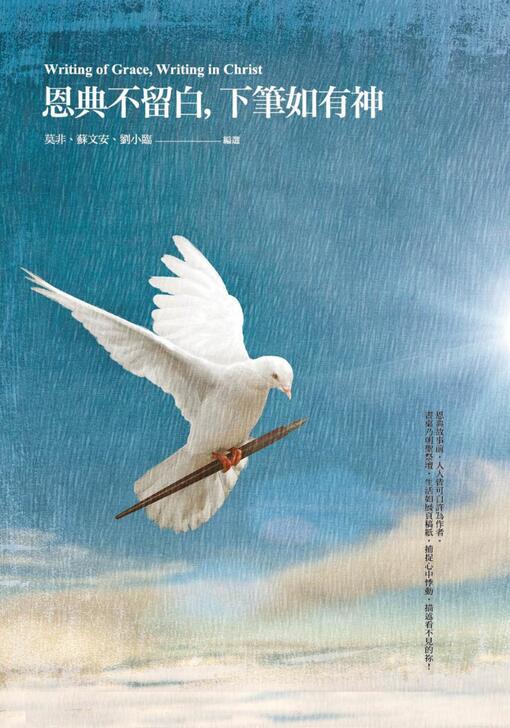
《恩典不留白,下筆如有神》
-莫非 蘇文安 劉小臨著-
恩典故事前,
人人皆可
自許為作者,
書桌乃朝聖祭壇,
生活如展頁稿紙,
捕捉心中悸動,
描述看不見的你!
購買資訊:
台灣:橄欖華宣 https://www.cclm.com.tw/book/1931
北美:gcwmi622@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