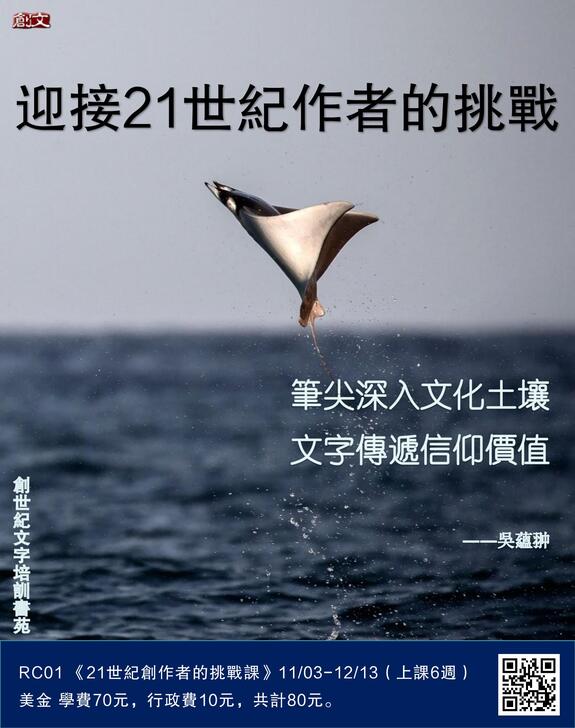大自然是一本獨特的天書。因用心「閱讀」這本書,他們讀懂了祂在其中留下的「創造性的語言」,由此生命被點燃照亮。讓我們一起來看。
筆尖深入文學土壤,文字傳遞信仰價值。歡迎查看文末海報,瞭解RC01《21世紀創作者的挑戰課》。

大自然的動植物,因我們把自己放得太大,又太聒噪,在生活中常顯渺小且沉默,但它們往往是祂安置的燈,等在那裡,被遇見,照明生命裡一些從前看不到的真相。
人生,某盞燈熄了,往往,會令另一盞燈被點亮。
約翰病了,習慣埋首在工作桌和學生當中的他,必須暫時放下一切計劃,重新聆聽身體的節奏。稍稍有力氣時,他就出外散步。
從小喜歡文學和植物,自劍橋大學文學系畢業後,他以優秀成績留校擔任老師,轉眼已經十年。這場病,把他從講堂和學生熱情的環繞中抽出,帶到野外。每天,他因身體虛弱必須慢慢地走,沒有目的地要到達,這使他能夠仔細觀察路旁各種不同花草的顏色、形狀。約翰驚歎於野外是一個伸展台,上帝親自為花草穿上自己設計的衣服,舉辦了一場又一場的服裝表演。三十一歲的他,彷彿第一次進入大自然的園子,被路旁各種植物喚醒,驚覺自己過去太忽略祂巧妙的傑作。
遇見花草,好似在病中的黑暗裡燃起了一盆火,點燃他自幼對動植物的研究熱忱。
兩年後,約翰·芮(John Ray,1627—1705)恢復了健康,也完成了《劍橋的植物》這本書。他說:「沒有一種工作,比認識大自然的美麗,並從中明白上帝無窮的智慧與美善,更有價值,更讓人歡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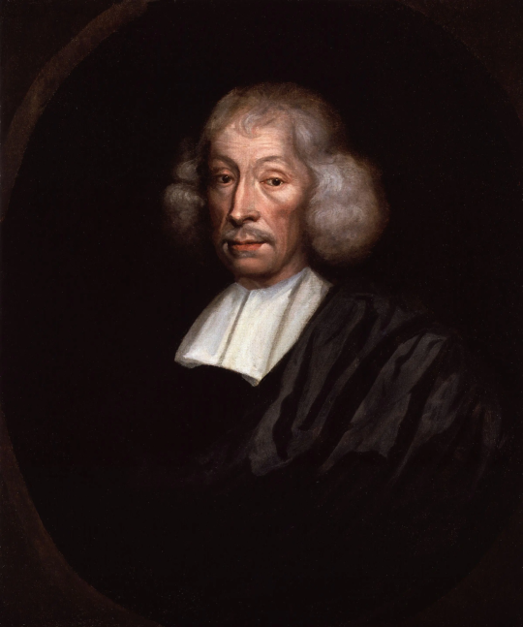
約翰·芮(John Ray,1627—1705)
他在花草的研究裡遇見祂的偉大,生命,也因此對祂屈膝跪下。1661年,當皇帝要求基督徒必須向皇帝效命,只能照皇室頒布的祈禱書祈禱時,已被按立為牧師的約翰·芮為真理起來反抗,逃到歐洲其他國家。他很清楚創造大自然生物的主也是自己生命的王,所以即使在逃亡的困境中,仍然繼續透過研究花草植物,紀錄祂的偉大。
「認識祂精美的作品,會讓你們獲得更大的滿足感。」他對學生如此說。
出身貧窮,到已經相當有學術成就時,動植物學家約翰·芮仍然兩袖清風,連奉養寡母都很困難,所以一直不敢結婚。但是在對各種動植物的認識過程中,他享受著創造主的富裕,也深感自己生命必定因祂毫無缺欠。果然,祂後來差遣一位富有的學生資助他開設實驗室,讓他可以和另一位動物學家走遍英倫三島和歐洲,收集各種植物、動物和岩石,做了非常整全的記錄,並且彙編成檔案。
這位曾經浸泡在古典文學作品中的劍橋老師,因著病中那場與花草的遇見,開始強調:親身觀察自然,遠勝於僅僅閱讀他人著作。他相信「研究自然」是敬畏祂、培養謙卑和敬拜祂的重要途徑。在自然的學術鑽研中,他從未停止尋找靈性啟示,向人述說造物主的智慧。
約翰·芮被視為英國博物學的先驅之一,最有名的貢獻是將「物種」作為分類單位,強調要依照自然特徵來劃分動植物,而不是人為或採用任意的標準。這樣的智慧,正是出於他對上帝的敬畏——人無法自己創造,卻可以透過瞭解祂的作為來理解被創造的動植物。
科學哲學家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曾講過:「在我們面前有兩本書可以研讀,第一本是聖經,啟示祂的心意;第二本是大自然,顯明祂的工作。」這正是約翰·芮的經歷——研讀聖經時,他聆聽著上帝的話,去認識祂是誰;而研讀動植物的時候,他閱讀著祂寫的另一本,為所有人打開的奇妙天書。

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
他的著作《上帝智慧的彰顯》,雖記載著對動植物的科學研究,卻也是他尊崇祂的一篇長長的信仰告白。
我想起作家楊腓力在《另一世界的傳言》這本書裡曾寫道:「自然與超自然不是兩個世界,而是同一實相的不同表現......我們生活在蛛絲馬跡之中,像救援者從炸裂的彩色玻璃碎片裡,去拼湊線索......若要完整遇見這個世界,我們需對自然界有更超自然的敏銳。」
那年,我也看見一位長輩因著遇見一片野花,點燃了活下去的盼望。
她從三十幾歲起就患上一種免疫系統的病,全身關節不停被攻擊,疼痛,是她的每一天。
誰都有痛的經驗,也會在痛的時候,想辦法忍受,同時想辦法解痛。但在那個醫學對免疫系統疾病仍然懂得太少的時代,每天,她只能看著那一瓶止痛藥,陷入什麼時候吃,什麼時候可以再等等的困難選擇裡。因為止痛藥吃多了藥效會減低,同時,她的胃被止痛藥長期侵蝕,已經出現潰瘍癥狀,連醫生給她藥時,都無奈地搖頭,告訴她:「忍不住,再吃。」
很多年間,她的生活可以縮寫成「被疼痛追趕」這幾個字。儘管身邊有愛她的家人和朋友,也有豐裕的財力可以提供她需要的醫療和富足的生活,她卻掉在疼痛的井底,爬不出來,每日都痛不欲生。
家人想盡辦法要讓她舒心,轉移她的注意力,同時,因為傳統醫學不能提供止痛劑之外的治療方案,她也嘗試了中醫和各種另類療法。可惜,這些都換不到她臉上的一個笑容。或者應該說,當她為了家人而勉強擠出一個微笑時,那表情仍充滿了苦味。
一個春天的午後,她望著藥瓶,知道才吞過藥沒多久,疼痛卻不見任何緩解,心情很抑鬱,幾乎絕望。她再也不想盯著牆上的鐘,苦苦地熬,只為了等候下次服藥時間的到來,於是,她決定換上鞋子,到外面走走。
長期生病,與外界幾乎斷了接觸,她已經忘了陽光照射在身上的感覺。丈夫曾希望帶她到處旅行,換換心情,但她總是說沒有體力,也不想出門,更不喜歡讓外面人健康燦爛的模樣來提醒自己的殘弱。
她居住的城市很安靜,每棟房子都很大,很深,被高聳的樹木擁著;只是藏在裡面的故事,就像她的痛,被包裹在物質條件的華麗裡,沒有被看見。
她走過那些和自家房子一樣,被專業園丁照料的院子。百花齊放,在她的眼中卻像一堆塑膠花那麼無趣。
突然,她被轉角路邊一塊空地吸引。
雖然那是個氣候乾燥的城市,但是她住的區每家院子都有自動噴水系統,土地總是被滋潤嬌寵出一園欣欣向榮的花草。但那片不屬於任何人家的土地非常貧瘠,明顯乾裂,連雜草都難以生存,卻長出一大片綠,還開放著好多粉色的花。
那些花的葉子和莖上布滿了透明、閃亮的水晶球,遠看以為是露珠,在陽光底下彷彿會跳舞。那花瓣薄如綢,多不勝數,呈放射狀恣意舒展,宛如一件被巧手精心裁剪的碎紙太陽;花瓣是嬌嫩的粉,有貝殼內裡最羞赧的光澤,像熔化的琥珀滴落人間。這絕非羞澀的色調,而是大自然用最純粹的顏料,在灰綠色畫布上揮灑出的頌讚。

它們如此安心地歸屬著荒地,如此安心地接受陽光的召喚而盛開,如此不介意明天的去處,只認真於當下,努力活到最燦爛,用所有生命力,去回應創造生命的設計家。
站在路邊,她想著這些路旁的花草也許這幾天盛開,明年,便不會再出現。在這種高級住宅區裡,到處都是昂貴的花草樹木,沒有人會在乎它們的死活,或是為它們駐足、多看幾眼。這些生命,只不過是脆弱又無用的存在。然而,創造主卻毫不吝嗇地為它們穿上不能被複製的色彩和造型,使它們成為天地間美麗的一份子。
她非常感動。
自己長久以來拖著殘缺的身子,連一把菜刀都拿不起來。她已經問過很多次,這樣的生命到底有什麼價值和意義?有什麼用?
之後,她才知道,那植物叫做冰花,生長在乾旱、貧瘠、充滿挑戰的環境中。最大的特點就是沒有選擇枯萎,而是演化出了儲存水分的「冰晶」細胞,使其葉子在陽光的照射下,仿彿鑲著施華洛世奇水晶鑽,將惡劣的條件轉化為獨特的美。冰花是「向陽性」極強的植物,它在夜晚和陰天會聰明地閉合起來。這是為了保存能量和水分,好在下一個豔陽天裡,能毫無保留地綻放。
遇見冰花,翻轉了躲在家裡愁眉苦臉度日的她。「從那天起,我告訴自己,至少要和冰花一樣努力活好今天。」她開始帶著疼痛與外界連結,把握每一個可以出門接觸大自然的機會,不再拒絕家人安排旅行的邀約。雖然多數時候她到了旅遊景點無法下車走路,或是只能坐輪椅在車子旁邊曬曬太陽,甚至必須待在酒店,從酒店的玻璃窗看向遠處美麗的風景,她都願意回應這每一個機會,全心頌讚祂在大自然畫布上的妙筆揮毫。
魯益師(C.S.Lewis)曾在他的著作裡多次提到,人類在自然中,看到諸如山巒、星空、海浪,所感受到的驚歎與吸引力,其實並不是我們最終渴望的東西,它們引導我們「想起」另一個更真實的世界,不再受困於眼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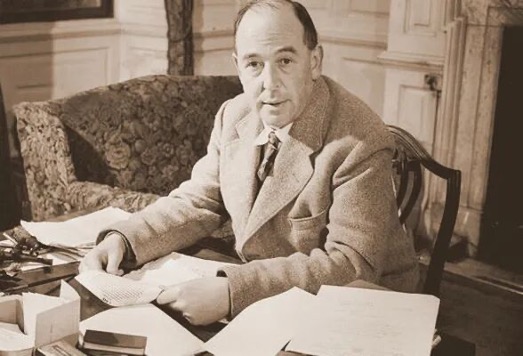
魯益師(C.S.Lewis,1898-1963)
寫《時間的皺紋》的小說家馬德琳·英格爾(Madeleine L‘engle)在她的散文集《踏水而行》裡,也多次提到自然是人類藝術創作的基礎。她認為祂在大自然裡留下了「創造性的語言」,而藝術家與信徒都需要學習「閱讀」這個神聖語言。
她寫到:
所有真正的藝術都是「道成肉身的」,真正的信仰也是如此。祂用話語創造天地萬物,天空、大地、江河、花草、鳥獸,都是那「神聖話語」的具體呈現,我們應當學習閱讀。
我們常常在螢幕上看到世界各地的好山好水。總有一些小視頻用幾分鐘,把某處自然奇觀送到眼前,也有高科技空拍才截取得下來的山川河谷鏡頭,配上介紹的文字,讓人彷彿身歷其境。每次去國家公園,對影像和空間有驚人記憶力的先生,總會指著某一個角度說:這是網路上最常出現的鏡頭。
大自然,似乎漸漸成為不出門也可以閱讀的神聖作品。
爸爸六十五歲退休後,我們一直勸他和媽媽多去旅行,到處走走。但他總笑著回答:「不用了,我天天在家看電視旅遊節目,可以到的地方更多,還很舒適,不必曬太陽,忍受舟車勞頓,最重要的是不花錢。」
這樣一晃,度過二十多年退休時光,除了幾次被姐姐、姐夫軟硬兼施帶出國之外,多半時間,因平日不愛追劇,身體硬朗的他都在螢幕裡觀看世界的天光奇景,和各種動植物的奇妙生態。
一直到那年,因糖尿病造成小腿動脈血管鈣化,步履越發蹣跚。他不想讓人看見自己的衰老,於是開始連家門都不肯踏出。身為醫生的姐夫屢屢勸他趁還能出門,假日一起到大自然裡,不用在乎能走多遠,只要能「到」,就可以享受其中。
但他固執拒絕。當時的他,雖然理性上承認有位創造宇宙萬物的主,卻未曾真正把自己交出去,仍抱著「人定勝天」的觀念。大自然,在他心中代表未知,總有一天要被征服。年輕時曾經非常愛爬山登峰的他,年老時認為面對一座爬不上去的高山,和遙不可及的大海,沒有什麼意義,只顯出自己的脆弱。
直到截肢,和身體其他器官突然快速衰微後,在離死亡線不遠處,他終於承認生命不能由努力賺取,永遠的救贖不在交換條件,而在白白領受。
相信,並且透過祈禱與主連結,使他過去對信仰的理性認知,轉變成生活的力量。稀奇的是,自尊心很強,曾經說過截肢和死亡之間會選擇後者的他,在真正開口對創造主祈禱,與祂建立關係後,竟答應坐在輪椅上,被媽媽推出門,到家附近的公園散步。

那天,在高聳的樹木圍繞下,輪椅上的他顯得格外渺小。陽光穿越樹葉,打在他蒼白的臉上,每一絲,都閃著金光。經過一片樹林,突然遇上不知名的蟲子和鳥兒扯開喉嚨飆歌。他靜靜地聽著,像一個孩子般好奇,驚喜。那一刻,他明白了自己終於不需要再與蘊藏於大自然的神秘力量爭競,害怕被吞食。放鬆的臉上出現了生病以來從未有過的笑容。
他遇到的蟲子和鳥兒到底在唱什麼?我不知道,但那是爸在這世間最後一次出門,與受造萬物告別。開口喊創造的主為父後,在生死難解的奧秘之中,他的靈魂有了安全感,不必和未知辯解,只需要信靠順服。
那個午後的蟲鳴與樹影,從未如此安靜,也從未如此響亮。它們是他一生中最後遇見的亮光——不是來自遠方,而是出自萬物深處。
原來我們從未真正遇見世界,直到世界以它本來的樣子遇見我們。
那創造的主,早已將邀請函藏在每一片花瓣的脈絡、每一聲鳥鳴的停頓之中。「遇見」,從來不是去找尋,而是被顯現;不是去征服,而是被啟示。
約翰·芮遇見了植物中的智慧,病中的長輩遇見了冰花裡的勇氣,而父親,在這最後一程的戶外時光裡,終於在自然這本天書裡,讀懂了盼望的緣由。他不再透過螢幕看世界,而是以一顆謙卑的心,接受花草樹木蟲鳴鳥叫的送行隊伍,它們向他預告著永恆的家已在不遠處,正在歡迎他回家。
路,還在延伸;
燈,依舊會一盞一盞地在路上點亮。
你願意出去走走嗎?
也許下一個遇見的,
就是你一直在等待的答案。
-END-
作者簡介
馬睿欣
電子工程學士,富樂神學院碩士。一生鍾愛寫作。曾任《宇宙光》、《真愛》雜誌專欄作者,文章發表於兩岸雜誌報紙、自媒體號等。
過去幾年主領「用心生活」線上群,透過文字去影響近萬名學員在不同人生階段(單身到成人子女的父母)的現實生活中認識真理,活出真理,享受真理。
著有散文集《遊子足音》、《管教的智慧》、《理家理心》、《直面網路》、《書蟲落網有出路》(合著)、《養育模式大逆轉》。
課程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