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安徒生大獎獲得者帕特里夏·賴特森是澳洲白人作家,卻常以澳洲原住民為主角進行書寫。她的創作有何特點,有哪些部分值得我們欣賞和借鑒?
一人一青春,一書一世界。以文學共讀,敲響少年心門。歡迎查看文末海報,瞭解YR110《樂讀少年寫實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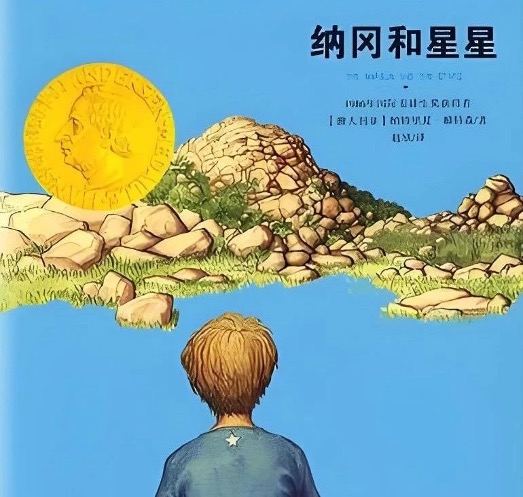
1986年在人們的記憶裡留下了難以磨滅的災難印象:美國挑戰者號航太飛機升空73秒後墜毀,蘇俄車諾比爾發生歷史上最慘重核電災難。然而那一年,也是澳大利亞兒童青少年文學發展史上星光閃耀的一年。小說家帕特里夏·賴特森(Patricia Wrightson,1921-2010)和插畫家羅伯特·英潘(Robert Ingpen,1936-)雙雙得到國際安徒生大獎的肯定,至今依然是澳洲唯二得此殊榮的創作者。
若說在地理上,於南太平洋自成一格的澳洲經過了漫長的等待,方獲得國際童書界的關注;那麼賴特森在65歲時得獎,筆耕逾三十年,也絕對算是老而彌堅的寫手了。

帕特里夏·賴特森(Patricia Wrightson,1921-2010)
兩次大戰間,在新南威爾斯州出生成長的賴特森,幼年長居鄉野,上的是給偏遠地區孩子開辦的通信學校。自然景觀無疑是她課本之外的老師,野外的動植物也是她玩耍時默默的同伴。她回憶說,從妙語如珠的律師父親那裡,她和五個兄弟姊妹享受了許多夜裡的說故事時光,以及「文學,哲學,幻想」方面的專門調教。二戰後賴特森大學畢業,在雪梨一家醫院工作,開始嘗試寫作。1955年,她發表第一本兒童小說《曲蛇》(Crooked Snake,暫譯),就得了澳洲兒童文學界最高獎勵,這鼓勵她再接再勵半個世紀。
這位晚年才獲得國際安徒生大獎的作家,2010年過世後卻彷彿再次無聲息地走入歷史,被時間的浪潮淹沒。這不只是一年新書出版量超過四位數的歐美童書界後浪推前浪,舊書很容易被忽略的結果,也是因為曾經令她揚名的乘風破浪的故事,後來卻被批評的石塊給砸沉了......我卻覺得,這位被忽視的作家和她的故事值得被打撈出來,讓我們端詳一番。
早期作品
賴特森早期作品多為寫實小說。《羽星/Feather Star,1962》、《太空人遇險記/Down to Earth,1965》和《我是跑馬場老闆/ I am the Racecourse,1968》雖然主題各異,但風格有相似之處。這些故事節奏相對舒緩,對場景刻畫細緻:《羽星》裡依山傍海小鎮的風情,《太空人》和《安迪》裡建設中的雪梨市區,讓哪怕從未到訪澳洲的讀者也彷彿親歷其境。
另一個明顯的特色,是她費心經營背景截然不同的人物如何互動,如何建立情誼。《羽星》的主角——十五歲的琳荻,不得已跟著養病父親來到海邊短期度假;她與鎮上素昧平生的少男少女幾經波折,建立起動人心弦的友誼。但把《羽星》故事提升到更高層次的,是琳荻對亞伯——那個遭到全村鄙棄,連他自己都厭惡自己的老人——從恐懼、憎惡到憐恤的複雜心理轉折。
《我是跑馬場老闆》裡的安迪是一個有特殊需要的少年,他用三塊錢向流浪漢「買下」了跑馬場,為自己和同伴帶來意想不到的衝擊與機會。這個故事翻轉了平常人的視角——原本一心一意要幫助安迪認清現實,回歸安全生活的同伴,卻因為安迪不被常規約束的想法和對跑馬場無保留的付出,被牽引著進入另一個更偉大的可能。

《我是跑馬場老闆》,甘肅少年兒童出版社
《太空人》一方面充滿了地球孩子接納保護天外來客(外星人的外表就像一個普通孩子)的暖意,一方面藉著外星人的新鮮眼光,帶出對現代文明的批判思考。賴特森的早期作品擅於從日常生活點滴裡編織故事線索,又讓不同線索彼此拉扯帶出張力;這些張力進一步帶出別出心裁的觀察和洞見:
封閉偏執不肯受安慰的老人,挑戰了少年想要多方嘗試,勇敢付出愛的冒險;天外來客外貌和平常小孩一模一樣,但思路行為挑戰了常態,挑戰習以為常的思維;有特殊需要的少年深信自己已經「買下」跑馬場,挑戰究竟什麼是擁有,挑戰所謂「主人」的責任、義務和權利。
評論家論及賴特森的作品時說:「曾有人把詩人分為兩種,一種詩人陳述己見,一種詩人邀請讀者和他一起探索。如借用此說,那麼賴特森屬於後者。」從這些故事根基牢牢紮在平常地土,枝葉卻伸向想像和哲理天空的早期作品裡,可以看見賴特森的獨特敘事魅力,與她想要借著故事探索議題的努力。
借著創作來探索思考的態度,在賴特森轉向奇幻文學創作時有了更上層樓的發展。她說:「我的一本本本書代表著一個不斷學習寫作的過程......(而)幻想是進行探索的主要手段。」
奇幻代表作
賴特森以幻想作為探索工具的第一部奇幻作品,也把她正式推向國際舞台,這便是1973年出版的《納岡和星星/Nargun and Stars》。西蒙的父母車禍喪生後,以牧羊為生的遠房親戚收養了他。
西蒙從城市來到山裡,與喜歡惡作劇的濕地精靈和山林精靈結交,他們面對著共同危機——從遠方來到山村,動機不明的石怪「納岡」。神秘的納岡比精靈們還要古老十倍,它的憤怒有可能給本地生物帶來巨大威脅。西蒙對納岡不僅是畏懼,在納岡深夜的嚎叫裡,在它移動的痕跡中,西蒙感受到從大地深處傳來的難以形容的力量。《納岡和星星》不僅是男孩西蒙與本地精靈合作阻擋了納岡的故事,也是城市外來者認識、尊重、愛護鄉野土地的故事。
在這本書的「引子」裡,賴特森敘述了納岡石怪的背景:
「流水飛奔而下,落入橫跨谷底的水潭中,發出吉他和弦般的陣陣迴響。在這水潭後面——這珠簾一般的流水後面,有一個寬寬的拱形入口;它深入懸崖底部,通向一處山洞。從很久很久以前開始,納岡就一直躺在這個洞穴裡頭。洞外雛鷹展翅,橡膠樹繁花綻放,星星爆炸,物換星移,地球雛形出現。洞穴裂開入口;滴水穿石,流水蓄滿了一個水塘,一滴又一滴,漸漸在山洞前面形成了無數根水晶柱——這一切發生的時候,納岡一直在香甜的睡夢之中。最後它終於緩緩睜開了雙眼,看到了亮光。它一點點從泥土中爬了出來。」這樣的筆觸,詩意盎然又渾厚大氣,在今日的少兒文學中已經少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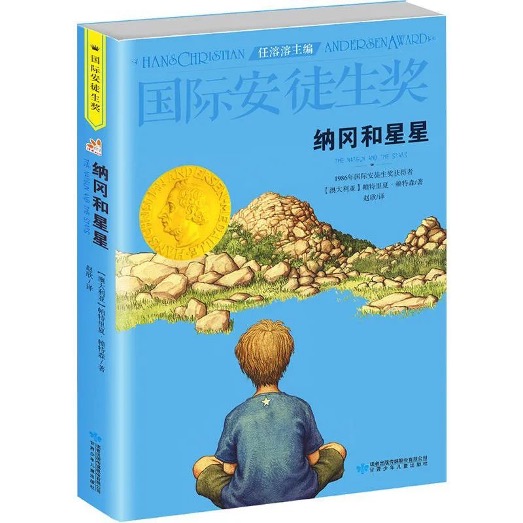
《納岡和星星》,甘肅少年兒童出版社
賴特森之後發表的《威倫歷險記三部曲》——《冰山來啦》(The Ice is Coming,1977)、《明暗之水》(The Bright Dark Water,1981)、《風的背後》(Behind the Wind,1983)更進一步探索澳洲大地歷史和原住民傳說。三部曲主角威倫是原住民後裔,起初在濱海城市受教育與工作,與白人同伴似乎沒什麼兩樣。但是當大地面臨冰河時期重新臨到的生存危機時,他受到一連串神秘呼喚,催促他離開熟悉的舒適圈。
威倫的成長之旅波折連連,尤其當他發現,外在危機與他自己的內在身份認同緊密相連:他必須願意認識自己和部族的過去和現在,也得決定是否接受下一階段任務。英雄路遙,上路之前沒有地圖,也不保證成功;並且花在傾聽和等候上的時間,往往多過勇猛爭鬥的時間。在橫跨大陸的旅行中,威倫雖然能靠祖先留下的魔法石禦風飛翔,必要時也能得到不同精靈的協助,但他生命的根,他解決問題的能力,還是得在他腳踏土地,傾聽大地密語時才深刻彰顯。
在《冰山來啦》的前言裡,賴特森如此說:
「我可以寫大家熟悉的歐洲傳統仙靈精怪——精靈、仙子、古龍和怪物......但要寫這樣的故事我必須先創造一個類似『中土世界』(托爾金《魔戒三部曲》的場景)或『地海』(娥蘇拉《地海傳奇》的場景)的奇幻異域場景,這些場景的確有強大魔力。然而我知道另一個同樣有強大魔力的場景——事實上這是我唯一深知,也唯一想寫的場景。」
賴特森唯一想寫的奇幻場景,就是她生於斯長於斯的澳大利亞,也因此她必須在這些故事裡包含澳洲原住民神話裡的精怪。她在一篇論文中總結:「For me,fantasy is man thinking; thinking about life and reality, but beyond the known facts.」(我認為奇幻文學是人類不停的思索,思索已知事實之外的生命與真實。)
誰有資格說故事?
最近這些年,賴特森的作品漸漸沉寂了。雖然在日新月異的童少出版界,老作家老作品在架上蒙灰,在網海裡沉入底層不算新鮮事,但她故事的文學濃度仍存,她探討的主題在多元文化廣被注目的今天方興未艾,而作品裡常出現的環境保護議題在21世紀也不過時,那麼為什麼她被忽視了?
賴特森被忽略,和她作品的品質高低關係不大,她本人的族裔背景才是關鍵。近年,西方文藝界越演越烈的爭議是:究竟多年長踞西方主流地位的白人作家,有沒有權利和資格述說少數族裔的故事?創作者可以從各個文化種族的豐富遺產裡自由選取材料嗎?如果創作者自身背景屬於既得利益者甚至欺壓者的族群,是否就不合適述說被壓迫者的故事?換句話說,賴特森身為白人作家,有沒有資格和權利編織以澳洲原住民為主角的故事?

《威倫歷險記》三部曲之《冰山來啦》,安徽少年兒童出版社
血統百分百白人的賴特森寫作這些以原住民神話為素材,以原住民為角色的小說,今天會被一些評論者批評為越俎代庖,奪去了原住民應該有的話語權。但賴特森創作這些故事的昨日——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澳洲白人作家對原住民文化題材普遍興趣缺缺,原住民創作者也未成氣候,她如今被批評為「撈過界」的作品,當年確實開闊了廣大讀者的眼界。
一方面,我完全同意各個少數民族或團體應持續有圈內者(insider)創作出版;擁有族裔背景的創作者說、寫、畫自己的故事,對作者和讀者都有無可取代的價值和力量。另一方面,我不能完全同意圈外人(outsider)就完全沒資格說另一個族群、另一個團體的故事。我相信,考量創作者個人寫作的時空背景,和創作者的寫作初衷對理解作品是必須的。再說,寫一個「他人」的故事,是嘗試以那個人的觀點看天地,是嘗試進入那個人的內在世界,是以理性和感性的眼睛凝視這個角色,這難道不也是愛和尊重的表現?
賴特森的作品,主角不論是白人、原住民,還是外星人,從來不是孤零零的。主人翁的發展和「他者」密不可分,這些他者與他們極不相同(年紀、階級、背景、特殊需要等差異)。主角要學習的主要功課之一,是與異己連結,建立團隊。
並且賴特森的初心,不僅在於述說單一族裔的故事。當她耕耘這些故事時,她思考的是整個澳洲,包括居住其上的各個族裔。她提出「泛澳洲神話」(Pan Australia Myth)的理念,用自己的奇幻小說來鋪陳對這個理念的深度思考。換句話說,她意圖建構跨古知新的澳洲當代傳說。這個當代傳說要夠廣夠深,能覆蓋不一樣的人種、動植物和精靈。
從歷史角度來說,千萬年來,動植物和原住民在澳洲這塊地理上孤獨的大陸上繁衍生息。兩百年前,一船船被載來的英國囚犯和接續移民,倉促甚且粗暴地改變了這塊土地。外來者成為主宰者,原住民成為邊緣人,原住民的故事或暗啞了或變調了,他們曾經有許多年無法向外界宣揚自己的故事。
逝者已遠,我無法詢問賴特森當年身為白人作者述說原住民故事時走過的心路歷程。不過從她的論文里可以管窺那不是容易的過程:
「即使我讀遍原住民的神話和傳說,認識了各種精靈,我依然沒辦法變成原住民。我終於理解到我和原住民間唯一的共享處,就是這片大地本身。既然我不能往前想像進入他者,我必須試著往後想像進入土地。然後,不可思議地成了。我發現只要我持續把原住民精靈視作土地的一部分,我就能感知他們。」
從賴特森留下的故事裡,我讀到她對所愛土地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思考,讀到她對這塊土地上所有生物如何彼此共存共榮的想像。即便我不百分百同意她的思考方向,我亦敬重她比同代人更具前瞻性的眼光,敬重她以故事編織真實願景,以故事提議不同族裔與萬物和平相處的真心實意。故事的天空豈不該和真實的天空一樣遼闊?故事的大地豈不該和真實的大地一樣寬容?願這世代的創作者,無論族裔背景,能繼續探索故事,也繼續以故事來探索。
(本文選自《尷尬少年遊》一書,橄欖華宣出版)
-END-
作者簡介
黃瑞怡
台灣大學圖書館學學士,美國俄亥俄州大學語文教育博士,專攻兒童青少年文學。多年在南加公私立中小學任職,現任聯合基督教學校國際學生部主任。台灣《校園雜誌》「尷尬少年遊」、「惡水築書橋」專欄作者。曾參與遠東廣播公司童話系列講座。
課程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