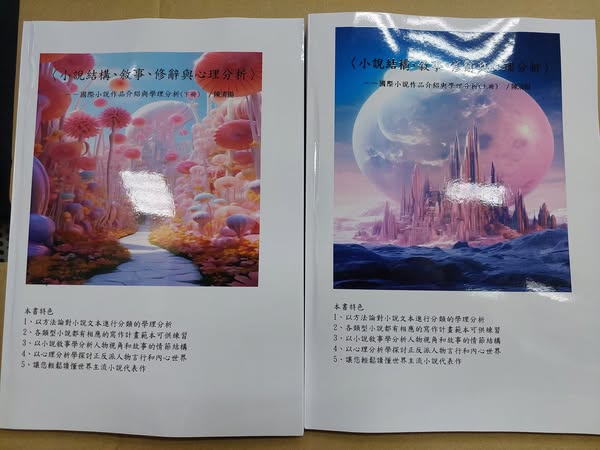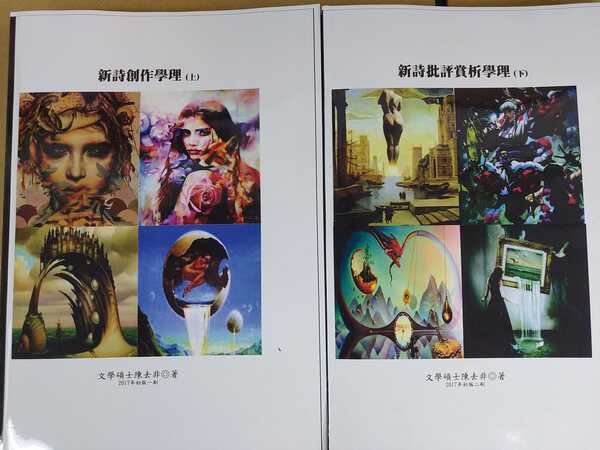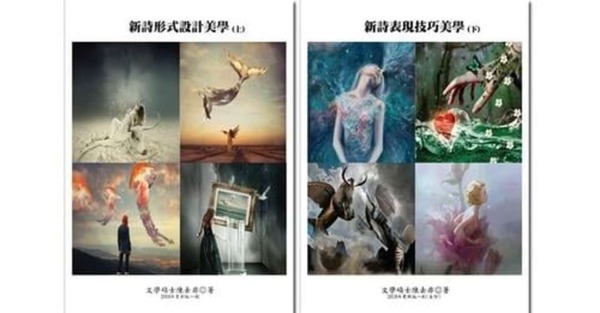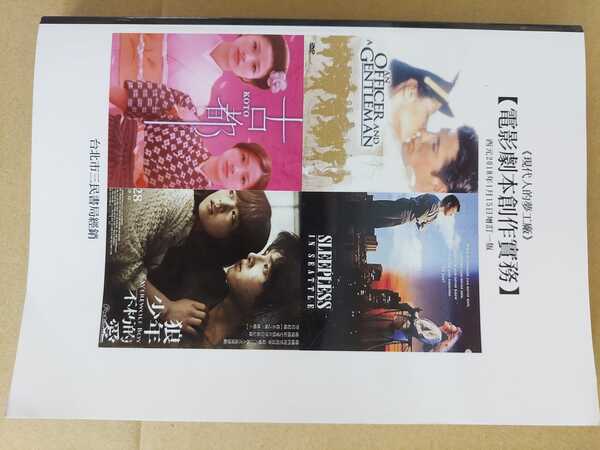〈春風放膽來梳柳〉
寫在出版前
筆者長期觀察台灣文創工作者,能夠跨領域創作的「文學的多妻主義者」相當有限,尤其是新詩和小說之間的相互跨越,難度最高,原因是新詩為最精練的語言,語意的飽和度(密度)要求最高﹔小說則非常倚重組織和整合能力,內文能夠容納的信息量龐大,並且強調戲劇性的張力(tension)。兩者各自形成一個極端,所以,小說家跨足新詩,輸在修辭表現技巧,多半淪為不入流的新詩作者﹔新詩跨足小說,輸在說故事的組織和結構能力,寫出來的小說,段落裡肯定會有一些金句和亮句,但是往往有佳句無佳篇,成不了氣候。從作者端而言,要寫出一首新詩佳作,只需靈活應用修辭學裡常用的表現技巧,能夠寫出三兩行有亮度的亮句或金句,掌握基本的敘事學概念,大致上就能在謬司的殿堂裡發光發熱。小說則有相當的入門門檻,從事小說創作,扮演的正是一個「說故事」的影舞者,小說作者自身所具備的能力(或條件),明顯超出新詩和散文作者,所以小說向來被推崇為「文學之母」。一篇小說裡,必須要有時空場景、人物及故事情節(人物間的互動),這三個基本元素,其次就是對於敘事學理概念的理解和靈活使用,能夠按照故事情節(Plot)結構,展開並循序推進故事:開端Introduction (Beginning)→發展Development→轉折Turning Point→衝突Conflict→高潮(+懸念) Climax (+ Suspense)→結局(+反轉或預留伏筆) Resolution (+ Twist or Cliffhanger)。如果故事要寫得深刻,人物要表現得立體,那麼人物的內在心理分析描寫,就必須精緻準確。當然,故事行進間的描述和人物間的對話,如果能夠加上幾句亮句或金句,令讀者印象深刻,肯定會有顯著的加分或增色效果。
從讀者端來說,要讀懂一首新詩,只需具備修辭學的基本素養,讀得懂詩句裡的「言外之音」,就已經是個「內行」讀者了。可是要讀懂一篇小說,讀者可能還必須有敘事學的概念,甚至是心理學的素養。筆者從新詩跨足小說創作是在1996年,那年發生「台海危機」。在那之前,筆者其實已經涉獵過許多海內和世界名著小說,印象最深刻的是遠景出版的「世界百大小說」,蓄積相當多的能量。從新詩跨界小說創作,我很快就抓住大方向,因為我的腦海裡儲存超過三四百本長篇小說故事,從中歸納出方法論︰結構、敘事、心理分析和修辭,這四個次元體系。
2010年,我的電視劇本《水色》拿下當年新聞局「電視節目劇本創作獎」長篇首獎,我開始把創作重心重壓到小說和劇本,新詩和新詩評論變成創作之餘的「伸展操」,讓腦細胞得到放鬆。這本論著前後歷經15年,調閱超過500本名著小說,消化了兩千則論述資料,我樂觀相信,這本著作可以為讀者打開閱讀世界名著的視窗,走出島嶼與世界名著小說接軌。並且,這本著作所採用的論述方法,肯定不是那些學院派的文學博士們,願意花時間去研究的,因為從事這些學理研究很難短時間就「立竿見影」看到成果,而我甘之如飴,原因正是佛家說的︰「歡喜做,甘願受」。提到淺碟化台灣的文化和政府主管文化部門,經過三十多年來親身體會的人情冷暖,當真是「關係網絡」在主宰文學作品的能見度,應驗了「會做人比會寫文章重要」。什麼「國家文藝基金會」的補助或者各類徵文競賽,我這類獨行俠似乎只能冷眼旁觀,看著那些充數的濫竽在特定評審的護航下,爽拿獎金和補助。這種「劣幣逐良幣」的惡質大環境下,優秀的作品往往被反淘汰。台灣無論新詩小說和電影,因為不諳國際主流趨勢,只能在島內自嗨,走不出島嶼,更遑論文化輸出了。不過,既然都已認清大環境,渺小如我只能繼續鴨子划水,反正無求於人,「春風放膽來梳柳」,想怎麼玩就怎麼玩吧﹖
陳清揚20250211
〈小說結構、敘事、修辭與心理分析〉 ∕陳清揚
--國際小說作品介紹與學理分析
本書特色
1、以方法論對小說文本進行分類的學理分析
2、各類型小說都有相應的寫作計畫範本可供練習
3、以小說敘事學分析人物視角和故事的情節結構
4、以心理分析學探討正反派人物言行和內心世界
5、讓您輕鬆讀懂世界主流小說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