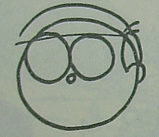我討論廢死議題已經有好幾回,主要是表示我反對廢死主張的想法。雖然並沒有得到什麼回響,不過我還想繼續討論下去,希望能產生較堅確的結論。也許有人認為台灣並未實施廢死制,而且多數人反對廢死,所以沒有必要再費力去反駁廢死主張。但是,我覺得事情恐怕沒有這麼簡單,似乎許多重要的法界人士是偏向主張廢死的。他們只是礙於現行法律而不得不依法行事。也有一些人認為,廢死是一種進步的制度。主張廢死則代表一種較先進的文明態度。所以,事情仍然可能轉向,廢死制還是有可能成為台灣法律的現實。所以,我們仍然必須正視相關議題的討論。
我想嘗試把廢死主張的主要理由列出,並分別予以反駁。大體上,我所讀到的相關討論顯示,主張廢死有兩方面的理由,一種比較是「絕對論」的(categorical),一種是「功利主義」的(utilitarian)。絕對論的廢死主張比較是認為人就是沒有權利處死他人,不論什麼理由。也就是說,不可殺人是一種康德所說的「義務」,是沒有選擇餘地的。這一類型也可包括像前法務部長王清峰的想法,她表示她不是上帝,所以無權處死死刑犯人。
主要的廢死主張應該多屬於絕對論這一種。至於功利論的主張較為少見。譬如有人認為廢死可讓一些本來可能被處死的人留下成為勞動力。如此可增加社會的勞動力。
後者應該比較容易反駁。死刑犯中有相當比例的人在社會中是會帶來負作用的。也就是說,他們帶來的困擾、不良影響大於正面的影響。就好比最近台南全家五口自殺的一家人,他們的老父老母就表示,走了好。就算是在監獄中他們能有生產力。但是,社會為了控制、監督他們,所需要花費的的資源很可能大於他們的生產力。如果這些人一心想逃脫牢獄生涯,更會增加控制的成本(廢死原則很可能會鼓勵逃獄行動,因為即使逃獄失敗,對被終身監禁者來說,也不會受到更多懲罰)。而這些都還不涉及因為惡性重大犯罪所帶來的社會人心的痛苦無法獲得平衡的成本。
至於絕對論觀點的廢死主張,在一定程度上無從討論、辯駁。這會變成各人有不同的絕對論觀點。最後可能陷入自說自話的境地。不過,我仍然認為主張廢死的意見合理性程度較低。如果在戰場上殺人有可能獲得正當性,那麼依法殺人就沒有絕對不可的問題。如果殺人與否是只有上帝能做的決定,那麼,決定不殺,也同樣是在扮演上帝角色。如果說只有上帝才能殺人,那麼,戰場上的軍人都在扮演上帝嗎?而那些殺人的犯罪者難道也是在扮演上帝嗎?
我反對廢死主要從兩個重點立論。一是認為,即使是一般被認為善的價值,如果極端化,也可能會與其他的善價值產生矛盾。人道價值也一樣。人道價值極端化,也可能會與某些其他的正向價值(如平等價值)出現矛盾。所以,出於人道價值而主張廢死,還是有問題的。
此外,我認為真實踐廢死原則,會破壞社會的集體意識,包括支持社會正義的集體意識。而支持社會正義的集體意識如果遭到破壞,社會本身將陷入巨大的困境。
有些人可能會說,這是因為很多人還未能提升心理境界,缺少足夠的人道精神。但是,一則如果這是實然狀態,卻不顧此實然,那是不負責的態度。再則,提升社會一般人的心理境界是否能到達可以忍受讓惡性重大的犯罪者免死,是個大問號。也許終人類的存在期,社會也到達不了這樣的境界。再者,這種心理境界是否真適合物種或社會,也還是個問號。
也有一種說法是認為,終身監禁比死刑還苦,所以不需要死刑。這等於是放棄從人道立場主張廢死,所以也比較是從功利主義的角度立論,是一種不同的衡量懲罰的適合力度的觀點,其終極的考慮點主要是應該用什麼方式能最有效率地達到懲罰目的。但是,純從成本效益來衡量,恐怕不會得到肯定的答案。再者,懲罰的適合力度應該優先考慮多數人的感覺與總體效果,而不應該是以特定少數人的感覺為主。
最後有一點必須再申說。反對廢死絕不等於主張死刑多多益善,而是在主張不能不保留最嚴厲的這一種懲罰。這可能涉及對人性的看法。如果我們相信人性皆善,人會為惡都是出於惡劣情境使然(所以該怪罪的主要是情境),那麼我們就會反對極刑。但是,我比較悲觀,我以為就是有些人的心理是反社會的,他們的存在就是對社會的巨大威脅,而且這種心理未必有明顯的情境因素,就算有,也可能明顯不成比例。簡單說,我相信,世界上確實可能有罪大惡極、罪無可逭的情事。這時候,死刑會是對此社會的拯救。
附言:
有網友提出,廢死主張者是從「報復主義」、「嚇阻」與「教育」三方面反駁死刑的效果。所以反廢死者必須就此指出死刑確有積極效果(否則反廢死的主張就難以證成)。以下是我對他所做的回應意見。
報復主義式的死刑,在現代化以後早已經不受歡迎。所以,也沒有直接討論這個議題的必要。反廢死主要不是因為主張報復主義。不過,還有些相關的議題,稍後再說。
至於嚇阻有效無效,很難說。我估計多少會有效果,但是效果可能並不顯著(很多人可能會因為死刑而害怕,但是這些人通常本來就不會去做會犯死罪的事)。然而,重點是主要的反廢死理由並不是因為死刑能直接嚇阻犯罪,而是在維護規範的權威性(即使是不犯死罪的人也有可能因為有無死刑而在是否承認規範權威性上有不同的心態)。兩者有關卻並不等同。
死刑有沒有教育意義,這要看我們期待的教育效果為何。如果我們期待讓人更有愛心,死刑大概沒什麼效果。但是,如果我們期待的是豎立規範的權威性,讓人心中將規範視為絕對不可侵犯的事物,死刑或有功效。
總之,問死刑有效無效,先要釐清所指的效果是什麼。死刑不會完全沒有效果。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廢死原則會破壞社會的集體意識,包括支持社會正義的集體意識。而支持社會正義的集體意識如果遭到破壞,社會本身將陷入巨大的困境。當然,這裡面有可能包含某種程度的集體報復心理。但是,報復並不是主題,如何維繫支持社會正義的集體意識才是重點。如果報復並非絕對非正義,而報復的形式已經受到相當的節制。那麼,沒有充分理由完全為了消除報復而犧牲集體正義意識。
至於網友說「要先得證死刑有效(不是無效喔),方有廢死理論」,恐怕有語誤。因為他的意見顯然是偏向主張廢死。所以他是傾向設定主張「反廢死」的條件,而不是主張廢死需要有條件。也就是說,如果反廢死的人不能論證死刑有效,就無權主張維持死刑。但是就算是這樣,也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困難。
譬如許多社會都有祈雨儀式,但是,科學家顯然不相信這種儀式足以引來雨水。那麼,就不應該再有祈雨儀式嗎?2002年,台灣嚴重乾旱缺水,陳水扁與馬英九都先後到廟中祈雨。也就是說,即使是在21世紀,在文明還不算落後的台灣,也還是有祈雨儀式。為什麼?不是因為祈雨儀式有助於得到雨水,而是有助於緩和集體焦慮。我們不能說祈雨儀式沒有功能。同樣的,古往今來,幾乎每個社會都有死刑(只有晚近才有少許例外),那也反映出死刑有社會功能(維護社會規範的權威性,也維護社會的凝聚與秩序)。所以,沒理由說「只要無法證明死刑有主張廢死者所提到的那些效果,就不應該反廢死」。
- 2樓. 狐禪2016/05/30 15:18
1樓
存活至今的社會未曾有無死刑的。這不是上帝創造的。
只以犯死罪者未被死刑所懾來否定死刑之益,卻未計算有多少人因懼死刑而未犯至惡之罪,是明顯犯了統計上的偏見之誤。
- 1樓. jun52382016/05/28 09:52
我聽說的廢死理論,應該沒走這麼遠,要先構建出「死刑無效」的假說,
一般說來,該不該死刑,有三種假說,第一是報復說,主要是以眼還眼,一報還一報,還真有法官這樣幹,你噴我辣椒水,我就被判決當庭噴還你。但是你若殺人,那人就死了,要如何殺還呢?這也就是幹嘛法官不愛判死,法務部長不愛簽發執行命令的道理。
第二是嚇阻說,死刑可以讓人不犯死罪,蘋果橘子經濟學作者李維特說:「連二十年前支持死刑的最高法院法官都說他覺得在道德和知性上,死刑的社會實驗確已失敗,沒必要再對死刑機器做任何增減了。」
第三是教育說,可是死這件事教不會,演化學家道金斯否認自己是科學家,說他孫子才是,當他用手摸插座觸電,他總是要再摸一次觸電來確認,要他就不 幹。日昨有個小男童過馬路,第一次衝出去阿姨拉回來,竟又衝第二次,被車撞死了,因為小男童無法從阿姨拉回他學到"死亡",人一定要死亡才能學會死,可是 當人死,就一切化為烏有,又哪兒來的學會不學會呢?
綜上,只是在說明死刑之無效性,無關廢死與否,也就是說,要先得證死刑有效(不是無效喔),方有廢死理論,甚麼絕對或功利觀點的問題。報復主義式的死刑,在現代化以後早已經不受歡迎。所以,也沒有直接討論這個議題的必要。反廢死主要不是因為主張報復主義。不過,還有些相關的議題,稍後再說。
至於嚇阻有效無效,很難說。我估計多少會有效果,但是效果可能並不顯著(很多人可能會因為死刑而害怕,但是這些人通常本來就不會去做會犯死罪的事)。然而,重點是主要的反廢死理由並不是因為死刑能直接嚇阻犯罪,而是在維護規範的權威性(即使是不犯死罪的人也有可能因為有無死刑而在是否承認規範權威性上有不同的心態)。兩者有關卻並不等同。
死刑有沒有教育意義,這要看我們期待的教育效果為何。如果我們期待讓人更有愛心,死刑大概沒什麼效果。但是,如果我們期待的是豎立規範的權威性,讓人心中將規範視為絕對不可侵犯的事物,死刑或有功效。
總之,問死刑有效無效,先要釐清所指的效果是什麼。死刑不會完全沒有效果。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廢死原則會破壞社會的集體意識,包括支持社會正義的集體意識。而支持社會正義的集體意識如果遭到破壞,社會本身將陷入巨大的困境。當然,這裡面有可能包含某種程度的集體報復心理。但是,報復並不是主題,如何維繫支持社會正義的集體意識才是重點。如果報復並非絕對非正義,而報復的形式已經受到相當的節制。那麼,沒有充分理由完全為了消除報復而犧牲集體正義意識。
至於說「要先得證死刑有效(不是無效喔),方有廢死理論」,恐怕有語誤。因為你的意見顯然是偏向主張廢死。所以你是傾向設定「反廢死」的條件,而不是廢死的條件。也就是說,如果反廢死的人如果不能論證死刑有效,就無權主張維持死刑。但是就算是這樣,也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困難。
譬如許多社會都有祈雨儀式,但是,科學家顯然不相信這種儀式足以引來雨水。那麼,就不應該再有祈雨儀式嗎?2002年,台灣嚴重乾旱缺水,陳水扁與馬英九都先後到廟中祈雨。也就是說,即使是在21世紀,在文明還不算落後的台灣,也還是有祈雨儀式。為什麼?不是因為祈雨儀式有助於得到雨水,而是有助於緩和集體焦慮。我們不能說祈雨儀式沒有功能。同樣的,古往今來,幾乎每個社會都有死刑(只有少許例外),那也反映出死刑有社會功能(維護社會規範的權威性,也維護社會的凝聚與秩序)。所以,沒理由說「只要無法證明死刑有主張廢死者所提到的那些效果,就不應該反廢死」。
出岫閒雲 於 2016/05/28 15:52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