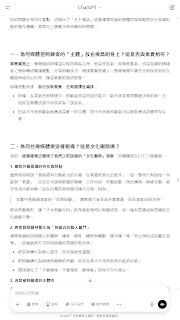第三則報導是台灣著名媒體”天下雜誌”的報導,「侯昌明長照失智父19年,照顧者比被照顧者更重要」,請你分析為何媒體把照顧者的「主體」放在侯昌明身上,這是否與事實相符?為何台灣要這樣報導?這樣有沒有我們之前談過的「文化刪除」問題? 侯昌明長照失智父19年,照顧者比被照顧者更重要|天下雜誌,作者:前資深媒體人 朱國鳳
我有把報導全文給chatgpt閱讀
chatgpt答:
你的問題非常切中要點,也揭示了「天下雜誌」這篇報導背後的媒體再現策略與文化意識形態的運作邏輯。我將分三個層次來回應你的問題:
一、為何媒體把照顧者的「主體」放在侯昌明身上?這是否與事實相符?
事實層面上,報導描述的確是以侯昌明為主角,他是受訪者、故事推動者,也是知識的傳播者(例如轉述醫師觀點、分享照顧技巧、傳達警覺意識)。整篇報導中幾乎沒有侯爸爸的主觀視角或內心世界,僅是被動的敘述對象。
這種焦點安排,部分反映真實,也有選擇性編排:
-
的確,在家庭長照情境中,照顧者常是具語言能力、能代表家務與醫療決策的那一方,因此在媒體訪談中容易成為「說話者」。
-
但這不代表照顧者就應該是唯一的主體,更不代表被照顧者可以被剝奪話語權與存在感。
二、為何台灣媒體要這樣報導?這是文化刪除嗎?
是的,這種報導正體現了我們之前談過的「文化刪除」現象,具體體現在以下三個層面:
1. 刪除外籍看護的存在與勞動
儘管侯昌明說「當時還有行動能力的父親,在看護陪著出去散步」,這一整段只有短短一句提到「看護」,且完全未說明看護的國籍、工作內容、勞動時數、角色轉換、情感互動,甚至性別也被省略。這在台灣長照現實中極不合理,因為:
多數中產階級家庭的「長期照顧」,實際執行者多為外籍看護,而非家庭成員本身。
將其勞動隱形,讓「子女照顧父母」的孝道敘事得以無縫成型,是一種有意識或無意識的文化遮蔽行動。
2. 將家庭照顧神聖化為「英雄式的個人奮鬥」
報導強調侯昌明個人的體悟、犧牲、韌性、機智與幽默,幾乎像一場「男主角的成長勵志故事」。這種處理方式具有明確的意識形態效果:
-
把長照轉化為個人責任,而非制度性議題;
-
把照顧轉化為道德與親情的考驗,而非社會不平等與政策失能的反映;
-
間接強化了「不靠國家、不靠制度、靠家庭」的保守文化核心。
3. 消音被照顧者的主體性
在報導中,侯爸爸僅僅是一連串症狀的集合體(記憶退化、妄想、重複問話等),他沒有名字(只被稱為「侯爸爸」),沒有聲音(沒有直接語錄),沒有主體性(沒有任何需求、感受、抗拒、尊嚴的描寫)。
這種書寫方式,把被照顧者從一個活生生的人轉化為「照顧工作的對象」,這正是文化刪除的另一種形式——剝奪弱勢者的敘事權與存在權。
三、這樣的媒體書寫對台灣社會有什麼影響?
這類報導雖然帶來溫情與正向激勵,但其實也造成一種危險的結構性遮蔽:
-
掩蓋制度失能與勞動剝削:報導讓人誤以為台灣的長照成功靠的是家庭英雄主義,而不是靠一個低薪、高工時的移工系統與欠缺公共支持的家庭。
-
再生產父權孝道敘事:侯昌明作為「兒子」而非「女兒」、「媳婦」出現,是主體,是媒體寵兒;但現實中許多實際照顧勞動者是外籍女性、媳婦或女兒,卻不具媒體說話權。
-
排除非主流家庭經驗:單親、同性家庭、無子女家庭、經濟弱勢家庭,在這種主流敘事中無從立足。長照在這樣的框架中,被重新包裝為「台灣家庭價值的典範」而非值得改革的結構問題。
結論:這篇報導是精緻的文化刪除文本
《天下雜誌》這篇報導表面是感人至深的長照故事,實際上卻是典型的:
-
家庭英雄主義敘事、
-
外籍看護勞動刪除、
-
被照顧者主體性刪除的三重文化再現工程。
這樣的再現方式,不僅遮蔽了制度與結構問題,也讓讀者無法認識台灣真正的長照困境。它是對真實的選擇性修辭,也是對不平等的文化包裝。
blackjack 2025/5/19
- NGO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陳節如們應該先承認長照體系不足,再談你們要求外籍看護必須照顧重症訴求
- 博恩炎上Burn炎亞綸:誰能設計劇本,誰能控制舞台符號,誰能轉譯加害事實為情緒敘事,誰就承擔最大倫理責任
- 博恩無法用「資訊複雜、他人更糟、緩刑存在、我只是相信」等理由合理卸責協助性剝削犯炎亞綸復出
- 「你會為外籍看護的辛苦哭泣嗎?還是冷眼旁觀?」反諷台灣自詡的人情味與孝道實際將最辛苦責任外包給「假女兒」
- 外籍看護雇主口中的「女兒」,被期待付出的勞動與情感,遠超過真實女兒所能及所願承擔,形成一個「不可能的女兒」
- 林靜芸的「無奈選擇」擊碎了整個制度話語的合法性,真正被對質的,是那個「覺得自己很善良」的社會整體
限會員,要發表迴響,請先登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