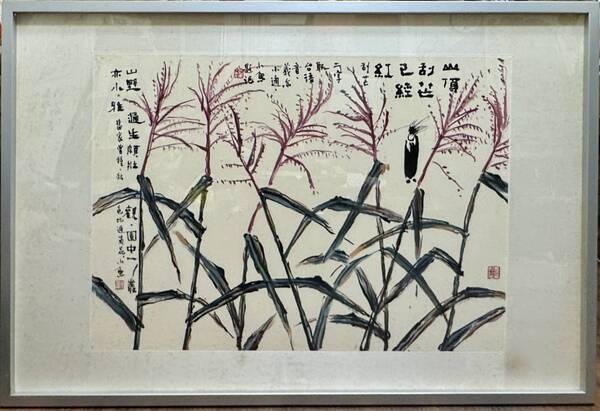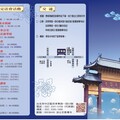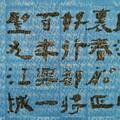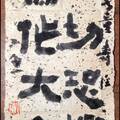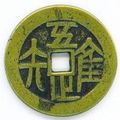《往生論註》難行道之五難(象山慶25.8.2)
曇鸞大師1《往生論註》開篇,引龍樹菩薩《十住毗婆沙論.易行品》云「菩薩求阿毗跋致,有二種道」,難行、易行:
難行道者:謂於五濁之世,于無佛時,求阿毗跋致為難。此難乃有多途,粗言五三,以示義意:一者外道相善,亂菩薩法;二者聲聞自利,障大慈悲;三者無賴惡人,破他勝德;四者顛倒善果,能壞梵行;五者唯是自力,無他力持。如斯等事,觸目皆是。譬如陸路,步行則苦。
易行道者:謂但以信佛因緣,願生淨土,乘佛願力,便得往生彼清淨土;佛力住持,即入大乘正定之聚,正定即是阿毗跋致。譬如水路,乘船則樂。
菩薩道亦如是,或有勤行精進,或有以信方便,易行疾至阿惟越致者。
(一)前序
鸞祖[1]為《往生論》作註,卻於文前先引《十住毗婆沙論》為其「判教」的理論依據。所謂「謹案」,不只是態度上的敬慎,也表示「學有所本」「所服有宗」,從其傳記可知,鸞祖學宗「四論」,稱龍樹菩薩為「本師、一切眼、慈悲尊」而南無(歸命)、禮拜之,可見其服膺之深[2],並追隨其「(已入初地)而往生安樂國」的示範,而「願共諸眾生,往生安樂國。南無至心歸命禮西方阿彌陀佛」。也可以說鸞祖除了教理上隨學龍樹之「般若中觀」,更於行願上跟從龍樹之「歸(彌陀)生安樂(淨土)」。日.知空[3]《無量壽經論註.翼解》亦云「註解之始,先引此論,憑龍樹尊,略有六意」,細述了鸞祖遵依龍樹《中(觀)論》與<易行品>之深義,以註解、判釋世親《往生論》之義理,並稟白其「歸命、願生」彌陀淨土之決心[4]。這是中國淨土教成立之初的義學基礎,並貫徹至今,談念佛往生西方極樂,其佛理根據,不離「真俗二諦」之一體相融。後世尊龍樹菩薩為「八宗」共祖[5],也包含淨土宗(慧遠/善導/慈愍三系)。
《易行品》[6],說學菩薩道者,求不退轉[7],有「難、易」二法(行道):
1.「勤行精進」,但是法甚難,「行諸難行,久乃可得,或墮聲聞、辟支佛地」:偏用「智」之(自修)度,須於此土斷(煩惱)證(涅槃)。除了道業上廣修六度萬行,次第上遍歷五十二階,時間上或須三大阿僧祇劫,這樣的數字對初學(發心)者或一般夫,既難以想像,更望而卻步,尤其到了五濁、無佛住持之惡世[8],自修很難,不退又更難。這既是龍樹菩薩的預言,也是古今教界的事實。
2.以「信方便」而「易行、疾至」不退轉地:娑婆凡夫煩惱重而智慧淺,只能偏於「信」之(佛攝)入,「應以恭敬心,(念是十方諸佛),執持稱(其)名號」,心態上歸命諸佛,行持上稱念佛名,此身於此地依稱名(三昧)之力而得不退,乃至成正覺;這是龍樹菩薩所說的方便,也是多數眾生所求的易成。
《易行品》之文義不過如此,鸞祖又進而釋曰「五濁之世,無佛之時,求阿毗跋致為難。」及「以信佛因緣,願生淨土;乘佛願力,便得往生;佛力住持,即入大乘正定之聚」;易行道的關鍵在有「他力持」,也就是「信佛、願生」「乘佛願力」而往生,由「佛力住持」而不退轉;此因彌陀淨土乃「無垢(濁)之世,有佛之時」,往生者依佛之常住加持,即可轉五難為五易;其具體行持就是世親菩薩「五念門」。
娑婆五濁之凡夫,修行不退之「難/易」差別,原因很多很複雜,鸞祖只略舉(粗言)五種「難」的現象(事),且云「觸目皆是」,就是說,諸如此類之內/外障緣,隨處可見,有如陸上步行,極其辛苦。這是在五濁+無佛之娑婆,依正二報皆不利於順於佛法,多所誘惑與障礙。而此「五難」乃由於「五濁[9]」眾生之共業所致,尤其生於「無佛」住世之時,在此娑婆修行,欲得長時精進,乃至不退,就更是難上加難,令人卻步。日.妻木直良《往生論註.服宗記》[10]云:
「世」之與「時」,唯是綺互[11];五濁約「根劣」,無佛約「緣薄」,……此有四句:一、無濁有佛,如嬰留孫佛時;二、有濁有佛,如釋尊時;三、無濁無佛,如彌勒滅後;四、有濁無佛,如今時,是為最難。
鸞祖所舉「外道、聲聞、惡人、顛倒」可歸於五濁之「根劣」而難以修習菩薩法;「無他力持」則是無佛之「緣薄」而唯靠自力以苦修;這五種即是「根鈍而障重(雖復三聞,不能得悟,止為結緣眾)」之機,「有濁而無佛(如今,為最難)」之時,若依道綽師之「約時被機」說,則是「機、教、時」乖,所以「難修難入」[12]也。何況,「五難」只是略舉(粗言五三,以示義意),而根(機)劣、緣(法)薄之於成佛之道所可遭遇的障難更多更細,如《服宗記》又云:
「此難乃有多途」者,事非一端,……《瑜伽》48說「十二種艱難之事[13]」,《寶女所問經》4明「三十二掛礙塹路[14]」,此等諸文,與今所明義趣大同。又《十住論》〈調伏心品〉說「失菩提心二十法」[15],次〈阿惟越致相品〉明「七種敗壞相[16]」,並取此等。
若憑自力進修成佛之道,不僅時劫長久(三大阿僧祇劫),且退緣甚多,難以把握;此之謂「難行」道。眾生於五濁惡世,世俗的獨善其身已很難,何況出世的修菩薩行就更難,《安樂集》第二、第五大門詳言之[17];發菩提心,是通途「修行成佛」的起點,也是別門「往生淨土」的根源;但也須多世多劫值佛發心的宿緣,乃能於今生惡世中,不謗大乘經,乃至書寫、講說,卻仍不解其深義,而不能如法的受持修行。更何況,「菩提心」難懂難發,且發心之後,須修十種行,相續萬劫,乃得證不退,如《易行品》云:「若人發願,欲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未得阿惟越致,於其中間,應不惜身命,晝夜精進,如救頭燃。」這對於「未出火宅、信想輕毛」的外凡夫,造惡受苦(生死痛燒)也做不得主了,豈能持久不倦的具備「福慧」資糧,勤修「六度」萬行,而成滿十信位,趨入十住位而得初階的位不退?
(二)以下細述鸞祖「五難」的內容:
1.外道相善,亂菩薩法:
外道有二說:
1.「佛外」之教;智顗《摩訶止觀》分三類,釋聖嚴增為四類:(1).佛法之外:如九十六種外道。(2).「依附」佛教:有神鬼的信仰與靈驗,但無思想的依據與歷史的根源,須藉佛法為靠山。(3).「錯解」佛法:於「三法印、第一義諦」之理解,皆落於有為、有所得,只求現世利益、後世福報。(4).「破壞」三寶:先取佛法之實,補自家之缺之後;又虛誇自家之長,編造佛法之短,並於大眾中公然斥責、誣陷,以破壞佛法。
2.心外求法:於「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之理,如法藏《妄盡還源觀》所說「攝境歸心真空觀、從心現境妙有觀、心境祕密圓融觀」,不能如法的信解行證,而縱令六根向外求六塵,執以為實有,妄生貪、瞋種種煩惱。[18]
上述之各種外道,也教說各種善法,表相上類似佛教,卻夾雜了邪見(斷/常二邊見,及邪因邪果,無因有果,有因無果,無因無果),能惑亂、遮障菩薩道(佛法)的真實義,似是而非,令學佛人誤入歧途。《服宗記》說,外道有兩種:1.於佛法之外,另生虛妄之見解(外之道);2.或於本心之外,別求著相之俗法(外於道);這兩種外道,不相應於佛教之涅槃(深妙之空.無相.無願,實相.真如)正理;雖也講說了種種有相之善法,卻不離於人天因果,若以此取相(我,眾生,分別,有所得,有見相)之行學佛,則亂失了(無我.無眾生,無分別.無所得,無見相)菩薩道[19]。《翼解》亦云:「理外、邪因」為外道,「斷見、常見」為相善,如印度的「六師、96種」,中國的「儒、道」,都是世間俗法;若小乘解脫道之「三法印」,或大乘菩薩道之「一實相印」,才是佛教的出世正法[20]。
外道則不然,迷惑邪見,所說之法,其相似善,而實非善;以邪亂正,人不能甄,分深成障道矣[21]。
心識行於正理之外(法外妄解),修邪教之因,而求佛法之果,必然執持「斷、常」二種邪解,或「增益、損減」二種邊見,而不能勝解中道(實相)之不生不滅,則是著相之善;迷惑於種種邪見,所說人天善法,皆是有漏之業,若以此邪見,擾亂正法,就成了菩薩道的障礙。外道與菩薩在行為表現上似同,但目標與本質不同,因此,外道的所見所行不得正果,而菩薩的上求下化終必圓滿。「八難」[22]之世智辨聰,耽溺於外道之經書而不信不學(佛教)出世之正法,可說是「聰明」反被外道誤。鸞《註》云:
諸外道輩,假入佛眾,而常伺求佛短;又如第六天魔,常於佛所,作諸留難。
不只學佛人易被外道之「相似善法」所誤導(迷惑),外道輩為了自身的利益,也常冒充佛教人而混入四眾(臥底),窺探、捏造佛之言行的缺失,以破壞其形象;乃至天魔波旬為了向佛陀爭取徒眾(魔眷屬)、壯大其聲勢,也常變現各種樣貌,故意在佛教團體中製造各種留難(留止人之善事,成為修行之障難),以障礙四眾的修行進度[23]。《大般涅槃經集解》卷17分邪正品:「魔亂真道,能惑始學人。……古今所可乖佛法事,盡是魔說。」魔羅(四魔、十魔)[24]有多義:奪命、障礙、惱亂、留難、壞人善根。總之,外道執著有相之善,不知佛法乃緣起性空,超越有無。所說法相,似善而非善,似法而非正,相似於佛法而實非無漏之善。
2.聲聞自利,障大慈悲:
小乘聲聞人,只求自我解脫,入無餘涅槃,而不發菩提心、不修菩薩法,斷送了利他的大慈悲。《服宗記》說二乘人所得乃佛法之下乘(但出世間,入無餘涅槃),因此,若墮於二乘,不再發菩提心,修利他行,是成佛之道的障礙,故名「菩薩死」[25]。《翼解》也說:「二乘雖七周行慈悲,而眾生不得其樂」[26],二乘人怖畏(厭離)「生死」,故滅盡三界「見/思」惑,入無餘(偏真)涅槃,唯「如來藏」獨存,沉空滯寂,不復於三界現身意,不再進修大乘法之自他兼利、理事圓融。生前雖修五停心之「慈悲觀」,將四無量心由近(親)至遠(疏),擴及七層對象,然其悲心並不徹底;於深入「五蘊無我」之後,就急證涅槃而不再受生、度眾,其終極目的,仍是自了生死求解脫[27]。鸞《註》對二乘人多所評論云:
但以聲聞為僧,無求「佛道」者。……但聲聞人天,所利狹小。……聲聞/辟支佛欲有所知,入定方知、出定不知,又知亦有限。
文中說,若但以「聲聞」為僧寶,則不再求「成佛」;然而,聲聞法只斷見思惑,了脫分段生死,成阿羅漢(辟支佛)之「解脫道」;也就是「以實際為證」,不能更生「佛道根芽」, 而進斷塵沙惑、無明惑,起大悲以度眾生,(斷變異生死)而覺行圓滿,成無上正覺之「佛菩提道」;因此,於自於他「所利狹小」;其所證一切智[28],遠不如佛的「如實三昧,常在深定而遍知」。《法華經》說聲聞,「但離虛妄」,未得「一切解脫」之「無上道」。若有人「聞佛名號,發無上道心」,但「遇惡因緣」而退入二乘,則於往生成佛之路「空過、退沒」,甚是可憫,可惜。因此,「聲聞」一詞,有時被用以譏言「不甚勇猛的軟心菩薩」;也由於「二乘」與「佛菩薩」所修所證所行,及其智慧/福德之差距甚大,故於佛法之見地,亦有寬有窄,如聲聞論云「一佛主領三千大千世界」,而大乘論則說「諸佛遍領十方無量無邊世界」;又對「眾生」的定義也不同,甚至相反[29]。因此之故,「佛一切種智,深廣無涯,不宿二乘,雜善,中下死屍。」而彌陀淨土亦無無「二乘、女人、根缺」之三種人與名。
其實,成佛之道乃唯一佛乘,無二亦無三,為順應行者根性而權說聲聞、辟支佛之「化城」,因此,《勝鬘經》說二乘之入滅乃「如來方便,有餘不了義說」,世親《法華經論》云:「唯有如來證大菩提,究竟滿足一切智慧,名大涅槃。」若墮於二乘而入無餘涅槃,則不再來三界上求下化,於自於他皆失「成佛」之大利,乃是「大衰患」。其所證入者,亦非究竟無上之「無住」佛涅槃。如法華會上,五千退席[30];佛深知此類人之善根、福德、因緣暫不具足,仍須多時熏習與調熟,故不強留,以免定性二乘因誤認「已得阿羅漢,是最後身,究竟涅槃」之「罪根及增上慢」,聞說不思議大法,而驚惶、毀謗[31]。二乘之心量與修證,既成了佛菩薩道上的障礙或陷阱,也就是「五濁、無佛」之娑婆修行的五難之一,學佛人難以明智輕易的避開或越過。
又,不只二乘之根性有此難,據云,七地(遠行)菩薩有「沉空」之難[32]:大乘菩薩於二阿僧祇之終(七地滿心,將入八地初心),專修「無相」觀,不見菩提與眾生,若是鈍根怯弱,著此空相,即可能廢「自他二利」之大行。如是狀態,或許有兩種應對法:
1.菩薩故意起(菩提/有情)實有之執而入八地(不動) [33],所謂「留惑潤生」, 可有兩種解釋:於(無生)法忍,(1)未得者,故留「煩惱」不斷盡,以潤「生死肉身」;(2)已得者,以大悲願,配合「習氣」,感得「法性生身」;此二類菩薩分別以兩種身,來三界修福慧,度眾生[34]。
2.諸佛神力加持,不令七地入涅槃。[35]所謂「沉空」之難,雖喻如二乘人之入(無餘)涅槃,然上地菩薩已發菩提心、得無生法忍,必得諸佛加持勸勉,故終必更上一層樓,而無退墮如二乘之事也[36]。鸞《註》云:
菩薩於七地中得大寂滅,上不見諸佛可求,下不見眾生可度;欲捨佛道,證於實際。爾時,若不得十方諸佛,神力加勸,即便滅度,與二乘無異。菩薩若往生安樂,見阿彌陀佛,即無此難。
就是說,上述的二乘人,已不能再生於三界,就只能由阿彌陀佛攝受,往生界外之淨土:
阿彌陀如來正覺住持力,自然止求聲聞/辟支佛心。
佛以本願不可思議神力,攝令生彼;必當復以神力,生其無上道心。……佛法最不可思議[37],佛能使聲聞復生無上道心。
我輩娑婆凡夫,唯有念佛往生西方,可免此「墮小、沉空」之難,因為阿彌陀佛的「正覺住持力」,能無功用的斷除其「求聲聞辟支佛」之心;乃至以「本願功德力」攝取二乘人來生淨土,進而以「悲智威神力」導引二乘人回小向大,生起大悲利他之無上菩提心,這是所謂五不思議之「佛法力」的至極成就。
總結上述「外道、二乘」乃五難之深而重者,《梵網經菩薩戒本》:說,菩薩戒子若「起一念二乘、外道心」者,犯輕垢罪[38]。又,外道與聲聞之修行高處,亦各有危險,如「非想非非想處」天,是世間修行者修行極處。修學到此,修行者再無所修,皆認為自己修到了究竟涅槃。修行者安住於此,如冰蟲/蜇魚,凍在那裡,享八萬四千大劫天福,享盡將墮之時,便謗無「究竟」涅槃[39];一念謗心,直墮地獄,重入輪回。
非想非非想定,「於無盡中,發宣盡性,如存不存,若盡非盡」(《楞嚴經》卷九),沒任何觀念,但有分別「無念無想」的微細心(非非想),壽長八萬大劫,為三界之頂。生四「無色界天」有兩種人:
1.凡夫/外道從色界四禪之「廣果/無想」等天,繼續深入禪定,而入於無色界。
2.不回心(住於空寂)的鈍根(不能出空)阿羅漢,不直從色界四禪「五不還天(無煩.無熱.善見.善現.色究竟)」之聖道中,以無漏智慧,逕出三界(已斷結使,不受輪迴);反取無色界「四空天(空、識無邊、無所有、非想非非想)」灰身滅智,住於「受/想滅盡定(五「無心」位)」,而寄居於「非想非非想處」,按部就班,多經20大劫,乃出三界。
聖道出離--此等窮空,不盡空理,從不還天聖道窮者--不迴心鈍(執事昧理)阿羅漢
凡外還墜--若從無想外道天,窮空不歸,迷漏無聞,不歸聖道,便入輪轉。
自「色究竟」天,歷「四空」天,乃出三界,為鈍根阿羅漢,若於「有頂」,用無漏道,斷惑銷礙而入空,此是樂「定」那含--定性聲聞;若在捨心,捨厭成就,覺身為礙,銷礙入空。若於廣果/無想[40],以有漏道,伏惑入空,即凡夫/外道也。
前四空處,前二色空俱亡,是窮境;後二識心都滅,發宣盡性,是窮心。心境俱空,謂之窮空。……凡夫不知我空,二乘不知法空,是謂不盡空理。若從「五不還天」,三果聖人,以窮究空力,遍歷「四空」天,方斷「四地九品」思惑,證我空理,成阿羅漢。從此保果不前,名不回心鈍根阿羅漢。若不幸而從「無想」外道天,或從「廣果」凡夫天(色界四禪天之3/4,鄰於五不還天),而入「非非想」處,究窮空理,以無「聞慧」,迷有漏天,作無為解,八萬劫後,無所歸托,隨其宿業,便入輪迴。所謂:「縱經八萬劫,終歸落空亡。」[41]
3.無賴惡人,破他勝德:
世間之違法亂紀,僧團之破齋犯戒,這些放蕩撒野的惡人,總是任意詆毀修道者,破壞其勝德;《服宗記》云,於諸修行人「種種加惱」而「無所顧難」的惡人,常能破壞初學菩薩之悲心[42]。《翼解》云:「濁世惡人,見修道,不能成人之美,反加破毀」[43];這兩註都解為「無顧」,其本性是諂曲、欺誑、憍逸、邪侈、無義無禮、無慚無愧;見有大修行人,既不知尊重、隨學,成人之美;反而橫加以惡罵、輕蔑、惱害、毀謗,破壞其「無相(寂/智慧)、大悲(照/方便)」之勝德,於自於他,皆失大利,兩敗俱傷[44]。另如鸞《註》云:
或有值佛而不免三途:善星、提婆達多、居迦離等是也。
見有如來雖有大眾,眾中亦有不慎恭敬者:如一比丘語釋迦佛「不為解難,改學餘道」。居迦離謗舍利弗,佛三語而三不受。[45]
此處所舉四例,分述如下;
#某比丘雖先以「無益之戲論」試探釋尊,但經佛解說之後,自知慚愧而信解佛語,得阿羅漢果[46]。這是個幸運而善果的例子,以下三例就至死不改而受惡報了。
#善星比丘,是釋尊在家之子,也曾任佛陀的侍者[47],《涅槃經》33/迦葉菩薩品,敘述其對釋尊之種種惡行,且不信受佛語,故唱反調,成一闡提墮地獄。釋尊雖預知其一闡提之惡性難改,卻不放棄,施設種種方便,開導救護之,終難以挽回,只能預留未來得度之因緣[48]。善星出家之初,修行精進得四禪,目空一切,越來越放逸,又親近一些外道惡友,致退四禪,卻說「無佛、無法、無有涅槃;無因無果,無有作業」;且對佛惡心相向,拒聽勸說;佛與大迦葉,來其住處,善星遙見,卻生惡邪之心,而生身墮地獄[49]。《楞嚴經》八云,善星「妄說一切法空,生身陷入阿鼻地獄。」其果報之嚴重,被記為「永斷善根,一闡提廁(廝)下之人[50],地獄劫住」。這或即是前引「以有漏道修,無多聞慧故,八萬大劫報盡,還墮入於輪迴」的實例。
#提婆達多(調達) 是釋尊的堂兄弟,因意見不合與權力鬥爭,另立教派。相關的事蹟與傳說甚多,且在二乘與大乘的經典中有相反的敘述與評價。在原始佛教中犯下五逆罪,破和合僧、出佛身血,《增壹阿含經》記提婆達多在地獄中受大苦;《法華經》則說提婆達多亦得授記成佛。有些佛典說,提婆達多是示現反派,勸令眾生勿作五逆罪。《大方便佛報恩經》說過去諸佛皆有提婆達多為「逆增上緣」,為忍辱、精進以修行的善知識,因此,提婆達多雖示現於阿鼻地獄,卻如「比丘入三禪樂」[51]。這是說無賴(顧)惡人的惡性深固,雖受佛恩而負義反咬,破佛勝德,是「不可度」者。
#居迦離(俱迦利):提婆達多的大弟子,跟隨其師壞亂僧團,俱迦離先懷嫉妬,常求舍利弗/目揵連過失,某次因誤會而毀謗二尊者與牧羊女行淫,且到處宣揚(散播假消息),雖經諸比丘、婆伽梵、釋尊依序「三諫」而不聽,於是舉身生瘡而生身墮地獄。《大智度論》將此歸於「妄證人罪,心謂實爾」,而俱迦離的「妄語」罪又更嚴重,雖經三次勸諫,仍不悔改:「心生疑謗,遂至決定」,「乃至佛語,而不信受」,是故生瘡命終,墮於八寒地獄。[52]
以上之惡人或即所謂「惡知識」[53],娑婆五濁之世,因眾生之惡業與煩惱,多有各種惡人惡知識,其自身不作善、不修行,更進而以瞋妒、毒害之心,謗他人之勝德,壞他人之進修,乃至佛勸亦不聽,臨死亦不悔;一般學佛人易被他擾亂或受其誤導,同流合汙,「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或「一盲引眾盲,相牽入火坑」。
4.顛倒善果,能壞梵行:
人天善果是顛倒、虛偽,而令人耽樂,障礙了菩薩道的清淨解脫;因果乃行為之報應(事),心性之修證(理),然其複雜性,唯佛乃能窮源遍知。《翼解》:「人天之果,非無漏善,暫樂還苦」,若終身追求這個,而捨棄了「離欲清淨」的梵行,就是顛倒。佛法所謂「四顛倒」,有二類人:(1)有為之凡夫,不知此世(迷界)之真實相,以無常為常,以苦為樂,不淨為淨,無我為我。(2)無為之聲聞、緣覺,雖對有正見,然誤以滅盡三業之現行為「涅槃」,不知佛界乃常、樂、我、淨。《安樂集》云「四倒長拘」,是知見上四種誤計,而被「顛倒」[54]所拘限而不得「正觀」實相。鸞《註》云:「人天諸善,人天果報,若因若果,皆是顛倒,皆是虛偽,是故名不實功德。」顛倒由想-見-心之無明妄計,是智慧(正觀)的欠缺,於一切「事理」遍計執而成了迷夢,以假(虛)為真(實),以邪(夢)為正(醒),於十二因緣順流而下,生滅流轉(輪迴),繫縛於三界獄,而無出離(解脫)之期。由顛倒而有「虛偽、輪轉、無窮」之煩惱汙染相,取著於種種人天(有漏)善果,以為究竟,故不能「依法性,順二諦;攝眾生,入畢淨」,於自於他,若因若果,皆無「真實清淨」之三業與利益;若依此顛倒見、妄想心而進修,只是增長個人的煩惱、無明,於人於己都無利益:「若無智慧,為眾生,則墮顛倒;若無方便,觀法性,則證實際」,又淪為外道與二乘,成了倒行逆施的難行道。
[1] 曇鸞大師乃中國淨土教的開祖,以下簡稱「鸞祖」,其《往生論註》簡稱「鸞《註》」。
[2] <讚阿彌陀佛偈>讚曰:本師龍樹摩訶薩,誕形像始理頹綱,關閉邪扇開正轍,是閻浮提一切眼。伏承尊語歡喜地,歸阿彌陀生安樂。……南無慈悲龍樹尊,至心歸命頭面禮。有人說:鸞祖也視龍樹為淨土宗的開創者與「易行道」的宏揚者,故以「本師」、「龍樹尊」等,表示崇高的禮敬;但龍樹《十住毗婆沙論》斥責「易行道」是:「怯弱下劣之言,非是大人志幹之說,汝若必欲聞此方便,今當說之。」所宗仰的是大乘難行之正常道。而淨土宗祖師的強勢「誤讀」,使龍樹與淨土宗關係緊密。天台智者亦「南無龍樹」而禮拜之。
[3] 知空(1634-1718,京都六條光隆寺,西吟門生);西本願寺派……學林之能化,則有知空、若霖、義教、功存、智洞等人,次第出現,其中以知空及……法霖,最為優秀。以下簡稱:知空《翼解》
[4] 一.因人重法故:此菩薩既有《楞伽》授讖之德,諸師所尚,聞者信伏,故以依之。二.示血脈義故:依《佛祖統紀》云:「一梵僧入鸞室,曰:『吾龍樹也,所居淨土,以汝有淨土之心,故來見汝。』……既於念佛一法,直被聖訓,所解之義,示非臆說故。三.令知「二道」教相,天親亦立故。四.彰二經有「二道」微旨,故謂世親本於三部,制於一論,密彰「佛願易行」微旨故。五.解主依憑師故,未入念佛之前,憲章「四論」,祖述龍樹;入念佛門,亦師龍樹<贊彌陀偈>[4],別造<龍樹贊>,崇重鄭寧,慎終如始,故茲憑之。六示所勸法門,是大非小故。龍樹本是「大乘」菩薩,所弘「念佛」是極大乘故。
[5] 「八宗共祖」?中國傳統哲學所蘊涵的和諧、合一思想,再與佛教如來藏思想合流,確立中國佛學的思想基調,而與龍樹的「緣起性空」有所歧出(亦是一種「創新」、「創造」)。此時龍樹「八宗共祖」之稱譽,對中國佛教而言恐流於「敬而遠之」的尊號,只是形式上的宣稱而未必是實質上的繼承。萬金川表示:「雖然在漢地佛教的傳統裡,龍樹被尊為八宗共祖,地位極其崇高;……中國佛教史上,除鳩摩羅什及其門弟所弘傳的關河舊學之外,事實上並無專肆弘揚龍樹思想的學派,……除《中論》、《大智度論》與《十二門論》外,漢地學者幾乎全然無視於龍樹的其他著作。」
[6]行大乘者,佛如是說:「發願求佛道,重於舉三千大千世界。」汝言:「阿惟越致地,是法甚難,久乃可得,若有易行道,疾得至阿惟越致地」者,是乃怯弱下劣之言,非是大人志幹之說!汝若必欲聞此方便,今當說之。……陸道步行則苦,水道乘船則樂。菩薩道亦如是:或有勤行精進,或有以信方便易行疾至阿惟越致者。……若人疾欲至,不退轉地者,應以恭敬心,執持稱名號。若菩薩欲於此身,得至阿惟越致地,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應當念是十方諸佛,稱其名號。
[7] 知空《翼解》云:《彌勒問經論》云:「自分堅固,名不退;勝進不壞,名不轉。」《起信疏》云:「不退有三:一信行未備,未得不退,以無退緣,名不退;二信位滿,入十住,得少分法身,名不退;三賢位滿,入初地以去,證遍滿法身,名不退。」又《妙宗鈔》云:「不退有三:若破見思,名位不退,則永不失超凡之位;伏斷塵沙,名行不退,則永不失菩薩之行;若破無明,名念不退,則永不失中道正念。」又慈照宗主云:「未斷煩惱,生同居土,為願不退;破見思,生方便土,為行不退;破塵沙,分破無明,生實報土,為智不退;破三惑盡,生寂光土,為位不退。今依彼論是初地以上之不退也。
[8] 此處雖不言「末法」之時,其後道綽師則特重「約時被機」,以中國帝王之毀佛/滅法為「末法」具體現實。
[9] 劫濁乃由「見--煩惱--眾生--命」四濁所成;或即是修道所應斷之「見-思-塵沙-無明」四惑。
[11]《大乘起信論.疏記.會閱》:「二義更互用之,隱顯相成,如綺之文。」《服宗記》引《止觀》二之三云:依《智論》立根(利鈍)障(輕重)四句。……第三〈調伏心品〉云:問:何等法失菩提心?答曰:「1、不敬重法,2、有憍慢心,3、妄語無實,4、不敬知識。」此中前三根劣,後一緣薄。天台智者《法華文句》卷四上:根有利鈍者,皆論大乘根性;惑有厚薄者,約別惑為言耳,即為四句:一、惑輕根利;二、惑重根利;三、惑輕根鈍;四、惑重根鈍。若別惑輕、大根利,初聞即悟;若惑重根利,再聞方曉;若惑輕根鈍,三聞乃決;第四句,雖復三聞,不能得悟,止為結緣眾耳。或可初兩句根利同為上根,或可中間兩句為中下根。
[12] 詳見象山慶< 《安樂集》之說/聽方軌-教赴「時/機」>
[13] 《瑜伽師地論》卷48:菩薩如是於諸有情,六種攝受,無倒轉時,當知遭遇略十二種艱難之事。聰叡菩薩,於彼十二艱難之事,當正覺了。1.於多安住違犯有情,若罰若捨。2.於惡有情,為調伏故;方便現行辛楚加行,防自意樂,不生煩惱。3.現可施物,極為鮮少;現來求者,其數彌多。4.唯有一身,眾多有情種種事業,並現在前,同時來請共為助伴。5.居放逸處,若住世間可愛妙定,若生天上樂世界中。令心調善。6.常求遍作利有情事,而於此事,無力無能。7.於其愚癡諂詐剛強諸有情所,若為說法,若復棄捨。8.常於生死,見大過失;為度有情,而不棄捨。9.未證清淨增上意樂,多分慮恐失念命終。10.未證清淨增上意樂,他來求乞第一最勝所可愛物。11.種種異見種種勝解諸有情類,若別教誨,若總棄捨。12.常行最極不放逸行,而不應斷一切煩惱。……若諸菩薩,遭遇如是諸艱難事;或於其中,應觀輕重,如其所應,而作方便。
[14]《寶女所問經》卷四/大乘品:行大乘者,有三十二掛礙塹路,以此塹故,不疾得成諸通之慧。1.樂聲聞乘,2.志緣覺乘,3.求釋梵處,4.倚著所生淨修梵行,5.專一德本言是我所,6.若得財寶慳貪愛吝,7.以偏党心而施眾生,8.輕易戒禁,9.不念道心專精之行,10.嗔恚之事以為名聞,11.其心廢逸,12.而心馳騁,13.不求博聞,14.不察所造,15.貢高自大,16.不能清淨身口心行,17.不護正法,18.背舍師恩,19.棄捨四恩,20.離堅要法,21.習諸惡友,22.隨諸陰種,23.不勸助道,24.念不善本,25.所發道意無權方便,26.不以殷勤諮嗟三寶,27.憎諸菩薩,28.所未聞法聞之誹謗,29.不覺魔事,30.習恃俗典,31.不肯勸化于眾生類,32.厭於生死。
[15]不敬重法,有憍慢心,妄語無實,不敬知識…… 【吝】惜最要法,貪樂於小乘,謗毀諸菩薩,輕賤坐禪者……不覺諸魔事,菩提心劣弱,業障及法障……許施師而誑,人無有疑悔強令生疑悔,信樂大乘者深加重瞋恚,於諸共事中心多行諂曲……
[17] 第二大門:(《大經》云)「凡欲往生淨土,要須發菩提心為源。」……(《涅槃經》云)「若有眾生,於熙連半恒河沙等諸佛所,發菩提心,然後乃能於惡世中,聞是大乘經典,不生誹謗;……若有於三恒河沙等佛所,發菩提心,然後乃能於惡世中,不謗是法,書寫經卷,雖為人說,未解深義。』」(第五大門)汎明修道延促者,……一切眾生,莫不厭苦求樂,畏縛求解,皆欲早證無上菩提者,先須發菩提心為首。此心難識難起,縱令發得此心,依經終須修十種行,謂信、進、念、戒、定、慧、捨、護法、發願、迴向,進詣菩提。然修道之身,相續不絕,逕一萬劫,始證不退位。……當今凡夫,現名信想輕毛,亦曰假名,亦名不定聚,亦名外凡夫,未出火宅。……以一劫之中,受身生死,尚不可數知;況一萬劫中,徒受痛燒。……(《俱舍釋論》卷九)說云:「於三大阿僧祇劫,一一劫中,皆具福智資糧,六波羅密,一切諸行。一一行業,皆有百萬難行之道,始充一位。」是難行道也。
[18] 雖說二種,其實唯一,即「心外求法」,因「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故心外無法,這是佛教出世間不共之特見;其他宗教所不能證、不能及,誤以為心識之外,別有境界(外法)實在,故徒然向外攀緣、執取也。
[19] 「外道」者,此有二義:一、外之道,《維摩義記》云:「法外妄解。」二、外於道,《三論玄義》云:「心遊道外。」言「相善」者,有相之善。「菩薩法」者,《十住論》四云:「信樂深妙法者,深法者,空.無相.無願,及諸深經,如般若波羅蜜,菩薩等於此法.一念信樂,無所疑惑」等,又云「菩薩不得我,亦不得眾生,不分別說法,亦不得菩提,不以相見佛,以此五功德,得名大菩薩,成阿惟越致。」當知菩薩苟取相者,亂失其法。
[20] 心行理外,唯修邪因,是名外道;斷/常邪解,不知寂滅,故曰相善。六師、九十六種,及此方儒/老等也。廣教澄彧[20]云:「我佛正法,小乘即有無常、無我、寂滅法印,大乘則有一實相印,依之行,必登聖果。
[21] 「如彼修六行觀[21],外道、菩薩,所期不克,而行相稍同,故云亂法也。」此云「六行」,或乃六波羅蜜,或以有漏智,次第斷除修惑之際,所修「厭下欣上」之觀法。三界分為九地,比較上地與下地,下地為粗、苦、障,故觀而厭之;上地為靜、妙、離,故觀而欣之。依此欣上厭下之力,可次第斷除下地之惑,故又稱「厭欣」觀。
[22]在世不遇佛、不聞佛法之八種障難,衍生為求證佛法的障礙:地獄、餓鬼、畜生、北俱盧洲、長壽天、聾盲瘖啞、世智辯聰、佛前佛後。
[23] 《大般若經》卷557:今此眾多外道梵志,來趣法會,伺求佛短,將非般若留難事耶?……爾時,惡魔竊作是念:「今佛四眾前後圍遶,欲、色界天皆來集會,宣說般若波羅蜜多。此中定有諸大菩薩親於佛前受菩提記,當得無上正等菩提,轉妙法輪空我境界,我當往至破壞其眼。」作是念已,化作四軍奮威勇銳來詣佛所。時,天帝釋見已,念言:「將非惡魔化作斯事,欲來惱佛,并與般若波羅蜜多而作留難。…….惡魔長夜伺求佛短,壞諸有情所修善業。
[25] 《十住論》四云:「二乘所得,於佛(乘)為下耳。但出世間,入無餘涅槃…….」又〈易行品〉云:「若墮聲聞地,及辟支佛地,是名菩薩死,則失一切利。…….若墮二乘地,畢竟遮佛道。」
[26] 聞佛教音而入聖道,是曰聲聞。…………《大集》十九經云:「有二種人,畢竟不能報如來恩,一者聲聞,二者緣覺,……墮解脫坑,不能自利,及以利他。」
[28]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三慧品〉說:「一切智」是聲聞、辟支佛智,「道種智」是菩薩摩訶薩智,「一切種智」是諸佛智。依《瑜伽師地論》、《顯揚聖教論》說明,解脫道的一切智,含攝了十智:世俗智、法智、類智、苦諦智、苦集諦智、苦滅諦智、苦滅道諦智、知他心智、盡智、無生智。
[29] 以受眾多生死,故名為「眾生」者,此是小乘家釋三界中眾生名義,……大乘家所言「眾生」者,如《不增不減經》言「言眾生者,即是不生不滅義」,何以故?若有生,生已復生,有無窮過故,有不生而生過故,是故無生。若有生,可有滅;既無生,何得有滅?
[30] 《法華經方便品》 (釋尊曰):「諸佛智慧,甚深無量,其智慧門,難解難入,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五千人等,即從座起,禮佛而退。佛陀未制止,默言任去:「此輩罪根深重,及增上慢,未得謂得,未證謂證,有如此失,是以不住」。
[31] <無著菩薩傳>云:「猶如焦芽與敗種,天雖降雨不生芽,若無賢善與福德,諸佛雖臨有何益。」《十住毘婆沙論》卷1:問曰:三乘所學皆為「無餘」涅槃,若無餘涅槃中無差別者,我等何用於恒河沙等大劫,往來生死具足十地,不如以聲聞/辟支佛乘,速滅諸苦。答曰:是語弱劣,非是大悲有益之言。若諸菩薩効汝小心,無慈悲意,不能精勤修十地者,諸聲/聞辟支佛,何由得度?亦復無有三乘差別,所以者何?一切聲聞/辟支佛,皆由佛出,……若不修十地,何有諸佛?若無諸佛,亦無法僧。……(自/他)共利者,能行慈悲饒益於他,名為上人。」
[32] 《大智度論》卷十云:七住(地)菩薩(入理般若為住,住生功德為地)觀諸法空無所有、不生不滅。如是觀已,於一切世界,中心不著,欲放捨六波羅蜜,入涅槃。
[33] 《大智度論》:卷15:菩薩於諸煩惱中,應當修忍,不應斷結。何以故?若斷結者,所失甚多,墮阿羅漢道中,與根敗無異。……菩薩心有智力,能斷結使,為眾生故,久住世間,知結使是賊,是故忍而不隨。菩薩繫此結賊,不令縱逸而行功德。卷27:菩薩得無生法忍,煩惱已盡,習氣未除故,因習氣受、及法性生身能自在化生;有大慈悲為眾生故,亦為滿本願故,還來世間,具足成就餘殘佛法故,十地滿,坐道場,以無礙解脫力故,得一切智、一切種智,斷煩惱習。卷28:諸聖人愛糠已脫故,雖有有漏業生因緣,不應得生。……菩薩入法位,住阿鞞跋致地,末後肉身,盡得法性生身,雖斷諸煩惱,有煩惱習因緣故,受法性生身,非三界生也。釋悟耿<《大智度論》中「無生法忍」之初探>
[34] 亦有對此起疑者,《大智度論》:「問曰:阿羅漢煩惱已盡,習亦未盡,何以不生?答曰:阿羅漢無大慈悲,無本誓願度一切眾生,又以實際作證,已離生死故。」二乘人雖已斷現行(煩惱)而未盡斷習氣,有如第二類菩薩;但因其聲聞性於一切眾生無「大悲」、無「本願」,故直證涅槃,而不願潤生死,回三界。
[35] 《大智度論》卷十:菩薩亦如是,立七住中,得無生法忍,心行皆止,欲入涅槃。爾時十方諸佛,皆放光明,照菩薩身,以右手摩其頭,語言:「善男子,勿生此心,汝當念汝本願,欲度眾生。汝雖知空,眾生不解,汝當集諸功德,教化眾生,莫入涅槃。汝未得金色身、三十二相、八十種隨形好、無量光明三十二業。汝今始得一無生法門,莫便大喜。」是時菩薩,聞諸佛教誨,還生本心,行六波羅蜜,以度眾生。也有說沉空之難是「第八地」:《成唯識論述記》十本釋曰:「前八地中,得無相樂,耽著寂滅,不肯進修(利他),諸佛七勸,方能進趣,故唯自利;九地之障,四無礙解,利他法故。」第八不動地菩薩,若欲登第九善慧地,必先斷此障礙。
[37] 力所不及、性不相應,故不可思議
[38] 若佛子,心背大乘常住經律,言非佛說;而受持二乘聲聞、外道惡見,一切禁戒邪見經律者……以惡心、瞋心,橫教二乘聲聞經律、外道邪見論等,……而捨七寶,反學邪見、二乘、外道、俗典、阿毗曇、雜論、一切書記,是斷佛性,障道因緣,非行菩薩道者。
這幾種「輕垢罪」之觸犯,所提及的外道、聲聞、邪見、戒禁取、惡心(橫教),與鸞祖「五難」前四種相似,若自犯或教人犯,都成了「斷佛性、障菩薩道」的因緣,若不能如法懺悔,將受惡報,又豈得不退轉於成佛之道?
[39] 《首楞嚴經.拾遺》卷九:識性不動,以滅窮研。於無盡中,發宣盡性,如存不存,若盡非盡,如是一類,名為非想非非想處,此等窮空,不盡空理;從不還天「聖道」窮者,如是一類,名不迴心鈍阿羅漢。若從無想諸外道天,窮空不歸,迷漏無聞,便入輪轉。
[40] 五「無心」位之一:念想滅盡,僅存色身及不相應行蘊,乃外道婆羅門之最高涅槃;亦為異生凡夫以「出離想」修定所感之異熟果報。凡夫與外道以其如存不存乃「非想」,若盡非盡乃「非非想」。……彼等落於偏空--於「有」之外求「空」,偏空滯寂,……從無想天(諸外道天),欣上厭下,窮空不歸,而入四空天,乃至非想非非想天。因以有漏道修(其本迷此「有漏」天,作「無為」解),無多聞慧故,八萬大劫報盡(受報已滿,無所歸託),還墮入於輪迴。
[42] 《十住論》四云:「心不端直者,其性諂曲,喜行欺誑」等是也。「無顧」者,《大經》云「無義無禮,無所顧難。」又《十住論》六云:「諸有惡眾生,種種加惱事,諂曲懷憍逸,惡罵輕欺誑,背恩無反覆,癡弊難開化;菩薩心湣傷,勇猛加精進。」此是無顧惡人相也。「破他勝德」者,此有二意,一云:彼直加惱害,如次上文。二云:由彼弊惡,菩薩失大慈悲,如乞眼緣。
[43] 《唯識論》云:「無慚不顧自法,無愧不顧世間,不顧自他,放逸邪侈,故曰惡人。」「他」指菩薩;勝德者,指上無相善、大慈悲之二,是寂/照之二,悲/智之雙,自/他二利之德;定/慧二行之義,不外此二,故曰勝德也。
[44] 此處所舉「如乞眼緣」,出自《大智度論》卷12:如舍利弗於六十劫中行菩薩道,欲渡「布施」河。時有乞人,來乞其眼,……爾時,舍利弗出一眼與之,乞者得眼,於舍利弗前,嗅之嫌臭,唾而棄地,又以腳蹋。舍利弗思惟言:「如此弊人等,難可度也!眼實無用,而強索之,既得而棄,又以腳蹋,何弊之甚!如此人輩,不可度也。不如自調,早脫生死。」思惟是已,於菩薩道退,迴向小乘……。這就是由無顧惡人之強索其眼又唾棄之,如此無端的侮辱,致令舍利弗「失大慈悲」,退失菩薩道而墮於二乘案,依《大智度論》原文,舍利弗只挖一眼而被嫌棄就退墮,另網路上流傳較廣的,是在原有故事上發揮、增添,編造了「挖兩眼」的情節,多有不合情理之處。如星雲法師《十大弟子傳》的那個版本。
[45] 《大智度論》卷34:有人生值佛世,在佛法中,或墮地獄者,如提婆達、俱迦利、訶多釋子等。三不善法覆心,故墮地獄。上已說有二種佛:一者、法性生身佛,二者、隨眾生優劣現化佛。為法性生身佛故,說「乃至聞名得度」;為隨眾生現身佛故,說「雖共佛住,隨業因緣,有墮地獄者」。法性生身佛者,無事不濟、無願不滿。所以者何?於無量阿僧祇劫積集一切善本功德,一切智慧無礙具足,為眾聖主,諸天及大菩薩希能見者。譬如如意寶珠難見、難得,若有見者,所願必果。釋迦文佛本誓:「我出惡世,欲以道法度脫眾生,不為富貴世樂故出。」1.若佛以力與之,則無事不能。又亦是2.眾生福德力薄、罪垢深重故,不得隨意度脫。又今佛但說清淨涅槃,而眾生譏論誹謗言:「何以多畜弟子,化導人民?此亦是繫縛法。」但以涅槃法化,猶尚譏謗,何況雜以世樂!
[46] 《大智度論》卷15:如一比丘,於此十四難思惟觀察,不能通達,心不能忍;持衣缽至佛所,白佛言:「佛能為我解此十四難,使我意了者,當作弟子;若不能解,我當更求餘道!」……佛言:「汝癡人今何以言:『若不答我,不作弟子?』我為老、病、死人說法濟度;此十四難是鬪諍法,於法無益,但是戲論,何用問為?若為汝答,汝心不了,至死不解,不能得脫生、老、病、死。……不欲出箭方,欲求盡世間常、無常,邊、無邊等,求之未得,則失慧命,與畜生同死,自投黑闇!」比丘慚愧,深識佛語,即得阿羅漢道。
[47] 《法華玄讚》一:「佛有三子:一善星,二優婆摩耶,三羅睺。」
[48] 《涅槃經》33:我于往昔初出家時,吾弟難陀、從弟阿難、調婆達多、子羅睺羅,如是等輩,皆悉隨我出家修道。我若不聽善星出家,其人次當得紹王位,其力自在,當壞佛法。……善星比丘若不出家,亦斷善根,於無量世,都無利益。今出家已,雖斷善根,能受持戒,供養恭敬耆舊長宿有德之人,修習初禪,乃至四禪,是名善因。……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我不聽善星比丘出家受戒,則不得稱我為如來,具足十力。其惡行之緣由與事蹟,如下:出家之後,受持讀誦,分別解說十二部經,壞欲界結,獲得四禪。……不解一偈一句一字之義,親近惡友,退失四禪。……生惡邪見,作如是言:「無佛無法,無有涅槃。」親對我前,聞我說法,見我經行,見我端坐,見我神足遊處虛空,見我降伏多千外道,於大眾中,摧彼邪法。如是等人,尚於我所,不生信樂,於步步間,恒欲毀我;由是步步,漸增其惡。于同行中,自謂為勝,是故親近同己惡友。既親近已,復得更聞「不具足」法;聞已心喜,其心染著,起於驕慢,多行放逸;因放逸故,親近在家,亦樂聞說在家之事,遠離清淨出家之法。以是因緣,增長惡法,增惡法故,身口意等,起不淨業,三業不淨故,增長地獄、畜生、餓鬼。
[49] 佛陀歎言:譬如有人,沒圊廁中,有善知識,以手撓之。……久求不得,爾乃息意。我亦如是,求覓善星微少善根,便欲拔濟。終日求之,乃至不得如毛髮許,是故不得拔其地獄。
[50] 廝下,地位低賤
[51] 前引《大智度論》卷34云:如提婆達欲令足下有千輻相輪故,以鐵作模燒而爍之,爍已,足壞,身惱大呼。爾時阿難聞已涕泣白佛:「我兄欲死,願佛哀救!」佛即伸手就摩其身,……提婆達眾痛即除;執手觀之,知是佛手,便作是言:「淨飯王子以此醫術足自生活。」佛告阿難:「汝觀提婆達不?用心如是,云何可度?」關於提婆達多宿世「因緣果報」之詳情,可參閱《觀經四貼疏》之象山慶相關論述。
[52] 《雜寶藏經》28<仇伽離謗舍利弗等緣>:昔有尊者舍利弗、目連,遊諸聚落,到瓦師所,值天大雨,即於中宿。會值窰中先時有一牧牛之女,在後深處,……見舍利弗、目連其容端政,心中惑著,便失不淨。尊者舍利弗、目連,從瓦窰出。仇伽離……不知彼女自生惑著而失不淨,即便謗言:「尊者舍利弗、目連,婬牧牛女。」向諸比丘,廣說是事。時諸比丘,即便三諫…..,佛復諫言:「汝莫說是舍利弗、目連是事。」聞佛此語,倍生瞋恚,時惡疱瘡轉大如柰。第二又以此事,而白於佛,佛復諫言:「莫說此事。」疱瘡轉大如拳,第三不止,其疱轉大如瓠,……即時命終,墮摩訶優波地獄。《大智度論》卷13:復有人雖不貪恚,而妄證人罪,心謂實爾,死墮地獄。如提婆達多弟子俱伽離,常求舍利弗、目揵連過失。……先懷嫉妬,既見此事,遍諸城邑聚落告之;次到祇洹唱此惡聲。……佛告俱伽離:「舍利弗、目揵連心淨柔軟,汝莫謗之,而長夜受苦!」……佛如是三呵,俱伽離亦三不受,即從坐起而去。還其房中,舉身生瘡,始如芥子,漸大如豆、如棗、如,轉大如苽,翕然爛壞,如大火燒,叫喚嘷哭,其夜即死,入大蓮華地獄。
[53] 《六方禮經》:惡知識有四輩。一者內有怨心,外強為知識。二者於人前好言語,背後說言惡。三者有急時,於人前愁苦,背後歡喜。四者外如親厚,內興怨謀。《正法念處經》云:「惡知識者,是貪瞋癡之所住處。……猶如毒樹。」。《大般涅槃經》也說:「惡象等唯能壞身,不能壞心。惡知識者,二俱壞故。」毒樹與惡象不過損人身命,惡知識甚至斷人慧命。《雜譬喻經》:「譬如賊師造惡逆,殺害君父,破亂天下,眾生被毒,殃無不加,與之從事,令人得大罪。」
[54]想倒,於六塵之境而思想非理;見倒,於事理之法而邪計推求者(邪見);心倒,於妄心邪識了事物,是諸顛倒之根本。《涅槃經》37:「如來己離三種顛倒,所謂想倒,見倒,心倒。」《宗鏡錄》42:「心如停賊主人,見是賊身,想如賊腳,根塵是賊媒,內外搆速,劫盡家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