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破舊的剪貼簿,承載著超過半個世紀的歲月,半世紀前隨我飄洋過海來到多倫多,它不僅是一件舊物,更是我青春的縮影,珍藏著那個年代特有的記憶與情感。
回首1960年代的台灣,軍公教家庭普遍生活清苦,父親在台灣大學任教,獨力負擔三名子女就讀私立大學的龐大學費,身為學生,我哪裡有餘錢去重慶南路的書店買書?
那時家中訂閱《中央日報》和《大華晚報》,每當讀到喜愛的文章,我總會小心翼翼地剪下,貼入這本珍貴的剪貼簿,那個年代,家家戶戶都會將看過的舊報紙論斤賣給菜市場攤販當包裝紙,為此,菜市場攤販還向我老媽抱怨,說我們家的報紙全都是千瘡百孔,根本無法使用,他們或許無從知曉,那些破洞的背後,是我對文字深深的熱愛與執著。
60年代,我曾多次參加救國團舉辦的青年活動,活動結束後,仍與幾位隊友保持通信,即使分屬不同學校,信中我們仍以「某某同學」相稱,與西人社會西人直呼其名的習慣截然不同,其中一位是就讀法商學院的徐同學,我們偶爾通信,他出國前還曾來我家拜訪,之後便失去聯繫。
直到1967年,他在《中央日報》發表了一篇名為「情祭」的文章,字裡行間訴說他與交往三年的女友,在服兵役期間,女方先他一步出國,最終嫁作他人婦的心路歷程,那是一篇血淚交織的文字,寫盡一段愛情的無奈與傷痛,我將這篇「情祭」剪下,貼進剪貼簿中,成為一段青春歲月最深刻的見證。
令人驚奇的是,最近一位住在洛杉磯的朋友,剛搬進當地一處退休社區,沒想到徐同學竟是該社區華人協會的會長!我得知後,立刻將剪貼簿裡的「情祭」拍照寄給朋友,她轉交給徐同學,徐同學驚訝地說,當年他自己並未保留那篇文章,萬萬沒想到,時隔五十八年,他竟能從我處重讀那段塵封的文字——這段久違的交會,令人感慨萬千。
剪貼簿中還收藏了雨僧的兩篇文章——「心燈」與「飄得一身落葉」,命運再一次安排了驚奇:2012年11月,我在 UDN 部落格註冊帳號,無意間瞥見「雨僧」這個熟悉的筆名——她可是60年代深受歡迎的女作家啊!當下立刻去她的部落格留言並將剪貼簿中的文章掃描寄給她。她回信說:「一枚風箏可以飛得這麼多年,又這麼遙遠」,她的女兒也在臉書分享這段奇遇:
「我媽媽在1970年代中期移民美國之前,是台北的一名記者,2005年,她的筆被換成了筆記型電腦和部落格,因為這個部落格,一位來自多倫多的讀者找到了我媽媽,並用電子郵件寄給她二篇她大約40年前寫的短篇小說的掃描報紙剪報,太神奇了!」
是啊,真是太神奇了,這些看似平凡的舊文章,歷經數十年後,竟能跨越時空與地域,再次串起人與人之間的連結與回憶。
這本剪貼簿所珍藏的,不只是報紙剪影與紙上文字,更是時光的印記、情感的溫度,以及無數偶然與必然交織而成的生命故事,它靜靜躺在書櫃中半個世紀,沒想到,如今竟能激起這麼多意想不到的漣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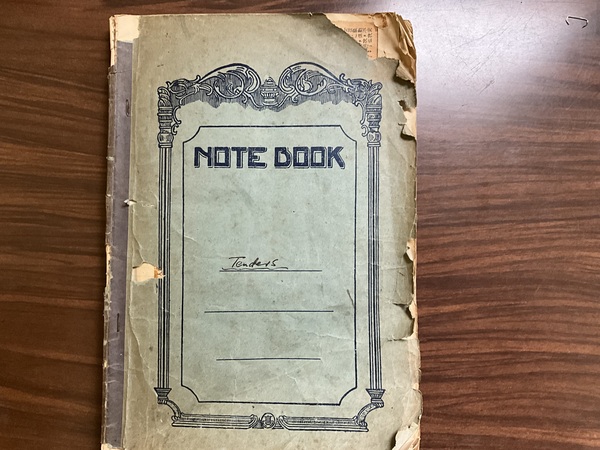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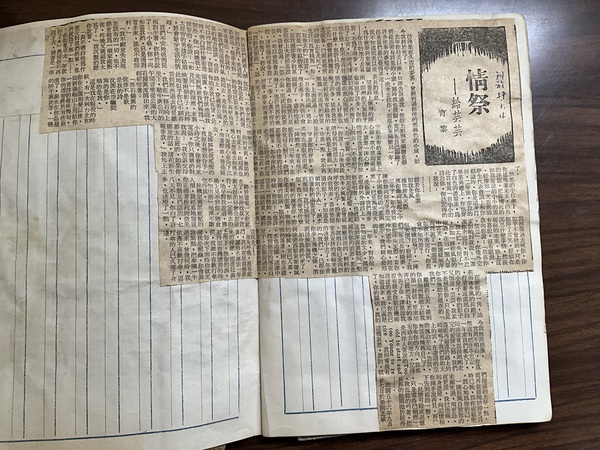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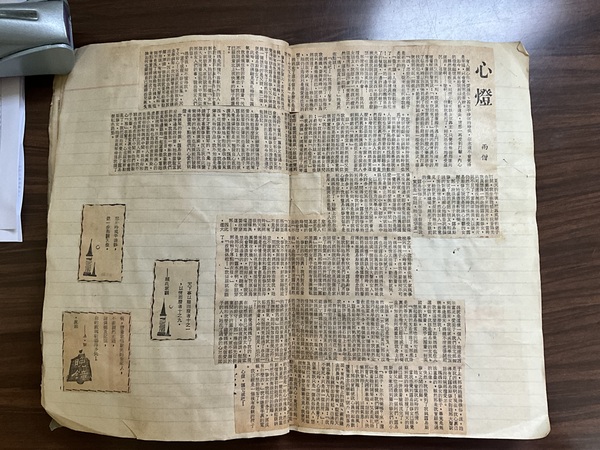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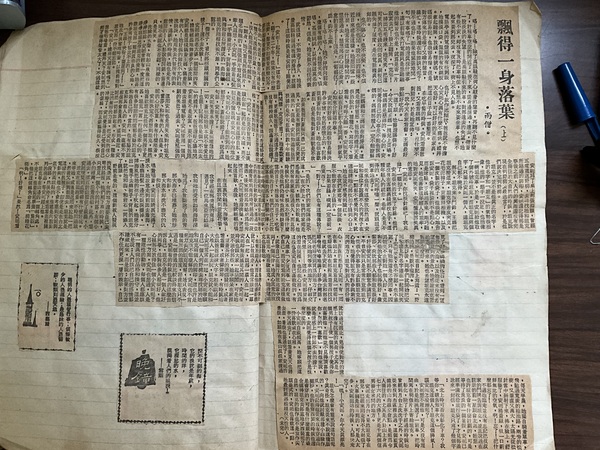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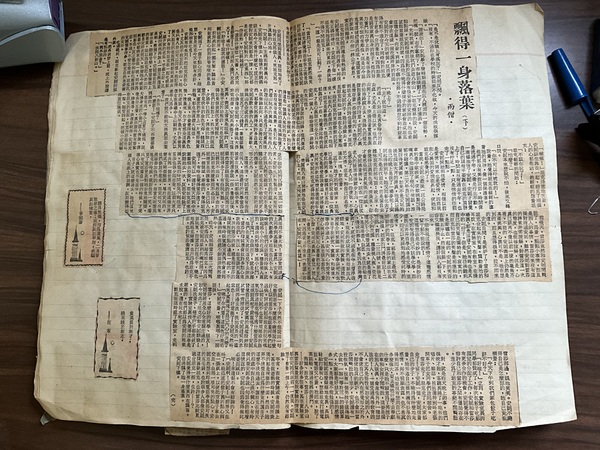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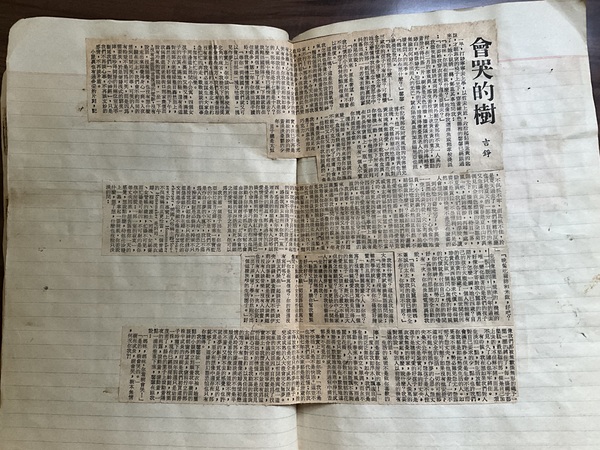
原文刊登於2025年8月1日美國世界日報 上下古今版
- 9樓. 異鄉芝麻事-洛城的居家生活2025/12/27 03:55很棒也很特別的記憶!年輕時也會一點剪貼, 但早已不知去向.
- 8樓. 四妹2025/11/08 13:42一張張剪報飄洋過海還能找到原作者,實在是神奇又令人感動
 沒錯!真的很神奇! 解曼曼 於 2025/11/08 23:07回覆
沒錯!真的很神奇! 解曼曼 於 2025/11/08 23:07回覆 - 7樓. Hegel2025/10/18 06:21
我年輕時也參加很多寒暑假的活動,除了認識能交往的朋友外,也認識幾位有才氣的作家,不過早早就沒有聯絡。中學時期也剪貼,主要是好文章,用來學習中文,也都失落在人生的遷徙中。特別遺憾的是,大學好友張X綱,他出國後去了洛杉磯,我唸完書回台灣後還曾去洛杉磯看過他,如今失聯,找了很久都無果。
你的剪貼簿能保存那麼久,又還能跟被收集的人聯絡上,真是驚喜。而我,最近在收拾台灣的家,要清除所有的東西,準備結束,那些生命的痕跡,一件一件,是如此的讓我不捨。
年輕時,我參加過青年救國團舉辦的各種活動——戰鬥文藝營、金山研習會、新聞研協會等等,那時一心一意想當編輯或記者,結果卻在加拿大做了一輩子的Accountant。
我對家具、家電、日用品、衣物從不留戀(舊的不去、新的不來),但對相片、信件,還有朋友出國旅遊時帶回來那些並不值錢的小禮物,卻珍藏如寶,就是不捨得丟,沒辦法,我就是這麼念舊。
你住在Calgary嗎?我家大兒子在那裡住了10年,現在我老妹住在那兒。那裡的洛磯山脈真是百看不膩,美得令人難忘。
解曼曼 於 2025/10/18 22:15回覆新聞研習會 解曼曼 於 2025/10/19 01:31回覆 - 6樓. 花露露2025/10/02 01:13心有戚戚焉
我也有剪貼的愛好,也有好幾本剪貼簿,都有經過歲月洗禮的樣貌和色澤。
哪天我也來敘述一下剪貼的心路歷程!
哇!你也有好幾本剪貼簿啊!那一定充滿故事,好期待你哪天也來分享,一定能引起更多共鳴! 解曼曼 於 2025/10/04 07:03回覆 - 5樓. samia2025/09/30 10:07我第一次寫文章被聯合報副刊登出,可惜沒有剪報保留
1972年我被派往西非的「象牙海岸共和國」擔任水利技師,我曾寫了一篇文章「我在非洲的體驗」被聯合報副刊登出,那時我在非洲,不但在台灣的朋友寫信告訴我,連在美國的朋友也告知此事,可惜我沒有剪報的習慣,那篇文章以後再也找不到了。那是一段很特別的經歷呢!在那個年代,能在聯合報副刊發表文章是很不容易的事,雖然剪報沒留,但這份回憶一直在您心中,也是一種珍藏,也許有機會可以試試聯合報的數位資料,說不定還能找到那篇作品呢! 解曼曼 於 2025/10/03 22:05回覆 - 4樓. 府城古意廣衡藝術郭老師2025/09/29 23:13讚讚好好的!
 感謝您與我都有欣賞了也有按讚了
感謝您與我都有欣賞了也有按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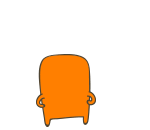 謝謝來訪、留言、按讚。 解曼曼 於 2025/10/03 21:59回覆
謝謝來訪、留言、按讚。 解曼曼 於 2025/10/03 21:59回覆 - 3樓. vivi 之東張西望2025/09/28 22:07
真是讓人感動的初衷與際遇;
也想起好久不再想起的剪貼簿,
滿心溫馨美好的回憶
- 2樓. king wang2025/09/25 22:12
曼曼文友:
細細讀完您這篇關於剪貼簿的文章,內心充滿了溫暖與感動。謝謝您用如此真摯的筆觸,與我們分享這段承載了半世紀光陰的珍貴記憶。
您筆下那個剪報紙的青春歲月,瞬間將我帶回了那個物質雖不豐裕,但精神卻無比飽滿的年代。您母親被菜市場攤販抱怨「報紙千瘡百孔」的趣事,是如此生動傳神,那每一個破洞,都是您對文學熱愛的最純粹證明,閃閃發光。
而故事中最令人驚嘆的,莫過於兩段跨越時空的重逢。想像徐同學在五十八年後,重讀自己青年時代的「情祭」,那一刻的震撼與感慨,該是何等深邃!您不僅是位珍藏者,更是緣分的橋樑,讓失落的過往得以完整。而與作家雨僧的相遇,更是命運最美的安排之一,證明瞭真摯的文字如同風箏,線頭始終握在有心人的手中,無論飛得多遠、多久,總有收線重逢的一天。
這本靜臥書櫃半世紀的剪貼簿,如今激盪起如此美妙的漣漪,恰恰說明了:我們當下珍愛的人、事、物,所付出的熱情與真心,都可能在不遠的未來,或是在遙遠的他方,結下意想不到的善果。它不僅是您的青春縮影,更是一則關於記憶、緣分與文學永恆價值的優美寓言。
再次感謝您的分享。祝您在多倫多一切安好,願這本充滿魔力的剪貼簿,繼續為您帶來更多生命的驚喜。
非常謝謝您花時間細細讀完我的文章,還寫下這麼用心的留言,讓我覺得很感動。
也謝謝您給我的鼓勵,讓我覺得寫這些回憶是有意義的,希望以後還能和您繼續在這裡分享彼此的故事。
解曼曼 於 2025/09/26 20:49回覆 - 1樓. 寧靜姐2025/09/25 15:58哇,存放這麼久!是啊!就是捨不得扔掉! 解曼曼 於 2025/09/26 20:40回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