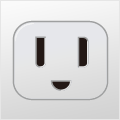撇撇嘴,她一揚水袖。
「我就說這些腐儒的腦袋只裝滿了書蠹蟲,妳偏不信。」
指著我手裡白紙黑字,她扠起腰,柳眉倒豎。
「這些臭酸書生,只把咱們當會唱歌跳舞的畜牲用。承平時候曉得上咱這兒來狎妓飲酒,自命風流的大筆幾張花箋,就以為搖身變作大文士了;每逢戰事一起,個個逃得忒快,誰管咱們死活,等到沒了國家、沒了銀兩,倒轉過頭怨起咱們沒節操。」
背過身,她冷哼一聲,攬著水絲花帶的腰枝妖嬈。
「誠心餵上野狗幾個肉包子,有難來時牠還懂得替妳吠幾聲;誠心供這些敗壞國家的廢柴玩樂,他不懂得羞恥自己無能,還要說妳不知亡國恨哩!」
走遠了,她的冷笑與甜聲還掛在我樑上垂啊垂的,像一折元曲的段子。
「男人啊男人,騙自己也騙別人,嘴裡什麼宏圖大業,不過都是勝者的自我催眠,敗者的自我安慰罷了~」
笑一笑,繼續埋首紙堆。
而這夜尚久尚長,如歷史的翻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