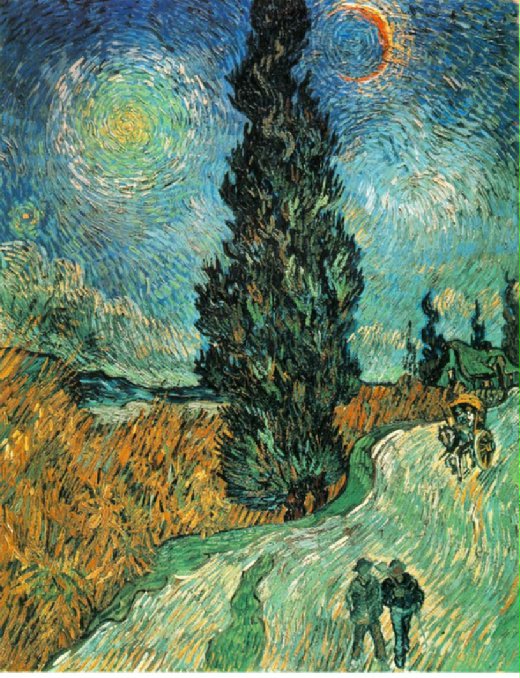
過去一、兩年是台灣經濟發展以來最艱困的一段期間。行政院林副院長信義在經濟部長任內曾說苦日子來了。如何才能讓台灣經濟再起飛?加強公司治理(corporategovernance)是一個必要的藥方。 公司治理是指如何透過市場機制與法律規範等制度因素,提升公司的營運績效與股東價值。在過去30年以來,北美、歐洲、日本都是此一課題所探討的熱門領域。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東亞公司治理問題也成為國際組織關切的問題。OECD也順勢地推出「公司治理原則」,以供已開發與新興國家參考。 在「恩龍」 (Enron)案件發出後舉世又有一波討論公司治理的浪潮。我國因為總體經濟的管理較健全,中小企業反應敏捷,避開了亞洲金融危機。不過,前幾年地雷股事件迭起,再加以我國與東亞各國一般,上市櫃公司都有股權過於集中、散戶短線操作的問題,金融體系不良貸款債權日益攀高,因此也有公司治理的問題。主管機關如證期會在近年也已開始重視此一議題,除了已要求加強獨立董監事的規定以外,未來還會要求各上市櫃公司制訂「公司治理最佳實務準則」,希望藉此改進企業體質,增進國家競爭力。 目前國內談論公司治理以及有關措施,比較以制訂行政規章以及加強行政監理為主。這是正確的方向,但太為侷限。從外國的經驗來看,必須要注意到下列幾個面向: 一、政企關係:政府是否介入產業、介入資本與信用市場?或是尊重市場機制,鼓勵企業優勝劣退?譬如近幾年政府國安基金、四大基金介入股市,不但業績不好,還造成政企不分的隱憂,大賣台積電的ADR也造成其股價下滑。希望國安基金以及其他干預性的機制儘早廢止。 二、金融體制與公司法規:金融體制是否能真正地保護存款人?公司法制是否能真正保障股東權益,又予企業募資的便利,以降低資金成本?從公司法大幅修正、金融六法以及企業併購法的制訂,可見我國已經開始財金法制的改革,但是速度太慢,金融體系仍有步上日本僵化十年後塵的隱憂,必須加速、深化改革。 三、徒法不足以自行。實證研究顯示在英美法系,公司治理的績效較好,與成熟的司法制度息息相關。去年司法院翁岳生院長曾廣邀外銀人士座談,並仔細聆聽他們對我國司法制度如何加強處理財金案件的各項興革建議,未來應促使司法體系關切公司治理的議題。 四、提升公司治理水準與鼓勵上市櫃公司從事企業併購有必然的關係,這也是政府草擬企業併購法的原因之一。但是,以往這種「震盪療法」的觀念與管制政策及企業文化皆不相容。不過,最近美商所羅美邦證券董事長杜英宗已直指此一問題是企業再造的核心。準此,未來因應更險惡的營運環境,有心從事組織再造的企業,勢必要借助併購活動。 五、國外探討提升公司治理的方式之一,為增加退休基金等專業機構投資人的比重。我國必須有效因應人口老化的趨勢,勞退基金機制也正擬從確定給付制改為確定提撥(包括個人退休金帳戶)制。不過,「勞工退休條例」草案這一方面的機制仍待加強。 企業界與大股東不必對公司治理採取負面、消極的看法。實證研究已證實,如果企業認同公司治理,投資人會願支付「公司治理溢價」以擁有其股票。由此可見,公司治理不但是提升企業競爭力的必要條件,也會是充分條件。 最後,從台灣企業加強全球化佈局,甚至赴大陸投資搶灘的策略來看,其實更凸顯公司治理的重要性,因為我們希望國內上市櫃企業把「銀根」留在台灣,繼續透過母公司募股募債。但是,這些上市櫃公司也會有控股公司化的傾向,所以也必須加強它們的管控機制與財務透明度。換言之,越是「西進」,越要「強本」;提升公司治理的水平,不但可以提升整體競爭力,更可維護本國長期發展的自主性。 (作者是理律法律事務所合夥人,東吳大學法研所暨台大 【 |
|
今年證期會的一個工作重點是推動「公司治理最佳實務準則」,目前已有草案。證期會這項準則的草案會透過證交所以及櫃檯買賣中心落實,它的淵源是出自1999年OECD公司治理原則(即OECD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以及東亞其他國家的類似準則。在國際財經組織之間,這是一種「軟性訴求」(即所謂soft law);最佳實務意指best practice,是一個努力的方向。「準則」不具硬性的法律效力,但可以形成市場上及同儕間的良性壓力。 OECD有關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則,大致上可以分為下列幾個重點。以下分別詳述:一、保障股東權益OECD主張公司治理的架構應以保障股東權益為重心,包括登記其所有權的權利、股份自由轉讓的權利,取得與公司有關之有效、即時訊息的權利、參加股東會並參與表決的權利、選舉董事會的權利、分配公司盈餘的權利。我國公司法制大致符合這個要求。較值得注意的是,OECD也主張應有一個有效率,並具備透明度的市場,以供公司控制權的競逐(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有關資本市場中公司控制權的取得、重大交易 (如合併、收購、處分重大資產)等行為之規章,應予明示並揭露,以便投資人行使其救濟的權利。前述交易應符合價格透明化的原則,並在公平的條件下進行,以便持有同一種股份的股東,可受到應得的保障。最近制訂的企業併購法,以及證交法修正增列公開收購要約,大致符合這些要求。 二、對股東的待遇應符合衡平原則OECD認為公司治理架構應確保對所有股東都公平以待,包括少數股東與外資股東。所有股東受到侵權行為,都應有權要求救濟。同理,不應容許內線交易,以及其他「自我交易」(self-dealing)的濫權行為。如果董事或經理人在公司所涉的交易中有重大個人利益可圖,應揭露這種利益衝突的事實。我國法制在這方面缺失尚多,徵求委託書的規則第17條尚有支持「當權派」之嫌,必須檢討。 三、其他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在公司治理方面的角色OECD認為公司治理架構應認同其他利害關係人(如勞工)依法所享有的權利,並鼓勵公司與這些利害關係人充分溝通、合作以促進財富、就業以及財務健全企業之永續經營。準此,OECD對於其他利害關係人的「權益」,認為應依法辦理,否則治絲益棼。稍早國內有「產業民主」及工會代表擔任董監事的呼聲,其實應審慎研議,不宜貿然推動。 四、揭露與透明度的要求OECD認為公司治理架構應要求及時、精確的揭露,其對象應包括與公司有關之所有重大訊息,包括財務、績效、所有權以及公司的治理。具體而言,這些重大訊息至少應包括:(一)公司的財務與營運訊息。(二)公司設定的目標。(三)主要股東及表決權狀況。(四)董事、主要經理及其薪資。(五)重大可預見之風險因素。(六)涉及員工及其他利害關係人的重大問題。(七)公司治理結構與政策。 以我國目前揭露制而言,水準大致是中上,但揭露(包括會計簽證)的品質仍有相當提升的空間。 OECD的準則制訂之後,每年的公司治理論壇有一個重要工作:就是進行「同儕審查」(peer review),檢視與會各國的進度與成效。我國即將實施的公司治理最佳實務準則當然不會完全參考OECD的準則。不過,中國大陸已在今年1月制訂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指導意見,洋洋灑灑的內容超過100條。台灣的公司治理水準顯然在大陸之上,更應即早通過有關準則,以深化加強公司治理的努力。 (作者為理律法律事務所合夥人,東吳大學法研所暨台大 【 |
|
|
公司治理的核心在董事與領航團隊的良窳,我國公司法也將執行公司業務的重責交由董事會。不過,囿於股權集中與家族企業的特性,一般人的印象是我國上市櫃公司的董事會功效有限,不太像「玩真的」。 如何將董事會落實成真正的「意思機關」?我們可參考OECD公司治理原則的作法。OECD主張公司治理機構應確保董事會可提供公司在策略上的指導功能,有效監督經理部門,並對股東與公司負責。董事會應取得充分資訊(fully informed),並應符合善意、勤勉、專注,以股東最大利益為依賴的要求。如果董事會的決議對不同的股東將造成不同的衝擊與影響,董事會應嘗試公平對待股東。此外,董事會應確保公司遵守法律,並考量其他與公司有利害關係的團體所享有的權益。 證期會在本年2月底核定證交所及櫃檯買賣中心,對今年申請上市、櫃的公司要求設立二名獨立董事,一位獨立監察人。其實,以前這兩個單位的有價證券上市(櫃)審查準則就有獨立董事的規定,但是囿於企業文化而績效不彰。這次修訂的重點在加強對獨立性的要求,依照這些新規定,下列人士不具獨立性:一、申請公司之受僱人或其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二、直接或間接持有申請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1%以上或持股前十名之自然人股東。三、前二目所列人員之配偶及二親等以內直系親屬。四、直接或間接持有申請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5%以上法人股東之董事、監察人、受僱人,或持股前五名法人股東之董事、監察人、受僱人。五、與申請公司有財務業務往來之特定公司或機構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持股5%以上股東。六、為申請公司或關係企業提供財務、商務、法律等服務、諮詢之專業人士,獨資、合夥、公司或機構團體之企業主、合夥人、董事 (理事)、監察人 (監事)、經理人及其配偶。七、兼任其他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超過五家以上。 此外,在新制之下,擔任申請公司獨立董事或獨立監察人,必須具有五年以上之商務、財務、法律或公司業務所需之工作經驗,也必須每年進修。 除了遵循前述規定以外,有關強化董事會與獨立董事會職能的議題,還有下列值得探討之處:一、要求獨立董事最好能再加強其法源基礎。有些學者認為這種規定可能違憲,筆者認為倒也未必。不過,如果在證交法中明定法源,對於限制大股東的「被選舉權」,是比較慎重、合情合理的作法。二、公司法第27條容許政府與法人股東推派代表出任董、監事,並可隨時改派。這種規定破壞董事發揮職能的機制,在企業文化上,也造成「一人事二主」的分裂忠誠困境,更易造成公營事業董事的泛政治化與酬庸,未來對上市櫃公司及公營事業宜予刪除此一規定。三、新制獨立董事的規定是否會造成「善者不來」的結果?國外實證研究顯示外部董事也需要足夠的財務誘因,包括認股,才會發揮功效。此外,我國外部董事的來源可能在學者、專家。公司如何為他們購買責任保險、或降低求償風險,也是任何愛惜羽毛的董事人選會關切的問題。四、新制獨立董事的規定是否也會造成「來者不善」的結果?也就是符合形式上的獨立性要件,但事實上與大股東關係密切,而不會真正獨立行使職權的人士,出面擔任獨立董事。這是證期會、證交所、櫃買中心未來把關的重點。五、獨立董事新制目前只對初次上市公司適用,這些公司正好是比較面對國際競爭的高科技事業。何時對已上市櫃公司(其中仍有不少屬傳統產業的公司)也實施此制,以避免「一國兩制」的批評,也會考驗主管機關的智慧與決心。 獨立董事是國際趨勢,連大陸都已在去年8月就已付諸實施,如果我國新制可避免以往形式主義的流弊,應可有助於提升公司治理的水準。 (作者為理律法律事務所合夥人,東吳大學法研所暨台大 【 |
|
|
如果說公司治理的核心在獨立董事,那麼董事的核心就是忠實義務(fiduciary duty)。在傳統中華文化之中,有「受人之託,忠人之事」的理念。不過,在從大陸法系引進民法及公司法之時,並沒有完全相對應的概念。這是因為忠實義務與利益迴避原則,原來是英美法系特別堅持的原則。不過,近年來忠實義務已成為普世原則,甚至大陸的公司法在1994年實施時,就已引進這個規定,其主因是怕在推動國營企業公司化、股份制之時,被倒賣國家資產。 去年11月我國公司法修訂之後,正式規定負責人忠實執行業務的要求,算是引進了忠實義務。不過,這個規定仍待學說與判例的落實。譬如,如董事未盡忠實義務似乎應連帶負責,因為董事是以集會方式運作。不過,監察人是各自行使職權,則其未盡忠實義務似乎就應各自負責。 這個忠實義務的規定似乎還有一個盲點,就是從條文看起來,似乎僅以公司為負責的對象。這是因為公司和股東是不同的法律主體,所以在大陸法系的形式邏輯之下,如果負責人違反忠實義務,應對公司負賠償責任,但是公司正好被負責人掌控,會主動求償嗎?以往,因為這種形式邏輯,所以公司是直接受害人,只有公司可提起刑事背信罪的自訴或告訴;股東是間接被害人,不得提出自訴或告訴。為了避免這種問題,在今年2月制訂的企業併購法對忠實義務的要求,改為以「全體股東最大利益」為圭臬,以免陷入原有形式邏輯的陷阱。 此外,雖然公司法參照英美法系的集體訴訟程序,規定少數股東可以代表公司向董、監事提出「代位訴訟」,但是因為這個條文是引進德國、日本的「改良版」,所以還要求少數股東持股達5%,每人持股達一年。所以,實際上,少數股東很難利用此一機制訴請法院救濟。這次公司法修正,將5%改成3%,其實毫無意義。德國政府委請的學者去年提出建議,以10萬歐元或1%持股孰低者計算,也無持股期限,算是比較合理的作法。韓國在亞洲金融危機後修改商法(即公司法),也做了類似修正。 訴訟費用預繳也是對少數股東不利的重要原因,第一審法院要抽成1%做訴訟費,由原告預繳,上訴各審級還有1.5%的裁判費,都不利於落實對少數股東的保障。證期會、證基會在地雷股案件中,為如何避免這些費用煞費心思。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行政院對上一屆的立法院曾提出「投資人保護法」草案,但未能獲通。游內閣應會再提出此一法案,不過,本草案是否能順利通過並予以落實仍待觀察。 忠實義務的落實,還涉及「獨立監察人」的機制。在實施單軌制董事會的國家,因為不能完全期待內部董事會落實忠實義務,所以還要求外部董事,這是它的邏輯。我國採取「雙軌制董事會」的體制,也就是由監察人監督董事會的運作,包括是否忠實執行公司業務。所以,監察人的功能就等於是外部董事。國際上就分為單軌制或雙軌制擇一的立法例。 不過,今年2月對新上市、櫃公司實施的獨立董事制度還包括「獨立監察人」,其邏輯就令人費解。因為監察人本來依法就已經要具備獨立性,恐怕這又是引進日本的制度,但是,它在日本實施的成效相當有限,是否必要與如何落實都值得再思。不僅只是台灣面臨如何落實忠實義務的挑戰。大陸最近上市公司「銀廣夏」涉嫌違反證券法的案件中,其核心的爭議也涉及董事違反忠實義務與是否可以提起集體訴訟。從東亞政治經濟發展的過程來看,賦予實體法上權利(如董事的忠實義務),如果沒有良好的程序機制(如集體訴訟、衍生訴訟)予以配合、落實,不可能提升公司治理的水準。 (作者是理律法律事務所合夥人,東吳大學法研所暨台大 【 |
|
|
去年是「金融改革元年」,也通過所謂「金融六法」。但是金融機構的公司治理工作其實仍有大幅加強的空間,而且時機越來越緊迫,因為不良貸款債權節節攀高,而且外資機構與民間專家對不良貸放比例的估計,大概都在政府公布數據二倍以上。 金融機構的公司治理問題較為特殊,因為銀行等吸收存款機構與一般企業不同,是「流通性」的創造者。因此,整體金融體系的風險(systemic risk)是其他產業所不會面對的風險。為了避免這種風險,而有存款保險的機制。但是存款保險對銀行的經營者又產生「道德危險」(moral haz-ard),也就是銀行對貸放可能過分冒進,因為虧了也有存保墊底。 準此,在1999年OECD制訂「公司治理原則」之後,巴賽爾銀行監理委員會馬上跟進,也提出「加強銀行的公司治理」。此一文件,除了重申OECD所整理出的原則以外,再強調內部稽核、內部控制、信用風險,以及防杜對關係人不當貸放的行為。 從公司治理的理念而言,銀行董、監事所負的忠實義務,其對象不應只限於銀行本身或其股東,而應兼及銀行的債權人(也就是存款人)。目前,國際上正熱烈討論此一問題。 本系列前文曾探討忠實義務負責的對象,在公司法明文修列此一義務之後,存款人是否可以援引主張,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不過,公司法也規定如公司違反法令,公司與負責人對受損的第三人要連帶賠償。那麼,公司組織型態的金融機構可能會違反什麼法令?基本上,這應是與貸款品質及揭露有關的金融法令。換言之,政府如果要加強公司治理,就必須加強執行金融機構打消呆賬以及相關資訊揭露的規定。 巴賽爾委員會對銀行監理曾提出一個「駱駝」(即CAMEL)的基本原則,強調資本通足性(即C)、資產與管理團隊的品質(A與M)、收益(E)與流動性(L)。不良貸款債權的處理與前述每一項因素都有關,所以是做為加強銀行的公司治理的一個適當議題。 但是如果對不良貸款債權用粉飾太平的作法,只會使資產品質再持續惡化。里昂證券新興證券市場分析公司(CLSA E-mergingMarkets)最近委請經濟學人的分析師Paul Cavey撰寫台灣的金融體系分析報告,就指出台灣有罹患日本症的危機。 如果沒有積極整頓不良貸款債權的政策,對公司治理的另一個不良影響是就不會有併購案件,因為有興趣的買家可能在等探底。在這種不確定的階段,呆賬就持續增加,並且必須用減免金融業營業稅的方式補貼,等於納稅人承擔損失。 此外,金融機構的併購尚且涉及我國主管機關對外資的立場。當然,政府原則上是歡迎外資。但是我們鮮有監管全部外資子銀行的經驗,最近第一商銀開始標售不良金融債權,有意投標的資產處理公司多為外資,這是相當具有正面與指標意義的發展。不過,這批標售是否會帶動金融機構的跨國併購,有待觀察。 除了銀行以外,其他金融機構也面臨公司治理的問題。此外,四大基金也是公司治理未來發展上的一個重大議題,因為他們資金用途(投資項目)受限,也往往受到政府干預。未來如依「勞工退休條例」草案的方向,邁向多元的勞退基金或賬戶方式,公司治理的問題可能會更嚴重。 就算在美國,已有制訂「勞工退休收入安全保障法」(簡稱ERISA),仍發生恩龍的員工過度將退休金購置本公司股票,而造成員工慘遭大幅損失的情形。我們未來如何預見這類公司治理的挑戰,以及把這些基金從近似金融機構的角度予以重新定位,以及如何促進主管機關勞委會對資本市場與公司治理的瞭解,都必須未雨綢繆。 (作者是理律法律事務所律師,東吳大學法研所暨台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