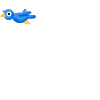那年我八歲,哥哥十歲。母親以「離婚」威脅父親提早辦退休,因此我們舉家從小琉球遷移到臺灣來。搬到臺灣之後一切都變成陌生,舉凡環境、人物、學校全部都換新。還有一位比我小三歲的妹妹,她從出生就跟山上的外婆居住,對我們兄妹來說她比任何事物都還要陌生!
母親拿了父親的退休金,他們一起到山上〈盧山〉跟著祖父種桃、梨、香菇,母親對著雜亂無比的山坡地野心勃勃的要去開闢它,使之成為金山。也不想想父親的心情,一位曾經叱吒風雲的軍人忽然變為拓荒者,槍枝變鋤頭,戰袍換農衫,當時我比母親還能感受父親淒淒然的心境。
母親雖然是原住民,卻有著最前衛的思想,她要我跟哥哥在鎮上讀書,說在部落無法學得好知識。她對我的期望是長大能當老師,她說那將不愁`吃、穿、卻不知我最痛恨老師了。
留我們在鎮上,母親都不知我們兄妹過的是地獄般的生活。那個年代,外省人和山地人的雙重血緣已讓我們飽受凌虐,她還找了個客家人來寄宿〈我們都叫她張媽〉,明明是找不到其它費用比較便宜的人家,母親卻撒謊說:「在校學國語,在民間學台語,在山上學山地話,在這可學客家語。」
她還很自負的說:「以後你們長大出了社會就能跟各種人溝通!」這點倒是應驗她當時說的話。
當張媽把我們安置在二樓最旁邊的木房間,屋頂銜接處還出現個大洞,一看就明白母親選了最便宜的房間!光是看那木板就能想像每晚該承受的煎熬,母親安慰著說:「別怕!冬天馬上就過去了,到了夏天用不著電風扇就很涼快..。」
給了我和哥一人一個空紙箱,要我們裝自己衣服用的。
兩條棉被、兩個枕頭、就這樣放我們倆在此。
張媽是開漫畫租借店,她的房子長又寬,隔了好多房間以價錢分出大小、好壞出租。後面還有個大空地供阿婆〈張媽的婆婆〉種菜、養些雞、鴨消遣渡日。
在張媽家總有做不完的事情等著我們兄妹倆...。
每天早上哥哥必須擦窗戶和整理昨夜租書者弄亂的書籍,我則餵家禽、掃地、這樣才能吃早餐上學。放學後,我必須守在張媽身旁服侍她煮晚飯,她一下子:「ㄚ頭!鍋拿去洗」一下子又:「ㄚ頭!去擺碗筷」。哥哥則在店裏替那些﹝還書﹞依原來的位置排列回去。
吃飯時,我們都有固定的位置,我跟哥總是面對一盤盤的青菜,魚肉永遠擺在阿婆和張伯伯還有張小妹〈他們家唯一的小孩〉面前。
張媽說:吃飯要有禮節,不能站起來挾菜,也不能在菜盤理撥弄。哥雖然長我兩歲,個子卻跟我一般瘦弱,他自從到張媽家就很少任意吃飽過。張媽每次都指著哥說:月光〈哥哥的名字〉「你是牛胃阿!每頓飯都非要吃兩碗?」所以哥都不太敢添飯。
我是負責替整桌添飯的人,所以每次都先把哥哥的飯擠壓得緊緊的,後來被發現了,張媽說要母親加伙食費,哥要我停止那種舉動。
張媽雖然派很多事給我們做,但!她也有通情達理之時,就好比等一切手中事和功課做完後,就可以在店裏看漫畫、小說、日子過得倒還好。
只是;每當早上,我就像一位受刑人等著上場被槍決!我恨透了且畏懼去上學!
我剛轉學時是國小二年級,哥讀五年級,當時我們兄妹跟本不是去受教育,而是去受凌辱。受同學的欺負和老師無由來的處罰,我常會壓抑住忿怒跑到廁所去哭泣!去咆哮!
哥哥卻總是默默無語任由同學欺壓,他的個性真像夜晚高高掛在荒野的月亮。我曾問他:「哥!你為什麼都不哭?」。
他笑著回答我說:「傻ㄚ頭!我的眼淚都被妳哭光了。」。他還說:「爸爸交待!男兒有淚不輕彈。我要像爸爸一樣永遠不哭!」。現在想起哥所說的這番話,他一定不知父親因為他的早逝!幾番在夜裏痛哭。
在班上,我的女老師是全校出了名的潑婦,不曾看她笑過。對於我,她視我為角落的掃把、窗戶上的灰塵。我也不去討好她,她似乎能從我眼神看出我的不屑。
所以每當有同學去打小報告說我:「垃圾沒倒乾淨啦!」、「窗戶沒擦亮啦!」、「廁所還很臭啦!」。她的巴掌總不讓我有心理準備就急速響在我雙頰上。罰我提熱水、抬便當、每節下課要擦拭黑板和拍清板擦,那時;我真的恨死她了!
記得有一天上課中;哥哥被他老師以老鷹揪小雞似的模樣出現在我班上。那男老師二話不說就將我的書包全給倒翻出來,又在我身上摸索像在找什麼。原來他懷疑哥哥偷了他的手錶。
我看哥哥滿臉受盡委屈,我好捨不得!為我們兄妹被踐踏的尊嚴,我好生氣!心中的堤防做一次崩潰,在班上我放聲豪哭。那時;我也開始恨男老師。
直到我升上三年級,一切逆境整個改觀!若要問我這輩子,將我的思想從陰霾中引進陽光的啟蒙老師是誰!我要說:不是別人而是我那陌生的小妹.... 她也下鎮來讀書了!..〈待續〉..
限會員,要發表迴響,請先登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