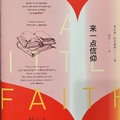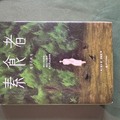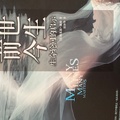2025年11月1日博城讀書會讀《老生》之讀後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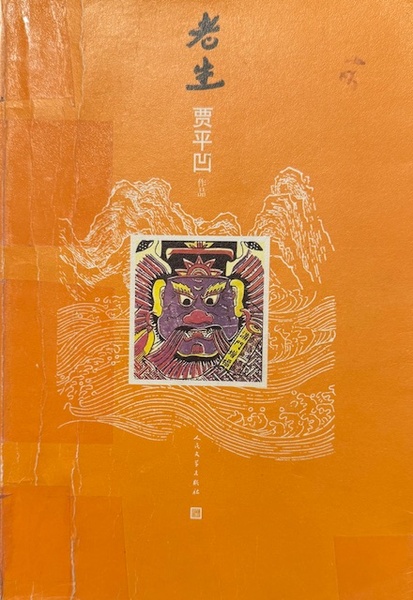
作者:賈平凹
出版社(大陸版):大陸 人民文學出版社
繁體中文版:台灣麥田出版社於2016年5月26日/28日
繁體版頁數:約 332 頁。
實體聚會出席者:鄧家齊、董汝瑰、杜妍美、王素楠、龔則韞
網上:吳怡芳
龔則韞
讀賈平凹的《老生》,像走進一條蜿蜒的黃土古道。腳下的塵沙被風輕輕吹起,迷濛了眼,也迷濛了心。那是一條通往過去的路,滿是泥土的氣味與人世的滄桑。而在這條路上,傳來一聲古老的歌,老生的「陰歌」。
「陰歌」是唱給亡靈聽的,是為死者引魂,也是為生者療傷。
老生唱著那歌時,聲音低沉、嘶啞,像是從土地深處滲出來的聲音。那不是表演,更不是哀號,而是一種生命與死亡對話的方式。他唱的不只是亡靈,也是唱給活著的人聽——唱給那些被命運壓彎了腰、被苦難磨壞了心的人聽。
在賈平凹筆下,老生的歌不僅是祭儀,更是一種精神的象徵。
這首「陰歌」,唱出了黃土地上人與天的距離,也唱出了中國農民千百年來的忍耐與悲憫。當時代的巨浪吞沒了一切,唯有這聲歌,還在延續人性的溫度。它讓人明白——即便生死輪轉,聲音仍能跨越陰陽,替人守住一絲「活的尊嚴」。
老生的生命其實是一首漫長的「陰歌」。他一生與土地為伴,經歷飢荒、戰亂、革命、改革,每一次苦難都將他壓得幾乎喘不過氣,但他從不倒下。他用歌聲替人送行,也替自己療傷。唱「陰歌」成了他與死亡對峙的方式。當別人畏懼死亡時,他卻能平靜地站在墳前,舉起嗓子,用最蒼涼的旋律唱出「人終要回到土裡」這個古老的真理。
有評論說,《老生》是賈平凹對「生」與「死」最深的凝視。
我卻覺得,那聲「陰歌」更像是他筆下人性的注腳。
死亡在書中不再恐怖,而是回歸,是土地的懷抱。老生唱的每一句,既是對逝者的超度,也是對活者的提醒——活著的人更需被撫慰。那首歌因此不只是陰界的聲音,而是陽世的祈禱。
讀著讀著,代表人物有老黑,李得勝,匡三,馬生,墓生,戱生等衆多人物一個個走過去,講的是民國時期、土改、人民公社,飢荒,改革開放,秦嶺游擊隊和保安團等的故事。其中老生是个傳奇人物,他为死人唱陰歌,年年如此,活得久而見證了這段百年歷史。
我忽然明白了賈平凹為什麼要讓老生這樣一個平凡的農人,背負起時代的苦難。他不是英雄,也不是聖人,他只是「會唱陰歌的人」——懂得在黑暗裡守住光。他以一首歌,延續了民族的靈魂。他以一顆平凡的心,承接了歷史的重量。
小說中四個故事沒有喧嘩的口號,也沒有英雄的姿態。只有一個老生,在荒野裡唱著他那首陰歌,風一陣一陣地刮過,山谷回應著微弱的回音。那回音讓人心酸,又讓人安心。原來,人只要還能歌唱,就還沒有被命運徹底吞沒。
他唱過太多的葬歌,也見過太多的離散,但他依然能面朝土地,對著天空,靜靜地呼出那聲悠長的調子。那不是悲鳴,而是對生的頌歌,對死的頌歌,對一切輪迴中仍然閃爍的希望之頌歌。
當我闔上書本,耳邊似乎仍有那聲低迴的陰歌。它不屬於過去,也不屬於死亡,而屬於所有曾在苦難中掙扎著活下去的人。那陰歌提醒我:人可以貧、可以老、可以被風塵打磨,但只要還能開口唱一曲,生命便仍有力量。
羅正瑜
和《山本》相似,贾平凹的这本《老生》讲的是从民国时期、土改、人民公社,饥荒,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围绕秦岭游击队和其后人展开的故事。其中老生是个传奇人物,他为死人唱阴歌,几十年不变老,活得久而见证了这段历史。
书中的亮点是对山海经的问答,其中有很多独特的观点,如同世外高人与凡人的对话。比如“经”指的是经历而不是经典,当时古代的人们还很原始,所以看到什么山都很新鲜,会给所有的动物植物安排拟人的特征,比如吃了什么东西人的性格上就会有相应变化。这可能只是把偶然同时发生的事人为加上了因果关系,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觉得很有趣。又如,“人是见不得有像人的动物,所以能征服的就征服,征服不了的就敬奉,软硬兼施。可以身上有颇多让人同情的善良人性,所以他的书更能让人读下去。我相信不管是在古代、近代还是现代,农村还是城市,一个社会中丑陋者有,高尚者也有,甚至同一个人身上有残酷的一面,也有温情的一面。美与丑是无处不在的,就看作家愿意描写哪一方面。《山本》和《老生》这两本书都注重描写丑陋的那方面,不是我喜欢的角度,但是我尊重作家的选择。在后记中,作者也提到他经历了这么多年这么多光怪陆离的事,不吐不快。想来把这些写下来作者也是经历了很多痛苦的。
董汝瑰
此書講了四個人民共和國時代的故事,中間穿插了「山海經」,對亙古山川大地,及萬物形成的講解,似乎是要擴大人們的視野,用千萬年的地老天荒,來對映並淡化中共執政之初的亂象:生時活得有聲有色,執著妄為,死後歸零,煙消雲散,成為神州大地上的一粒塵土,無足輕重!甚至王朝帝代,也終將會成為歷史上的一筆!
故事從嶺南的一位主持喪事的老唱師 - 老生講起,唱師老生經歷過許多年代,没有人知道他有多老,但在一次大瘟疫時,他唱得太久、太累,病倒了!後來牧人發現他臥在土窑中的炕上,不吃不喝。牧人為兒子請了教師,一邊牧羊一邊學習,教師就教他「山海經」。唱師老生在駕鶴西歸前,聽著土窑外朗頌的三海經,回憶了這本書所述的四個故事。
透過他的視角,看到共產党如何在抗日戰爭時期與國軍互殺,爾後興起,在神州大地上實行了共產政權。故事始於市井之徒匡三如何翻身,從地痞變成共党游擊隊員,胡作非為,後來升到省軍区政委,再到大軍区司令。他的近二十個親戚也全當上了県長、省長、司法厅長、公安局長、市長、主任、董事長…..,秦嶺143個鄉鎮裡,有76個鄉鎮領導與匡家有关。本書寫盡了對窮人大翻身,各顯其能,爬上高位卻德不配位的諷剌,及對世代勤墾富農被共党打擊、掠奪、迫害的不平!但看看「三海經」,世事無常,所有人,不論成敗,終將老邁腐朽!
另一個故事是講1950年代的土地改革,窮人分得了富人的地、房屋、及傢具,毫無法治的共產主義,破壞了生產線秩序,對此黑暗時期,多有描述。但对神州浩劫的日本侵畧及國軍的抗日,隻字未提,對大飢荒時期,全國餓死了三千多萬人,也著墨不多,是對這些「隱瞞」的反諷嗎?
賈平凹用這些故事,顯示了共產黨的善於製造矛盾,大家為了自保,人與人之間互不信任,互相批鬥揭發。上層自定法規,執法者的妄為,泯滅了儒家溫良恭檢讓的美德,只有少數人尚存良知!如第二個故事中慈善的地主王財東,幫助憨厚的白土葬了父母,結下善緣。白土感激萬分,自此去王家做長工。雖然是有階級的表象,但那不計回報的慈悲心,和知恩圖報的美德,使人與人之間融冾和美。但共產主義這把尺度,如何衡量呢?是極其偏激的對富人嫉恨及迫害!
如三海經中所說,古代生活及大自然無為而治的規律,對映了近代,許多人為因素對社會及世界造成的影響,值得我們深思!
賈平凹的寫作是鄉土文學的風格,有時形容得過份詳細粗野,令人覺得非常不文雅,讀得很不舒服!這是我很難接受或欣賞的。
王素楠
作者賈平凹是1952年生於陝西的鄉下, 1972年,偶然的機遇,進入西北大學學習漢語文學。此後一直在西安,從事文學編輯兼寫作。出版很多作品,有世界各國的翻譯出版二十多版本,得到很多國家的最高榮譽文學獎。
初看時,對於作者筆下對秦嶺落後地區的鄉鎮人物粗俗地描述,人如草芥,各種粗暴殘忍的做法,無緣無故的人就沒了,實在不敢領教,幸好有先讀完讀友的導讀,能助我閱讀完。之後,我還回頭又看了幾處,的確是本好書。
作者認爲自己有使命,以本書老生為主角,講述中國百年的歷史,是中國的縮影。老生的職業是唱喪歌的,身在兩界,長生不死超過百十幾年,見證了幾代人的命運輾轉和時代的變遷。書中有四段,是從當初游擊隊開始,經過文革後又來到疫情之間的時代背景下,描述代表人物有老黑,李得勝,匡三,馬生,墓生,戱生而書名是老生,都是意味著在逆境中,要求生存嗎?
作家解讀山海經來推進歷史,山海經描述的山川地理,動植物,礦物,醫藥,宗教等等,也就是描述紀錄整個中國。老生這本書里也是這樣,寫村莊,寫人物,寫時代,寫國家和這個國家人的命運。
人在大自然中和動植物在一起,人從來不怕何動物和植物,人只怕人。人是產生一切災難惡苦的根源。所以在秦嶺,大戶人家門口的石刻童子捂耳和掩嘴的家訓,是符合儒家"非禮勿聽,非禮勿言"的做人原則。大概試圖教育人們減少因人而產生的摩擦和災難。(2025.11.22抄錄)
限會員,要發表迴響,請先登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