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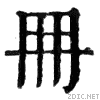
家父從元旦前就住進了醫院,病情一度轉差,以致一直到三月初才出院,而剛出院從電視新聞得知歌手林良樂小姐故世的消息時,頗為感觸,他撫慰過我心靈的歌聲跟他的唱出過的歌詞間,頗有徘徊,而這幾個月,照顧家父已五年的看護,為了女兒屆青春期的學業,也回國去了,也不好挽留,而仲介公司又遲遲安排不上,不少時間也在醫院中,而在新看護的適應期中,剛才想藉點未盡的功課恢復點原先的步調,又再搜尋了「江緒林」,沒想到看見的是他在上個月竟已辭世的消息。
年輕魯男子時敗給過一本《理想國》的,一些曾有的境遇對於那【衛士的生活】篇章,在很多僅是流過的解讀偏差中,潛藏著帶有些自己也無法明確的恨與怨的衝動莫名的,而那帶讀的老師也剛退伍不久吧,認真說當時抓住了多少的「理想」與「國」都不得而知,而又剛從服從及潛藏的叛逆揪混中遇上辯證,成長的環境真也不曉得學這些要做什麼吧,家人、學校也不慣我在那其中陷入的狂亂,也就輟學了,甚至收拾行囊時,還曾將那本《理想國》給扔到了垃圾堆中,在當時並沒有太多思辯的翻閱,【知識說】就已看的縹緲失魂,是僅翻跳到了【專制者】篇章的開頭,盯著那專制兩字就落下了盲魄的,而任課老師兩個月不到則早已帶讀完,而說起了他接著將講述的亞里斯多德時,也說當時找不到適當的書籍介紹,要我們自己到圖書館找資料,不過自那後到輟學前,就沒再進過他的教室了。
是歷經了一段服役生活,遇上過一本E.佛洛姆的《逃避自由》後,又遇上當時郝總長的「家譜」運動,也不知為何從服役的生活,想起了那當時不知曾是如何矛盾的【衛士的生活】,那次又再買了本再翻開後,那次曾翻開到了【來生說】的三張床,而中山室書架上的《論語別裁》再加上《逃避自由》的某種草草化合,是自己畸型,自己經歷畸形,還是那兩次世界大戰後及那兩岸的分治讓我自己所處的學習及生活環境畸型,都也只能是對那些得先採取或遺或忘,朝向對於那「畫家」、「工匠」、「神祇」與「神祇」、「工匠」、「畫家」所造的兩種三張床就先別去怨和歎吧,而一點的「精微」與「賊」的提醒間,自己也感覺那或較適合「五十」以後吧,當時改看起自己也沒修完的經濟學及家姐書架上的會計學。
不常上台北的,關於柏拉圖後來也僅在所謂二線城鎮的書店角落內,遇上過一本吳錦裳先生翻譯的《饗宴》,而體力的活中,那個陌生討論境域翻開則更遙遠,當時的雙足雙手一天下來,看到書很容易就瞌睡,在開頭很多的更陌生中,也沒能翻開,一直到也過了五十歲,才在網路書店找書時,看到有王曉朝先生2003年出版的《柏拉圖全集》,不過台灣也曾出版的繁體版已購不到,幾經思量後才購下了套簡體版。
自小那些微言大義記誦,及俠義小說鋪陳的兩極,到了年過五十對那些篇幅中的描述仍抓不住,加上簡體文字的仍陌生,能翻開的也不多,又好一段時間後才想到從書籍上的篇名在網頁上尋訪,尋訪後更看見更多自己的不曾認識也頗有驚嘆,曾希望能更有清靜時再來閱讀,但一些生活步調仍是不能,以致在梗概與微細間也更有自嘲,而之後停下好久又再尋訪,是去年年九月在一種仍是感覺厚到無力的書頁中,盯著封面上的"PLATO",也忘了加什麼作搜尋,才無意中遇上江緒林先生的閱讀筆記的,而關於筆記的內容除了佩服外,也頗好奇他又是怎樣的一個人,甚至從他任職校園的網頁照片上,懷疑過「那或得怎樣的渾厚天資天份及地理地時養成」,才能在那個年齡階段有那樣的認識,但稍更翻開仍也是不能,只好暫交與自己都不知道能否有的晚年,以致上週從過去維基過去也並沒有的頁面,見到他竟以這種方式辭世的消息時,一種莫名的慟久久難去,至於「學者、行者、辯者」與一種「牛」間,也只能冀盼他在天有靈,能更護視國與家及人與類,在不僅政治思想上的差異與不足了。
至於「煩惱濁」、「眾生濁」間,則又不知為何又想起了席幕蓉女士的「無怨的青春」開頭的「在年輕的時候」,及杜斯妥也夫斯基《罪與罰》開頭的那「用力過度的青年」,及關於中國近代史上那列強入侵所需要的「力量思想」所曾干擾影響的幾代及各種年輕,就不知又仍得怎樣的價值觀有更大的剩餘,及何時才能潤的出「質」、「量」與「力」的和諧平復了,至於「英才作育」與「公子讀書」的大慈與大嚴,又得該如何三十、五十,也不曉得是不是醫院的關係,從「差太多」與「差不多」間,所曾想起的社會心理及社會思想教育的發情期與凋零期的父子聖,就不知道苦勤修的燈籠,與纍劫累世間的燈油間,是要到什麼時候才能辨別啤酒、威士忌、白酒與XO了。
自去年送了瓶金門高樑給少年學徒時的師傅後,認真說去年還是碰觸白酒較多的一年,曾聽說他年輕發現癌症後跟了位師父學習,後來也設了處神觀,去年恰值二十五週年第一次邀請我,想起聽說平時頗好喝上一杯時,在前一天就帶上了,也看見他先獻祭給神祇的虔敬,後來一次完福祭祀時,可能又因些琳瑯滿目的酒廠及酒種,猶疑間恰又有人介紹,又購下過了瓶馬祖所生產的高樑,有些年很少喝酒了,好多年或家人出差帶回的,或購下作為祭祀的,開過瓶的還剩不少,這些非是至親好友,也怕不禮貌不敢拿出來分享,至於以前也檢討過的轟轟烈烈所影響的正正當當,關於寂靜涅盤與無法寂靜間,或就更不知道周星馳先生的《長江七號》又是想訴諸給誰的了,說來慚愧,在有線電視的轉臺間,多次還曾誤以為那又是部搞笑的諜報片呢,也都忘記一次是撞上那七仔的哪個段落,才又找出從頭看起的!
剩下的就是候選人學習這些學科的次序了:20歲時選擇一批人進行系統的、綜合性的學習;30歲時再挑選一批人,“通過辯證思維的能力這個用作爲考驗的工具…一直走向那‘是’的本身。”【360,這時候要防止由辯證法走向無神論和玩世不恭】;35歲,回到洞穴,參與管理戰爭的事務以及其他適合年輕人擔當的職務,迫使在實際事務中接受考驗;50歲經過考驗者:一方面將靈魂之光向上投射去觀照善本身,由輪流用之來整飭和治理城邦、公民們和自己。“他們把大部分時間.....
這是一篇最具重要的關於知識論或認識論的對話,主題是“知識是什麽”;思想深刻且成熟,內容繁複而艱深,並且由於翻譯並不上佳,我對此文的閱讀和理解並不充分。聊做記錄,以備日後閱讀之用。
陳康先生對《巴門尼德篇》有專業詳實的注解,可是其譯文是1940s年代的翻譯,文字對我有點拗口了,轉用了王曉朝先生譯本;但陳康先生的注解很精深,以後再補讀。這是我讀得最潦草,最沒有把握的一篇對話了。
Plato 《巴門尼德(Parmenides)篇》小摘要(2_7)
「拒斥模仿性的詩呀!」這是在《理想國》【來生說】開頭蘇格拉底的語句,不知道是他留下的多少語句中的一句,至於千篇及一律的師與學,與當肖與不當肖的父與子,就或不知道又當如何父傳子、師傳生,得是在釋或得是在放了,至於「有樣看樣」、「無樣自己想」的「行儀」、「觀法」、「禁忌」,又想起些或早已知、仍未知的所謂識的難感難應,及或開放或封閉的知的難別難辨,或就更不知道利己亡心的忘,與利他言己的記,又當如何去離性自性及第一義了!
至於觀天如何記,觀地又如何者,關於《巴門尼德篇》中討論的一與多中,關於年少年蘇格拉底提出的有譯作型論的,也有譯作相論的,關於法的邏輯始源又出自怎樣的驚與歎的磨與合,就不知道又是什麼讓江緒林先生沮喪到沒能繼續去完善的了,而關於「黃安」到「紅安」,以及從「黃安」到「黃西」,那之中的物理及化學就又不知道當如何的中及如何的美了,也許吧,或也該想想《大國民》的「底魯」與「梯樓斯」的差異吧,但就不知道那是否又是犯了癡戒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gZczqZdR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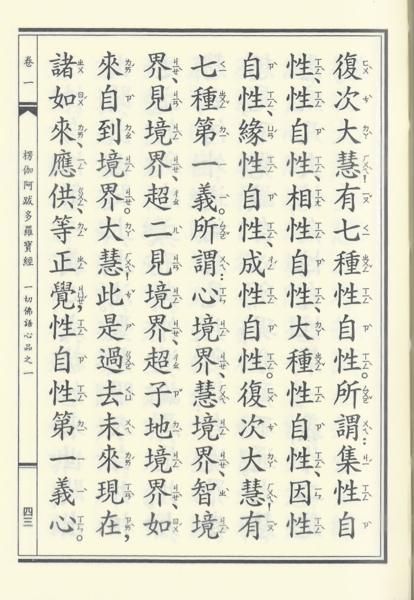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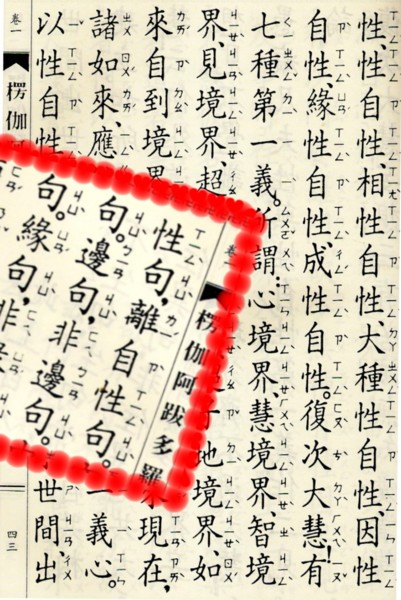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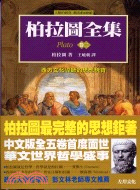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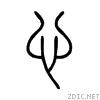



 ..........
..........  .........
......... 


 .......
.......
云何真言教法。謂阿字門一切諸法本不生故。迦字門一切諸法離作業故。............波字門一切諸法第一義諦故。............縛字門一切諸法語言道斷故。奢字門一切諸法本性寂故。沙字門一切諸法性鈍故。娑字門......
摘自:大日經卷二
然而,柏拉圖的分離相論卻有可能引發諸多困難,這主要可由《巴曼尼德斯篇》裡的少年蘇格拉底所遭遇到的三個困境所表現出來:○1少年蘇格拉底對於是否有卑下者的相的存在,顯得猶疑不定;○2由於無法回答相與現象之間到底是如何分有,以致於分有成為不可能;○3更進一步地,正是由於相與現象彼此的完全分離,以致於原本肩負拯救現象這使命的相,到頭來卻反而根本無法拯救現象,而且也面臨無法為人所知的這個最大困境。
這三個困境其實正是柏拉圖真理之路---愛智者如何能擁有那與現象完全分離的相的知識?---所蘊含的兩個一體兩面的論題:第一,思考與知識的可能性如何成立?也就是,相如何拯救現象?第二,愛智者要以什麼樣的方法才能正確地獲得相的知識以成為真正的哲學家?關於第一個論題,筆者認為,柏拉圖在《巴曼尼德斯篇》第二部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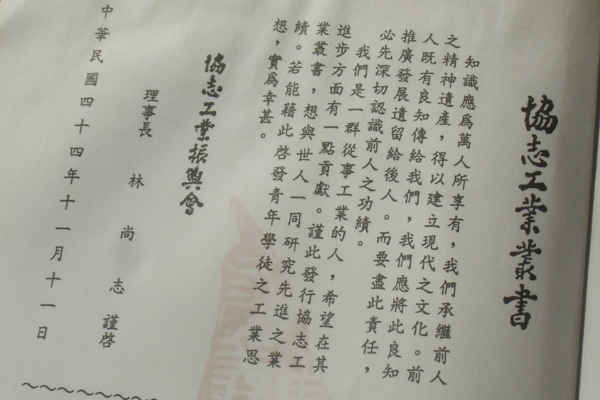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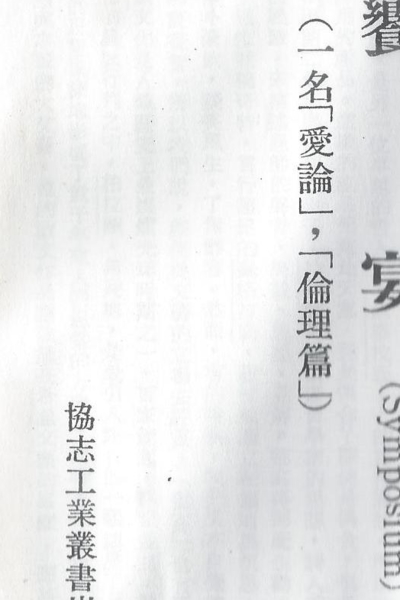
限會員,要發表迴響,請先登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