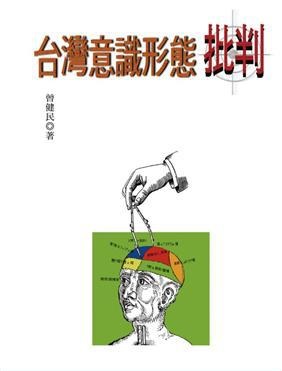打破魔咒化的“二二八論述”
曾健民
日本人宮澤繁在他的著作《臺灣終戰秘史》中曾談到,當他看到臺灣脫離殖民統治光復後不久便浮現“省籍隔閡”,或不同省籍間以“阿山”“蕃薯仔”互為蔑稱的情形時,曾十分難過並痛陳:“分析兩者間產生這樣的感情分裂,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應當是最主要的原因;當然日本和日本人是使兩者分裂的元兇。在臺灣的日本人一想到這問題,便羞愧得無地自容,真恨不得鑽到地下去”。
這是一位有良知的日本人,眼見臺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後不久,出現諸多省籍間的紛亂時的肺腑之言。他指出了一個簡單而大家經常疏忽的道理。那就是:殖民後出現的諸多問題,其原因無他,主要是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所造成的。殖民的傷痕並未隨著殖民統治的結束而結束,它遺留給殖民地人民的惡果是巨大且長遠的。
一﹑看不到歷史的歷史論述
實際上,這也是近年知識界盛行的“後殖民論述”的中心議題。雖然後殖民論述在臺灣也成了時髦的東西,學術界開口後殖民閉口後殖民,但當落實到臺灣實際的殖民後的歷史﹑文化問題時卻完全變了調;這些論述中不但看不到日本帝國主義殖民者的真面目,反而把脫離殖民後複歸的“祖國”當做新“殖民者”看待。真正的帝國主義者﹑殖民者,卻消失了!這種顛倒是非的荒唐後殖民論,與其說是文化或歷史論述,倒不如說只不過是政治論述吧!
當然,這種現象也集中出現在“二二八論述”上,實際上,兩者經常是混同的。
仔細算來,今年已是二二八事件的五十九周年,明年將是第六十年,早已超過半個世紀;在這已超過六十年的戰後世界,人類文明有驚天動地的進展,然而臺灣卻仍自囚於二二八的論述中,無法自拔。近六十年間,有關二二八事件的論述幾乎完全取代了臺灣戰後初期歷史的論述,據初步統計,有關二二八的研究﹑論述已超過二百種,這種對於單一的歷史事件有如此龐大的著述,在世界上也是少見的;依據補償基金會資料,事件傷亡人數不超過二千人,如此的歷史事件,竟然出現了如此龐大的論著,真是匪夷所思。
而且這些龐大的“二二八論述”大多數出現於八O年代以後,特別集中在九O年代李登輝政權轉向以後;可以說,基本上它是與臺灣的分離主義政治勢力同步急速膨脹的,因此普遍帶著濃厚的分離主義的政治意識形態。
譬如,陳芳明在一九八八年出版的《二二八事件學術論文—臺灣人國殤事件的歷史回顧》就是其代表作。從它的書名就可以知道,作者早在八O年代末已把二二八事件定位成“臺灣人的國殤事件”,把二二八事件“建構”成“外來政權=國民黨政權=外省人=中國人”鎮壓“臺灣人”的論述,說二二八事件就是外省人﹑中國人屠殺臺灣人的事件,以激起省籍矛盾,呼喚臺灣民眾的悲情意識,強化所謂“臺灣人主體意識”;由於類似廉價論調的反復炒作,政權輪替後,果然二月廿八日取代了十月二十五日的“光復節”,成為“國定假日”—陳芳明所說的“臺灣人的國殤日”。
由於二二八論述日益成為臺灣現實政治鬥爭的工具,因此論述普遍呈現了“非歷史性”的問題,簡單地說,就是去歷史脈絡的問題。這使二二八事實遠離了“歷史”,成為分離主義意識形態的一部分。其中完全看不到二二八歷史的前因後果,看不到事件與當時的世界潮流或中國局勢的關聯,看不到島外的歷史世界。這種被囚於孤島內的井蛙似的歷史論述,在其中只有所謂“外來的”與“本土的”“族群”鬥爭,完全障蔽了“民主”的問題﹑“民族”的與“階級”的問題,以及“社會公義”的問題。因此成了分離主義政治勢力絕佳的政治鬥爭魔咒,且無往不利。而且,由於它模糊了臺灣資本主義化過程中的階級矛盾,而成了臺灣新興壟斷資本的最愛。
要打破這種政治魔咒化的二二八論述,唯有跳開現在為止的論述邏輯,把二二八事件重新放回歷史的現場,儘量還原其“歷史”的本貌。
就像前述宮澤繁所揭示的:日本殖民統治就是臺灣光復初期諸多紛亂的元兇,或更直接地說,首先,要追究搞清楚日本殖民末期嚴苛的戰爭動員體制,諸如經濟榨取﹑人命動員﹑皇民化運動等等,到底對臺灣造成了怎樣深刻的精神上和經濟上的遺害,而這種殖民的遺害當然與解放後一年半爆發的二二八事件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怪不得如宮澤般有良識的日本人,看到在臺灣的中國同胞相殘的情形會羞愧得無地自容。然而,臺灣的分離主義者不但素來只熱衷宣揚日本殖民給臺灣帶來多少現代化﹑文明化,還盡力去擴大殖民者遺禍的傷口;而且近年還陸續去參拜入祠侵略元兇的靖國神社,這種認賊作父的行為,在某種程度上可視為六十年前殖民歷史的遺害,精神上無法自立的重大傷殘。
總之,要認識到日本殖民統治的歷史是二二八事件的重要“前因”,把這問題弄明白,自然是打破魔咒二二八論述的重要一步。
二﹑打破井蛙式的“唯族群對立論”
當今魔咒化的二二八論述的另一特徵,就是把臺灣與中國局勢和世界潮流孤立出來,在時代與歷史的真空中論述二二八,井蛙式地不斷虛構複製外來與本土的“族群對立”,這種論述造成了臺灣社會思想意識不斷退化的悲哀;為了符合現實的“唯族群對立論”的政治要求,只有不斷陷入這個窠臼。實際上,二二八事件並不是臺灣獨有的,它正是當時全中國混亂局勢的一個突出部分,也與戰後世界新的美蘇對立,亦即東西冷戰息息相關。
臺灣光復後一九四六年年末,也就是爆發二二八事件的半年前,臺灣早已出現了各種紛亂,臺灣的人心呈現不安焦慮。當時的知識人也已經深刻地認識到臺灣的問題與中國的政局﹑世界的新對立有密切的關係。
作家龍瑛宗在一九四六年十月廿四日也就是在告別他主編的日本版文化欄之時,寫〈臺灣將會怎樣〉一文,表達了他對臺灣前途的憂慮他認為決定臺灣未來命運的,有“不依臺灣本身意志而變化的外來力量”,“具體地說,臺灣的命運是受到中國全體的政治所制約,而且中國的命運也受到美國和蘇聯的對立所制約”。他更深刻地預見到“國共的”“和或戰”牽動臺灣的命運,他說:“必將來臨的國共和談應是重要的關鍵;如果和談破裂而內戰長期化,不但臺灣,全國同胞也將面臨更悲慘的黑暗日子,屆時,中國將面臨有史以來空前的危機。”
在發表這篇文章的前一天,龍瑛宗也寫了一篇短詩〈停止內戰!〉詩末他疾呼道:
“停止內戰
和平﹑奮鬥﹑救中國
在自由與繁榮之上
給我們美麗的新中國”
詩人﹑評論家王白淵,也在同期間﹙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七日﹚發表了〈給青年諸君〉,面對臺灣混亂的現實,他鼓勵青年人說:“現在,我們雖居於臺灣的一隅,但見一斑而知全豹,今日臺灣的現實正是中國的縮影及其斷面……要高舉理想,深究現實,進而清楚地認識歷史的方向,妥善對應,朝向建設民主主義中國的大道邁進。”
可見得,爆發二二八事件前夕的臺灣知識人,他們的認識和認同是很清楚的,他們是立足於作為中國的一省的臺灣觀察世局,早已認識到臺灣的前途系於中國的命運,而中國的命運是與戰後新的美蘇對立息息相關,而事實證明他們的這種主觀認識是與客觀的歷史進展相契合的。可悲的是,六十年來的大多數知識份子不但無法認識到這歷史的真實,近年來還淪落入像二二八論述式的歷史論述而不自覺。脫離或違背這種客觀的歷史事實的二二八論述,除了只是為了當下現實政治需求的虛構之外別無其它。
就如臺灣知識人所憂慮的,在二二八前夕,中國已陷入混亂的局面;經濟崩潰,到處爆發反蔣反獨裁的抗爭事件與鎮壓事件,國共和談破裂,和平﹑民主的希望破滅。也同在二月廿八日那天,國府下令駐在上海﹑南京﹑重慶的中共代表團限期撤離國統區,宣佈中國共產黨為非法政黨,關閉了國共和談的大門,香港《華商報》的社論〈半個中國黑暗了〉痛指:“國民黨一口氣吞滅了,被視作和平民主希望的燈塔,……正式宣告今後的政策是反共﹑內戰﹑反人民﹑獨裁……國民黨統治區現在完全是一片黑暗了。”
在臺灣,十二月爆發抗議“澀穀事件”的大遊行;二二八事件的前一個月,爆發了與北平﹑上海等全中國各地同步的抗議美軍暴行﹙沈崇事件﹚的大遊行示威行動,這時,臺灣與全中國各地一樣,“反美﹑反內戰﹑要和平”已經是共同一致的願望和行動。要論述二二八事件,怎麼可能無視這些呢﹖怎可“掩耳盜鈴”自欺自欺人呢﹖
三﹑“二二八”的本質是“反獨裁爭民主”
由此可知,二二八事件的歷史本質是“反獨裁﹑要民主﹑要和平”,更具體的說就是“要民主自治”,而不是什麼“族群對立”。這也可從二二八處委會提出的三十二條政治要求可知,就是要求“高度自治”﹑“台人治台”。
楊逵在事件中發表的〈二.二七慘案真因——臺灣省民之哀訴〉,除了痛陳獨裁﹑官僚﹑腐敗的現象之外,也清清楚楚地指出二二八的真因,他說:“我們認為這些都是國賊漢奸行為。這次民眾的義舉,並非要反抗國民政府,也不是要叛離祖國,更不是要做那一國的殖民地,正是要捉姦拿賊而已。”
可見得二二八事件的本質,是民主起義;是臺灣最早的民主運動,絕不是魔咒化的二二八論述所反復虛構的“族群矛盾”。
在二二八民變中領導武裝部隊進行鬥爭,失敗後潛行上海的謝雪紅,在七月十七日寫就的〈告同胞書〉,對二二八民變做了一次政治總結,該文對二二八民變的歷史意義有正本清源的作用。首先,它對當時戰後的世界形勢做了鮮明的敘述,它說:“戰後世界充滿了和平﹑民主的歡聲……世界上無數被壓迫被榨取的弱小民族和殖民地人民,到處都在爭取獨立﹑民主和自治。”
然而另一方面,美國帝國主義卻“在世界上到處霸佔,和建設了無數的軍事基地,另扶植德﹑意﹑日和中國的殘餘法西斯份子,”使“整個世界變成人民與反人民,民主與反民主的兩大陣營。”,而“國民黨獨裁政府的延長統治,對臺灣政治經濟的壓榨,與對全國人民的進攻根本是一樣的。”
謝雪紅在做了這樣的世界與中國的根本形勢分析後,強調二二八民變的基本性質是:“完全是和全世界與全中國的反獨裁爭民主自治的路線相符合的。”
不管從處委會提出的三十二條要求看,或從楊逵的“捉姦拿賊”來看,乃至謝雪紅的“反獨裁爭民主自治”看,都明明白白顯示了二二八民變的基本歷史性質就是“反獨裁爭民主”,是臺灣民主化運動的先聲。
四﹑“反美﹑反蔣﹑爭民主”——二二八後的新路線
謝雪紅也在〈告同胞書〉中也提及,經過檢討後“今後要進行的路線”,就是:“為著新臺灣的建設……要求最徹底的民主自治,反獨裁﹑反內戰﹑反對封建的保甲制度,反對連保聯坐,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實施土地改革使耕者有其田……擊滅日本對臺灣的野心,打倒美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反對臺灣的國際託管,反對任何某一國對臺灣有特殊權利。”
這代表了二二八後,實際參與並領導二二八“反獨裁爭民主自治”的運動轉進了新的時期,有了新的組織和目標。當年的十一月十二日,來到香港的謝雪紅﹑楊克煌﹑蘇新等人,共同籌組了“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繼續朝新的目標推進。
“反獨裁爭民主自治”的二二八民變,並沒有因事件被鎮壓後消失,在新的時局下,留在島內的有許多人轉入地下,投身中共“省工委”,在臺灣島內為紅色祖國奮鬥,而直接轉往大陸的人士,便以“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為中心朝新的目標前進。直到五O年代韓戰爆發,東西冷戰尖銳對立,臺灣自此進入了冷戰和內戰的雙戰時期,完全籠罩在五O年代白色恐怖的時代中。
二OO六年二月九日
原載《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二二八:文學與歷史」二OO六年春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