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侑實業有限公司設立於民國92年,憑藉著對複合材料的專業,以獨特的專業技術長期為各大品牌OEM、ODM提供產業全方位服務。
我們每天有1/3的時間需要枕頭先相伴。這也是身體、器官獲得休息的寶貴時刻...偏偏,我們卻很容易因為睡到不適合自己的枕頭,睡得輾轉反側、腰酸背痛,又或還沈浸在白天的煩惱、緊張明早的會議、害怕趕不及早上的飛機等等...讓我們的睡眠不夠優質、不夠快樂、沒有辦法快速入眠。
德行天下創辦人有鑑於過去開發各類生活產品的經驗,便想利用本身所長,結合各類複合材料的特性,投入枕頭開發的行列。
從枕頭模具開發、材料研發、創新製造到整合顧客需求過程中,了解到一款枕頭的製作,除了要解決一般乳膠枕悶熱且不透氣的問題,更要同時兼顧到人體工學的體驗性,創辦人常說:「一個好的枕頭,支撐透氣兼顧,仰睡側睡皆宜,才能每天快樂入眠。」
現在導入石墨烯加工技術,讓枕頭的功能性更上一層樓
石墨烯具有良好的強度、柔韌度、導電導熱等特性。它是目前為導熱係數最高的材料,具有非常好的熱傳導性能
德侑實業有限公司為了替自己身邊重視的人們做好一顆枕頭。不論是在外形,還是在舒適度上都能達到最好的需求,即便現今許多的工廠因成本上的考量,顧了外形,忘了內涵,但德侑實業依然不忘在品質上的「堅持、 執著」。
引進先進的加工技術,就是要給消費者最佳的產品
開發、研究、創新以及對材料的要求是德侑實業開發枕頭的初衷,憑藉獨特的專利技術將極其珍貴的天然乳膠與千垂百練的備長炭完美結合後
創造出獨家環保無毒的TakeSoft 徳舒孚專利綠金乳膠;乳膠材料,備長炭,石墨烯應用提高到更高的層次。
同時具備防霉、抑菌、透氣、除臭、遠紅外線等五大功效,並榮獲多國發明專利。
生產過程採用專線製造專利乳膠材原料,全自動化生產保證品質與產量穩定,達到品牌客戶的最高要求。
石墨烯枕頭製作開模一條龍:

選材品管

原料調配

成品製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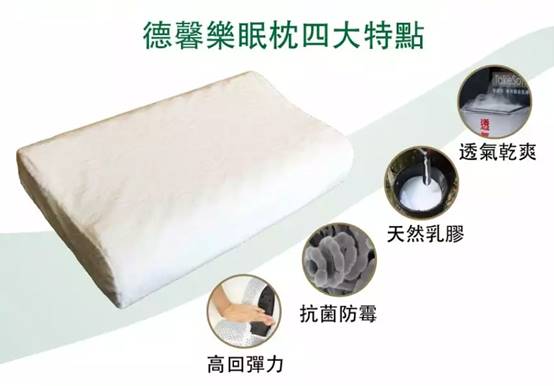
包裝設計

若您有枕頭開發構想或是想OEM自己的品牌,歡迎預約現場諮詢,體驗無毒的TakeSoft 徳舒孚專利綠金乳膠做製作的枕頭,用最專業MIT精神幫助您打造你的專屬品牌。
德行天下:

地址:427臺中市潭子區雅潭路二段399巷200 -7 號
電話:04-2531-9388
網址:https://www.deryou.com.tw/contact.php
| RR1515CEFE15ERFE |
我們在向前走,向前跑。擁擠的人流,就是時間流。我們一波又一波的向前走著,歷史因此很長。 倘若有一個人在高空俯視著,在這樣龐大的人群中,他往往只注意到了群體,沒有注意到個人。 為什么他會記得你?注意到你?不是因為你帥或者漂亮。不是因為你有錢有權。站在高處的那個人不看這些。 所有的職位和身份都太渺小了。即使你拼命舉著這樣那樣的牌子,甚至大聲炫耀,也只能得到同伴的嘲笑。卻不能被高空的那個人所注意到。被他注意到的一定腋下生翅或者瑩瑩發光。 個人在浩瀚的宇宙中是渺小的,但個體溶入浩瀚的宇宙中,就與宇宙一樣浩瀚了。這才是偉大的真理。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抬頭仰望星空吧。你越覺得他高遠,你就越離他近了。(美文精選網:www.meiwenjx.com) 智慧的生命需要生存,不智慧的石頭也一樣要存在。你只要想到這種無差別的客觀,你就應該時刻學會尊重。 滾燙的生命在奔跑,可別忘了腳下是堅實的土地和石頭。愛,就是要不停的跑起來。停下來,就會被抱怨。但時間流不會忘了你。 俯視你的人,是愛你的宇宙,是遙遠的星空。而你就是宇宙的化身。,沒有什么成功比俯視自己更成功。 生命在于運動,更在于探索。跑起來吧,我的伙伴。一定有一個人在高空俯視著你! ——靈遁者(美文精選網:www.meiwenjx.com) +10我喜歡
張玉武/作 一 簡約餐具圖片分割線 村主任吳天貴背著一捆柴禾從店門口經過,見一群娃娃正在往下撕扯前天貼在墻上的選民榜,他一聲吆喝,將他們嚇跑,紅紙黑字的選民榜像破了相的女人,在寒風中抽泣著,一抖一抖的。 吳天貴看了一眼寫著二百多人的選民榜,搖搖頭,走了。 還沒走到家門口,就聽背后有人把他叫住了:“我們家沒水三天了,你管不管?”他吃力地將身體傾斜成三十度角,認出是堂弟吳天明,有氣無力地說:“電費收不起來,我有啥辦法!”“照你這么說,電費一輩子收不起來,你得把全村人都渴死。”吳天明硬梆梆頂了回去。吳天貴顯然生氣了,索性將背上的柴禾卸下,氣呼呼地說:“有能耐你當,看能把高家店搞成啥樣子。”“誰當也比你強。”丟下這句話,吳天明徑直走了。 吳天貴的媳婦桂花做好早飯出外看丈夫回沒回來,一眼看到他將柴火撂在離自家柴垛十步開外,扯著破鑼嗓子叫開了:“你個狼吃狗喂的,把燒火柴放在那兒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想給‘破鞋’送去?”吳天貴剛才受到吳天明無情指責,現在又遭到老婆辱罵,氣上加氣地撲到妻子面前,抬手就給她一巴掌。這下可捅了馬蜂窩了,只見妻子一個倒仰躺在地下不起來了,使出吃奶的勁兒連哭帶喊罵吳天貴:“挨了刀子的,跟你吃不上喝不上,還要挨打,我……我不活了。”說完,跪爬起來就要往旁邊一口枯井跳去,出來看熱鬧的人將她攔住解勸一番,倆口子在人們的推搡中回了家,一個頭朝東,一個頭朝西,誰也不理誰,屋里靜得只聞到桂花嚶嚶啜泣聲,間雜一兩聲老鼠打架撕咬聲。 吳天貴一鍋子旱煙抽完裝上一鍋又抽完,扭頭看了看妻子還沒有和緩的意思,長長嘆了一口氣,緩緩走到媳婦面前,低聲下氣地說:“大寶媽,都怪我,不該打你。看在大寶死去的份上,你就原諒我吧。”一句話戳到桂花的心肝,她由小聲飲泣變為嚎啕大哭,吳天貴自我譴責,不該撕開那縫合的傷口,想起兒子為了配合自己收抽水電費,與高虎發生沖突,被高虎一刀結果于地的慘景。他含悲忍痛從臉盆架上取下毛巾替妻子擦去滿臉淚水,擠出一點笑:“這一屆終于到期了,下一屆愛誰當誰當,選上我也不當。”桂花抬起頭,淚眼婆娑地說:“別像上次,沒人當,你又當。”吳天貴悲哀地說:“當了六年干部,我算是傷心到家了,爛事不說,還搭了個兒子。”妻子見他眼睛紅紅的,反過來安慰他說:“只要你不當干部我就歇心了,好在咱們還有二寶……”說著說著,她伏在丈夫肩頭又一次哭了。 吳天貴明白,妻子這一次哭泣是對他不當干部的哭,這是喜淚。 二 簡約餐具圖片分割線 候選人產生了,第一名仍是吳天貴,吳天貴堅決跳出了候選人名單,按照順序,位列第二很有可能在下一輪競爭中挑大梁,出乎意料,高大洋也不干,既然第一第二名都不愿意干,第三名總不會退出競選的圈子,可高家店這地方就是怪,文生龍也如出一轍,提出不干。 人大主席魏光源得出結論:吃水問題解決不了,誰當也不好當。 三 簡約餐具圖片分割線 高家店由于情況特殊,選舉工作未能如期進行。這下可急壞了鄉長李有旺,他每天都能接待來自高家店的村民,反映的共同問題是飲水難。萬般無奈的李鄉長只好作出批示,由鄉財政出資,墊付每月的抽水電費。 只要不向老百姓伸手要錢,咋說咋好辦。可來鳳鄉是個窮鄉,日常經費都保證不了,哪有閑錢給村民交電費? 李鄉長給魏光源下了死命令,無論如何也得選出村干部,魏光源報怨說根本問題解決不了,村干部沒人當。 一天,魏光源坐在辦公桌前捉摸選舉的事,高秀生推門進來。 魏光源觀顏察色,見高家店的地痞一臉和氣,不像尋釁鬧事,不安的心落了地。 高秀生給魏光源遞來一支煙,掏出打火機點燃,魏光源說你太客氣了。高秀生抽著煙,屁股還沒坐穩,就說我想當干部。 “你想當干部?”魏主席疑惑地問。 “別當我跟你開玩笑!”高秀生嚴肅地說。 魏光源見他不茍言笑,才信了他的話。“現在都是民主選舉,過了半數才能當選。”他提醒高秀生。 高秀生胸有成竹:“高家店多半個村都姓高,只要我想當,就能把選票拉過來。” 魏光源腦袋像裝了風輪,飛快運轉著,捫心自問,這樣的人能勝任工作嗎?人們會不會擁護他?如果他當選,高家店的村民不就陷入水深火熱之中了?轉而一想,管那么多干啥?只要有人當,我就算完成了任務,至于有什么問題,那是政府的事了。想到此,他露出了一絲喜悅之色,但還想考考他: “上任后,吃水問題怎么解決?” “吃水交電錢,天經地義。哪戶不交,我看他是皮緊了。”高秀生兩眼兇光,好像不交電費的是魏光源。 無賴當有無賴的好處。村民懼他,不聽話的人也聽話了。皇帝還輪流坐呢,遑論村官呢。 魏光源說只要村民選你,你就能當,鄉里不卡脖,誰當還不是給鄉政府辦事。 高秀生聞聽此言,一臉燦爛出了人大辦公室。 四 簡約餐具圖片分割線 吳天貴與妻子見高秀生提著兩瓶酒,腋窩夾著一條煙進了家,大感意外地從炕上下了地。 高秀生將東西放在大紅柜上,滿臉堆笑地說:“冤家宜解不宜結。自從我侄兒殺了你兒子,我侄兒判了死刑,兩家就結了冰。時過境遷,我看也該和解了,國共兩黨還有合作的時候哩。” 吳天貴見妻子身子抽搐著扭過臉去,他也想盡快將高秀生趕出門,直截了當地問: “你來我家是什么意思?” 高秀生像公雞打鳴似的干笑兩聲,聳了聳肩膀說:“夜里睡不著覺,我就想咱村沒個領頭雁可不成。我把我的想法跟老魏說了,老魏很支持我,這不我就……” 吳天貴鄙夷地看了看他,眼角的余光掃了掃柜上的禮品,心里罵道:黃鼠狼給雞拜年不安好心。你想賄賂我,投你一票,門兒都沒有。他說東西你拿走,村里愛誰當誰當,我決不發表任何意見,我投棄權票。 高秀生大為光火。若在往日,他早就連諷帶譏、怒形于色了,可今天為爭取民心,只好裝孫子了:“你在咱們村德高望重,一舉一動都影響著人們的思維和行動,你棄權,還讓人們怎么投我的贊成票?” 吳天貴上上下下看了看他,看不出他當干部具備的素質,心里直犯嘀咕:倘若他用賄選的方式當上了村官兒,以他的心狠手辣,村民可就遭殃了。善良的人們啊,不要被他的糖衣炮彈擊倒,頭腦清醒一點,都投反對票,他就沒戲了。 “我的意見代表不了大家伙的意見,請你把東西拿走,我要睡覺了。”吳天貴下了逐客令。 高秀生冷冰冰地問你真不給面子?他見吳天貴將頭轉向一邊,拎起煙酒灰溜溜走了。 桂花見高秀生消失于黑漆漆的戶外,大罵丈夫:“你個一根筋,當面應承,到選舉那天,你給他畫×,他也不知道。何必得罪他!” “我就是要明著跟他干,看他能把我捏把成啥樣。”說完,吳天貴脫了衣服鉆進被窩,想起高秀生要當干部,怎么也睡不著,他不是擔心高秀生當了村官對他不利,怕的是選舉成功他的胡作非為。都是一個村的,他對高秀生的本性太了解了,他是沒利不干的人,蔫知當了村干,會做出什么損公肥私的事來。作為受黨教育多年的老黨員老干部他深知有必要去鄉里提反對意見。 翌日清晨,吃罷早飯,換了身干凈衣服,妻子問他去哪兒,他說趕個早集,騎上除了鈴鐺不響其他部件都響的自行車,歪歪扭扭向鄉政府進發。 邁進魏光源的辦公室,魏光源正在剔牙縫,一見吳天貴,始料不及地一哆嗦,他猜不透老吳此來是什么目的。 待賓主坐定,抽上煙,吳天貴婉轉地將高秀生選上村干部他不同意的話抖露出來,魏光源挖苦說民主選出來的你不同意還能尿幾丈高,你一個人總不能罷免他吧?說實在的,你們那個破爛村只要有人當就不錯了。 “難道賄選出來的,也算數?”吳天貴使出了殺手锏。 魏光源慢悠悠地說:“管它是什么方式產生的,只要是民主選舉,都不違規。” 吳天貴的嘴好似魚兒離開水,張了張,終沒說出口。他對魏光源不負責任的態度極為不滿。 魏光源見吳天貴呆坐在那兒沒有走的意思,猜度地問是不是你還想當? 吳天貴把頭搖得跟撥浪鼓似的,氣鼓鼓地說:“我當還能臨到他?村民若將他推上臺,當不到頭兒,集體財產就被他揮霍完了。” “不要枉加推測。” “你不死我不死,還有一看哩。” 魏 光源剜了他一眼。 吳天貴深知再呆下去也無趣,既然把話說透,聽不聽是他的事,作為一名舊任干部也盡到責任了,“嚯”地站起,出了人大主席室。 五 簡約餐具圖片分割線 高秀生上任了,吃水問題也解決了。 小雞不撒尿,各有各的道。高秀生收用水電費別出心裁。他不像吳天貴在任時那樣登門逐戶討要,而是在高音喇叭上一通知,限三天也好五天也好交上來,否則加罰。人們懼怕高秀生的淫威,在規定的時限內交到會計手里。公道說,高秀生當上村干部也給村民辦了幾件實事,例如將廢棄的小缸磨重新啟動承包給他人,人們加工米面再也不用到鄰村去了;認真解決房基地有爭議的幾戶,使他們心服口服,不再上訪上告;禁止羊上坡,度絕了羊去退耕還林地遭踏的現象…… 吳天貴耳聞目睹了高秀生上任后一系列善舉,不無感慨常對桂花說作為一個村干部只要心里裝著老百姓,老百姓就擁護你,你這個干部就會連選連任。妻子說但愿他一如既往,把點子用到正道,也不枉村里人投他一票。 時間過得很快,轉眼一年過去。 三月的高家店,人們除了往田里送送糞,基本處于農閑時間。 吳天貴靠在自家門前大青石板上微閉雙眼曬太陽,陽光照得他渾身暖洋洋的。 卸任后,麻纏事少了,家里那點活兒,妻子就能擺平,沒事的時候,他就圪蹴在村子最繁華的店門口,聽人侃大山,有時興致所之,也摻和幾句,十分開心。 就在他閉目養神的時候,吳天明來到他面前,他不情愿睜開眼,問:“有事嗎?” 吳天明未曾開言先噓唏,吳天貴老大不高興地說有啥事就說嘛。吳天明氣憤地說: “高秀生要賣學校!” “啥?賣學校?” 吳天貴見吳天明使勁兒點頭,才信那是真的。 六年前,吳天貴第一回當村官,他見村子小學校夏天漏雨冬天透風,十幾個讀書娃擠在教室不受用,去縣上爭取的資金重新蓋的。如今高家店小學撤并了,校舍作為村委會辦公地點仍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憑啥他要賣學校?”吳天貴追問。 “人們說他要用賣房子的錢交收不起來的電費。” 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高秀生當了一年干部,狐貍尾巴便露了出來。 按理說以他的威力,收用水電費不是個大事,怎奈他私心太重。大約在半年前,他本人就沒交,而是將虧損的錢給每戶攤開,他見人們沒反應,又將岳父家、小舅子家、七大姑八大姨家的電費全部豁免,村民見用水電費比當初他當干部那時多了起來,互相打聽,嘀咕不休,群起而問會計,會計招架不住審問,招了出來,原來他家也有好幾個月沒交了 人們不敢明的與高秀生干,暗地里沒少向鄉里奏本,魏光源不信高秀生貪圖小便宜影響正常工作,但他忽視了高秀生是用賄選的方式當上的村干部。羊毛出在羊身上,他從上任那天起就抱著“撈”的宗旨,辦得幾件順民心的事作為漂亮的外衣將丑陋的肉體遮住了。 吳天貴目光逼人地說:“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得了高秀生一點好處,就投他票,這虧吃大了!” 吳天明哭喪著臉,說: “選舉那天,他指使村里幾個賴皮在會場巡邏,不投他票還不行呢。” “我就沒投他的票,他也沒把我的球啃掉。咱們村的人都是屬核桃的,砸著吃才舒服。” 吳天貴說有所指,吳天明想起吳天貴當干部那幾年因為沒照顧上他,沒少找他麻煩,不好再說什么,走了。 六 簡約餐具圖片分割線 魏光源與高秀生沒有什么特殊關系,可最近一段時間,他連續接到好幾封匿名信,都將矛頭指向了他,大罵他這個人大主席當得不稱職,不該讓地痞擔當村官。魏光源心里也有氣,高秀生是民主選出來的,不走法定程序,縱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任命呵。他翻閱著一封封檢舉高秀生胡打狗鬧的信,也覺汗顏,若不是與鄉長李有旺有磨擦,他決不會任命高秀生為高家店的帶頭人。正是他要看李有旺的好戲,才把高秀生推到了前臺,心想你李有旺馴服高秀生,也算你小子行。事實證明,李有旺沒有管住高秀生,高秀生像一匹脫韁的野馬,橫沖直撞,拿鄉政府的令箭當雞毛撣子用。 退耕還林款和糧食直補款,按上級規定,哪級政府也不能扣留,高秀生將這兩筆錢從財政所領出,不給群眾發,而是販賣牲口。高家店的村民怨聲載道,攪得李鄉長心神不寧,見有反映高秀生問題的,頭皮發緊,眉頭皺起老高。魏光源見此情狀,幸災樂禍地唱起了京劇《智取威虎山》的段子。 前任鄉長調走,很有可能魏光源接替鄉長一職,結果半路上殺出個程咬金,比他小一圈的李有旺赴了任。 為此,魏光源心里很不平衡。他打參加工作就在基層,全縣二十三個鄉(鎮)轉了個遍,四十四歲才當上有職無權鄉人大主席。他牢騷滿腹,發出朝里沒人難做官的喟嘆。眼見比他晚提的人不是上調就是任鄉(鎮)主要領導,他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團團轉。 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魏光源的積極向上,在縣級領導眼里屬于正常現象。手握人事權的縣官都了解他干工作是一把好手,可沒一個人提名。魏光源心里清楚得很,空手套白狼在現在的社會越來越少了,只恨自己沒有多余的銀子孝敬上司。 歲月不饒人。魏光源年近五十,終于有一個伯樂可以識得千里馬,這個人便是組織部長。呂部長知人善任,將魏光源作為鄉長的人選予以提拔,沒想到遭到縣委書記的冷場,胳膊扭不過大腿,呂部長沒堅持己見,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李有旺走馬上任,對魏光源是個打擊。他把沒當成鄉長的滿腹怨氣發泄到李有旺身上,認為李有旺不從中攪和,鄉長一職非他莫屬。 高秀生當選村主任,本來鄉里還要進行考察,魏光源沒走這個程序,直接任命他為村官兒,高秀生狗帶嚼子胡勒,激起老百姓對魏主席不滿也就在所難免了。 七 簡約餐具圖片分割線 吳天貴吃罷早飯上山割柴禾去了,桂花在家收拾碗筷。 高秀生撩簾進來,桂花一愣怔。他陰森森地說:“據知情人透露,你男人糾集一伙人去鄉里告我,今天我找他報仇來了。”說完,從腰間拽出一柄明晃晃的殺豬尖刀。 桂花嚇得腿肚子朝前,結結巴巴說:“怎么可……可能呢?你當你的干部,他干他的活兒,井水不犯河水……” 高秀生吹胡子瞪眼:“少跟我來這套!”他將刀子抵到桂花的下巴,惡狠狠地問,“吳天貴在不在,我找他算賬!” 桂花一腚坐到鍋臺上,鍋臺上的泔水將她的屁股洇濕一片: “他上山不在家。” 高秀生的眼珠子轉了轉,命令她把大街門閂上。桂花明白他要做什么,哀求道:“我比你大出十幾歲,就不要這樣了吧。有看上眼的,嫂子給你串通。” “那是以后的事,現在老子就想跟你睡。”高秀生淫火上竄地說。 桂花始信高秀生假借去戶里做工作,沒少奸污小媳婦的傳聞。以高秀生的脾性,只要他提出的,沒有辦不到的。她的兩個奶子顫顫抖抖,好像兩只左沖又突的肥兔,高秀生越發春心蕩漾,迫不急待強行與之親熱起來。 吃晚飯的時候,吳天貴割柴回來,見媳婦還沒動火焰,躺在炕上蒙著被子睡大覺,他感到詫異地將她叫起,只見桂花面色蒼白,兩眼呆滯,盯住某一處久久不肯移開視線。他不問還好,一問,她像一頭暴怒的獅子向他發起了進攻: “你他媽吃飽喝足干啥不好,非要串聯一幫人去告狀!你知道高秀生今兒把老奶子怎樣了?”說到這里,她坐起來,伸長脖頸讓丈夫看,吳天貴分明看到上面有牙啃噬的印痕,紅紅的一道,醒目而特別。 “難道你被他玩……”吳天貴不愿也不敢往下說了。 桂花飲泣高歌,將吳天貴的心撕得條條縷縷的。他瞪著血紅的眼珠子,操起炕頭一把利剪就要找高秀生拼命去。桂花死死抓住他的手腕子,連哭帶勸:“高秀生打架是出了名的,你斗不過他……” 高秀生的蠻橫無理,是打架打出來的。二十幾歲的時候,曾將與他爭風吃醋的一賴皮打得半死,蹲了三年的牢。放出來的他不思悔改,變本加厲橫行鄉里,派出所也奈他不得。上了四十的高秀生雖然不怎么打架了,但他的威名還在,許多人都不敢與之較量。 “難道就讓他白白占了你的便宜?”吳天貴手中的剪子慢慢垂落于地,胸脯劇烈起伏著。 桂花微微嘆了一口氣,無奈地說:“不這樣,還能怎樣?” 吳天貴一巴掌打在自己臉上,堅決地說:“不能便宜那混蛋,我要告他去!”說完,邁著把大地都震顫的大步沖出了屋子。 桂花追出門外,眼見丈夫的身影消失于村子的盡頭,靠在大青石板上號啕大哭。她的哭引來眾鄉親的問詢,人們從她嘴里搗出高秀生奸污了她的話,一時群情激憤,大罵高秀生是披著羊皮的狼,當場就有人提出將他罷免,還有人說把他趕出高家店…… 桂花見這么多人給她撐腰做主,腰桿挺直了,抬頭見天邊一抹晚霞將云彩燒紅了。 END 作者簡介 張玉武,1968年生,河北省赤城縣人。 +10我喜歡
“三十八年過去,彈指一揮間……” 謹以此文紀念知識青年上山下鄉50周年 總647#似水流年之青蔥歲月系列十(05)# 乍暖還寒時候 (中篇小說) 一九八零年十一月十日 接上篇 一路上,舒令怡向他匯報隊上的情況。王隊長起早貪黑,村東村西地跑,可積極著呢!就是社員有點不爭氣,好像這莊稼是給隊長種的:出工稀稀落落、沒精打彩的,真急死個人。說到這里,姑娘那好看的眉毛蹙了起來,一臉的焦灼。 張泓釋然一笑,安慰地說:“會有辦法的。”一面岔開問道:“今晚的飯派到了誰家?” “派飯?什么叫派飯?隊長安排我們就在一家吃啊!嫂子待人可熱呼了。” “噢,——……是這樣。”張泓不說話了。 不知不覺,已經來到了隊部。看屋老頭叭在裂著大縫的桌子上,守著一臺陳舊的搖柄電話在打瞌睡。舒令怡示意張泓放下被包,隨后躡手躡腳地走出了隊部。 他走在坑坑洼洼的村道上,覺得這是一個沉悶的屯子。歪歪斜斜的土房,星散在土路兩旁,橫不成線、豎不成行。披著薄薄一層茅草的房頂上,伸出了散著炊煙的筒子,有土坯砌的,也有兩只掉底的舊水桶接起來的;再富貴一點的,是用了一截打井剩下的缸管。家家前后園子里,只剩下一些瓜藤匍匐在地,黃煙被扒去了葉子,剩下桿子孤零零地在寒風中瑟縮發抖。 “那是王隊長家。”舒令怡對他說。張泓順著指示的方向,陡然將目光射定了這座在蕭條破敗的村落中,分外突出的建筑——又高又大的三間房,屋頂上的苫房草足有兩拃來厚,砌磚的煙筒,一米高的石頭墻基,“前浪后不浪”的房身,水泥窗臺,一色五扇的大南窗,木框都刷著天藍色的油漆。夕陽殘照映在玻璃上,反射出一片血也似的紅光。 “值個萬八千塊錢吧!”他掂量著。 “喲,萬八千?”舒令怡咋了一下舌頭,不禁把肩膀一聳。 “甚至還要多一些。” …… “這就是我們吃飯的老王家。”走到緊挨著這座顯赫建筑物的一個院套,舒令怡推開了拳頭粗的柞木條編起來的柵欄門。 “噯喲,是袁兒回來了嗎?快進屋——”隨著這陣甜蜜蜜的招呼,走出了一位四十來歲白凈臉蛋的婦女。她穿著一件緊繃著胸脯的大絨上衣,腳上蹬一雙帶繡花的棉鞋,一步三搖、妖妖道道地走上前來。 “哎喲喲喲……”她驚訝了,“這可是打哪來的稀客喲……八成是新來的領導吧?”她的臉并不難看,但堆滿了難看的諂媚的笑。 “嫂子,他是我們工作隊長張泓書記。”舒令怡從旁介紹道,并沒有注意到張泓的表情。 “哎呀,叫我說的”。女人一拍大腿,“原來是書記官到俺家了!上咱這兒來吃飯的書記,走馬燈似地,你來我往,還真的不少。可這樣年輕的,倒是頭一回喲!” 女人一點也不外道地伸出雙手,把張泓顯得纖細修長的手拿過來,結結實實地握住了。張泓分明感到對方那種攫取的目光,他馬上掙脫出來,但是晚了,手上已經起了一種滑膩膩的感覺。 “張書記,俺們這兒可比不上你們大城市里潔凈,您可別嫌乎……”女人殷勤地將他們讓進了東屋,“她怎么啥都知道呢?”張泓不禁有點心煩地想道。 一踏進門檻,他遲疑的步子,就馬上立定在屋地中央了。一幅非常富貴氣派的擺設,映入了張泓的眼簾:正面明晃晃的兩面大鏡,一字排開;緊挨著的,兩邊各一的條幅鏡框里,鑲滿了密密麻麻的相片。南炕梢放著新刷油的炕琴和被柜,一直頂住了天棚。彎子炕上是黃笸羅面的瓷磚條琴。條琴上,擠滿了臺式收音機、三五牌座鐘,各種各樣的脂粉盒,梳妝鏡、茶杯、茶壺和皂盒。連過去的北炕梢上,是一對箱子。四圍的墻刷得雪白,屋地鋪著磚。 “來、來、來!快上炕里,剛出鍋的餃子,趁熱吃。”女人端上了滿滿的盤子,里外屋穿梭般地走動,一邊招呼在外屋幫著燒火的舒令怡,一面取來了早在臼子里搗得爛爛的蒜泥。 “這有燙好的。”女人拿上來一個描了金的的小酒壺和兩個酒盅。“張書記,你們成天在外面辛苦,到俺這,就趕到家一樣,喝口暖和暖和身子。”說著就捏起酒壺要倒。 “不,嫂子,老王大哥呢?這陣兒還沒收工嗎?” “嗨,他嘛,得一會兒呢。咱們先吃起來,吃餃子不耽誤喝酒,”說著她又要動作。 張泓伸手做了一個拒絕的表示:“不是年節,我不喝酒,決不要倒!” 他的臉色很嚴肅。在那些吃喝成風的年月里,在那塊吃喝成風的土地上,客氣的拒絕就等于接受。這不僅在于張泓,就是立身炕沿的這個女人,心中也很明白。過去的書記官她接待的有多多少,誰還不是半推半就、最后都端起了酒盅?俗話說:“酒壺一端,政策放寬”,每次黑魚屯局勢的轉危為安,還不得歸功于我——“王八德”媳婦手中的酒盅和眼底的波瀾! “可是今天這位……卻好像有點來者不善……”一股凜然的正氣、兩道冷峻的目光,鎮住了她多年勸酒生涯練就的自然。她抽動著嘴唇,卻一個字也沒有說出來。 “張隊長,咱們就先吃飯吧!”按照事先說定的招呼,舒令怡發話了。 他吃著,但沒有覺出味道來,疑慮集中了他的全副思考,這壓抑了他的食欲。對他來說,現在更需要抽煙。 “也不知道您的口輕口重,可還行?”女人恢復了常態,說著脫鞋上了炕。像一下子沒坐穩,便把身子歪斜著靠上了張泓。她伸手扶了一把他盤坐著的大腿,這才坐正了自己的身子。 張泓分明感到了這個熱烘烘身體的依靠。他一轉臉,便見到女人正沖他含義復雜地笑著。餃子蒸騰著熱氣,炕上像是蒙上了一層霧,炕桌對面的舒令怡的面目也不甚清晰。于是,他明白這個女人的用心了。 他放下筷子,接著掏出錢包,點清了票子放在炕桌上,就要下地。 女人的臉,不自然地抽動著。沒有片刻的游移,女人右手麻利地抓起了票子,左手扯定了張泓的袖口:“怎么,還給錢?那可不行!別說工作隊上門來,就是不認得的,過路趕上飯,還不得招待一頓好吃的?”她正要把錢塞到他手里,張泓敏捷地躲開了 “你就別給我來這一套了!”在張泓近于威嚴的口氣下,胖女人不由自主地松開了手。一張一元的票子包著一斤糧票,掉在鋪炕的刷了綠油漆的纖維板上。女人傷心地噓唏起來。 …… “你為什么要這樣!”舒令怡急匆匆地從身后趕上來。 張泓指著四下跑散的孩子們,頭也沒回地說:“小心第一步,就掉進了……” 他的話沒說完,便被自己的思考打斷了。 (下接之六) +10我喜歡
限會員,要發表迴響,請先登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