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征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是台中稅務爭議解決及訴訟最佳稅務後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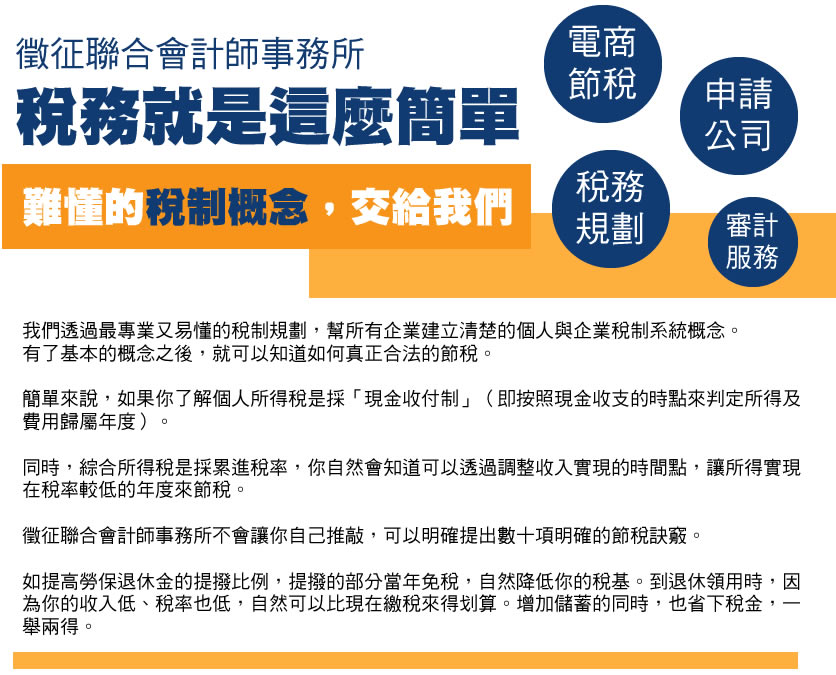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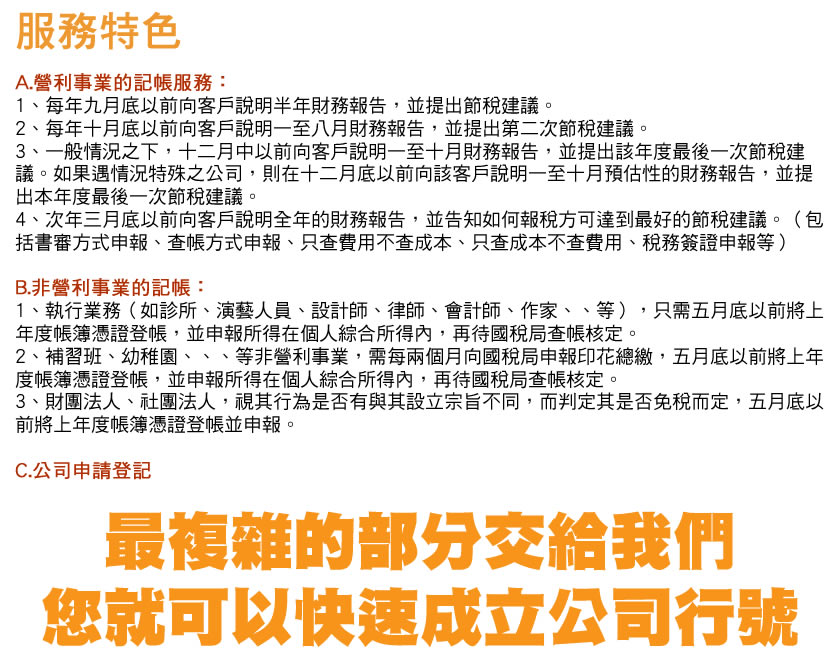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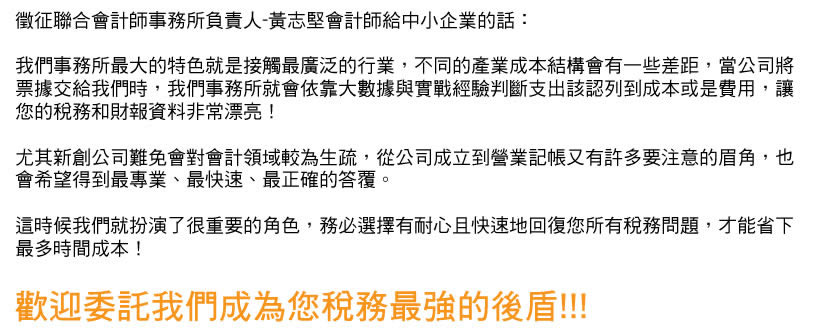
台中北區申請免用統一發票會計師事務所, 台中中區人才資本管理會計服務推薦, 台中潭子國內稅務諮詢
楊絳:林奶奶 林奶奶小我三歲。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她忽然到我家打門,問我用不用人。我說:“不請人了,家務事自己都能干。”她嘆氣說:“您自己都能,可我們吃什么飯呀?”她介紹自己是“給家家兒洗衣服的”。我就請她每星期來洗一次衣服。當時大家對保姆有戒心。有人只因為保姆的一張大字報就給揪出來掃街。林奶奶大大咧咧地不理紅衛兵的茬兒。她不肯胡說東家的壞話,大嚷:“那哪兒成?我不能瞎說呀!”許多人家不敢找保姆,就請林奶奶去做零工。 我問林奶奶:“干嗎幫那么多人家?集中兩三家,活兒不輕省些嗎?”她說做零工“活著些”。這就是說:自由些,或主動些;干活兒瞧她高興,不合意可以不干。比如說吧,某太太特難伺候,氣得林奶奶當場左右開弓,打了自己兩個嘴巴子。這倒像舊式婦女不能打妯娌孩子的屁股,就打自己孩子的屁股。據說,那位太太曾在林奶奶干活兒的時候把鐘撥慢“十好幾分鐘”(林奶奶是論時記工資的),和這種太太打什么交道呢!林奶奶干了這一行,受委屈是家常便飯,她一般是吃在肚里就罷了,并不隨便告訴人。她有原則:不搬嘴弄舌。 她倒是不怕沒有主顧,因為她干活兒認真,衣服洗得干凈;如果經手買什么東西,分文也不肯占人家的便宜。也許她稱得上“清介”“耿直”等美名,不過這種詞兒一般不用在渺小的人物身上。人家只說她“人靠得住,脾氣可倔”。 她天天哈著腰坐在小矮凳上洗衣,一年來,一年去,背漸漸地彎得直不起來,不到六十已經駝背,身上雖瘦,肚皮卻大,其實那是徒有其表。只要掀開她的大襟,就知道衣下鼓鼓囊囊一大嘟嚕是倒垂的褲腰。一重重的衣服都有小襟,小襟上都釘著口袋,一個、兩個或三個:上一個,下一個,反面再一個,大小不等,顏色各異。衣袋深處裝著她的家當:布票,糧票,油票,一角二角或一元二元或五元十元的錢。她分別放開,當然都有計較。我若給她些什么,得在她的袋口別上一兩只大別針,或三只小的,才保住東西不往外掉。 我曾問起她家的情況。她的丈夫早死了,她是青年守寡的。她伺候了婆婆好多年,聽口氣,對婆婆很有情意。她有一子一女,都已成家。她把兒子栽培到高中畢業。女兒呢,據說是“他嫂子的,四歲沒了媽,吃我的奶”。死了的嫂子大概是她的妯娌。她另外還有嫂子,她曾托那嫂子給我做過一雙棉鞋。 林奶奶得意揚揚抱了那雙棉鞋來送我,一再強調鞋子是按著我的腳寸特制的。我恍惚記起她哄我讓她量過腳寸,可是那雙棉鞋顯然是男鞋的尺碼。我謝了她,領下禮物,就讓給默存穿。想不到非但他穿不下,連阿圓都穿不下。我自己一試,恰恰一腳穿上,正是按著我的腳寸特制的呢!那位嫂子準也按著林奶奶的囑咐,把棉花絮得厚厚的,比平常的棉鞋厚三五倍不止。簇新的白布包得厚厚的,用麻線納得密密麻麻,比牛皮底還硬。我雙腳穿上新鞋,就像猩猩穿上木屐,行動不得;穩重地站著,兩腳和大象的腳一樣肥碩。 林奶奶老家在郊區,她在城里做零工,活兒重些,工錢卻多。她多年省吃儉用,攢下錢在城里置了一所房子,花了一二千塊錢呢。恰逢文化大革命,林奶奶趕緊把房“獻”了。她深悔置房子“千不該、萬不該”,卻倒眉倒眼地笑著用中間三個指頭點著胸口說:“我成了地主資本家!我!我!”我說:“放心,房子早晚會還給你,至少折了價還。”我問她:“你想‘吃瓦片兒’(依靠出租房屋生活)嗎?”她不搭理,只說“您不懂”,她自有她的道理。 我從干校回來,房管處已經把她置的那所房子拆掉,另賠了一間房給她——新蓋的,很小,我去看過,里面還有個自來水龍頭,只是沒有下水道。林奶奶指著窗外的院子和旁邊兩間房說:“他住那邊。”“他”指拆房子又蓋房子的人,好像是個管房子的,林奶奶稱為“街坊”。她指著“街坊”門前大堆木材說:“那是我的,都給他偷了。”她和“街坊”為那堆木材成了冤家。所以林奶奶不走前院,卻從自己房間直通街道的小門出入。 她曾邀一個親戚同住,彼此照顧。這就是林奶奶的長遠打算。她和我講:“死倒不怕,”——吃苦受累當然也不怕,她一輩子不就是吃苦受累嗎——“我就怕老來病了,半死不活,給撂在炕上,叫人沒人理,叫天天不應。我眼看著兩代親人受這個罪了……人說‘長病沒有孝子’……孝子都不行呢……”她不說自己沒有孝子,只嘆氣說“還是女兒好”。不過在她心目中,女兒當然也不能充孝子。 她和那個親戚相處得不錯,只是房間太小,兩人住太擠。她屋里堆著許多破破爛爛的東西,還擺著一大排花盆——林奶奶愛養花,破瓷盆、破瓦盆里都種著鮮花。那個親戚住了些時候走了,我懷疑她不過是圖方便,難道她真打算老來和林奶奶做伴兒? 那年冬天,林奶奶穿著個破皮背心到我家來,要把皮背心寄放在我家。我說:“這天氣,正是穿皮背心的時候,藏起來干嗎?”她說:“怕被人偷了。”我知道她指誰,忍不住說道:“別神經了,誰要你這件破背心呀!”她氣呼呼地忍了一會,咕噥說:“別人我還不放心呢。”我聽了忽然聰明起來。我說:“哦,林奶奶,里面藏著寶吧?”她有氣,可也笑了,還帶幾分被人識破的不好意思。我說:“難怪你這件背心鼓鼓囊囊的。把你的寶貝掏出來給我,背心你穿上,不好嗎?”她大為高興,立即要了一把剪刀,拆開背心,從皮板子上揭下一張張存款單。我把存單的賬號、款項、存期等一一登記,封成一包,藏在她認為最妥當的地方。林奶奶切切叮囑我別告訴人,她穿上背心,放心滿意而去。 可是日常和仇人做街坊,林奶奶總是放心不下。她不知怎么丟失了二十塊錢,懷疑“街坊”偷了。也許她對誰說了什么話,或是在自己屋里嘟嚷,給“街坊”知道了。那“街坊”大清早等候林奶奶出門,趕上去狠狠的打了她兩巴掌,騎車跑了。林奶奶氣得幾乎發瘋。我雖然安慰了她,卻埋怨她說,“準是你上廁所掉茅坑里了,怎能平白冤人家偷你的錢呢?”林奶奶信我的話,點頭說:“大概是掉茅坑里了。”她是個孤獨的人,多心眼兒當然難免。 我的舊保姆回北京后,林奶奶已不在我家洗衣,不過常來我家作客。她挨了那兩下耳光,也許覺得孤身住在城里不是個了局。她換了調子,說自己的“兒子好了”。連著幾年,她為兒子買磚、買瓦、買木材,為他蓋新屋。是她兒子因為要蓋新屋,所以“好了”;還是因為他“好了”,所以林奶奶要為他蓋新屋?外人很難分辨,反正是同一回事吧?我只說:“林奶奶,你還要蓋房子啊?”她向我解釋:“老來總得有個窩兒呀。”她有心眼兒,早和兒子講明:新房子的套間——預定她住的一間,得另開一門,這樣呢,她單獨有個出入的門,將來病倒在炕上,村里的親戚朋友經常能去看看她,她的錢反正存在妥當的地方呢,她不至于落在兒子、媳婦手里。 一天晚上,林奶奶忽來看我,說:“明兒一早要下鄉和兒子吵架去”。她有一二百元銀行存單,她兒子不讓取錢。兒子是公社會計,取錢得經他的手。我教林奶奶試到城里儲蓄所去轉期,因為郊區的儲蓄所同屬北京市。我為她策劃了半天,她才支支吾吾吐出真情。原來新房子已經蓋好了。她講明要另開一門,她兒子卻不肯為她另開一門。她這回不是去撈回那一二百塊錢,卻是借這筆錢逼兒子在新墻上開個門。我問:“你兒子肯嗎?”她說:“他就是不肯!”我說,“那么,你老來還和他同住?”她發狠說,“非要他開那個門不可。”我再三勸她別再白慪氣,她嘴里答應,可是顯然早已打定主意。 她回鄉去和兒子大吵,給兒媳婦推倒在地,騎在她身上狠狠地揍了一頓,聽說腰都打折了。不過這都只是傳聞。林奶奶見了我一句沒說,因為不敢承認自己沒聽我的話。她只告訴我經公社調停,撈回了那一小筆存款。我見她沒打傷,也就沒問。林奶奶的背越來越駝,干活兒也沒多少力氣了。幸虧街道上照顧她的不止一家。她又舊調重彈“還是女兒好”。她也許怕女兒以為她的錢都花在兒子身上了,所以告訴了女兒自己還有多少存款。從此后,林奶奶多年沒有動用的存款,不久就陸續花得只剩了一點點。原來她又在為女兒蓋新屋。我末了一次見她,她的背已經彎成九十度。翻開她的大襟,小襟上一只只口袋差不多都是空的,上面卻別著大大小小不少別針。不久林奶奶就病倒了,不知什么病,吐黑水——血水變黑的水。街道上把她送進醫院,兒子得信立即趕來,女兒卻不肯來。醫院的大夫說,病人已沒有指望,還是拉到鄉下去吧。兒子回鄉找車,林奶奶沒等車來,當晚就死了。我相信這是林奶奶生平最幸運的事。顯然她一輩子的防備都是多余了。 林奶奶死后女兒也到了,可是不肯為死人穿衣,因為害怕。她說:“她又不是我媽,她不過是我的大媽。我還恨她呢。我十四歲叫我做童養媳,嫁個傻子,生了一大堆傻子……”(我見過兩個并不傻,不過聽說有一個是“缺心眼兒”的)。女兒和兒子領取了林奶奶的遺產:存款所(www.lz13.cn)余無幾,但是城里的房產聽說落實了。據那位女兒說,他們鄉間的生活現在好得很了,家家都有新房子,還有新家具,大立柜之類誰家都有,林奶奶的破家具只配當劈柴燒了。 林奶奶火化以后,她娘家人堅持辦喪事得擺酒,所以熱熱鬧鬧請了二十桌。散席以后,她兒子回家睡覺,忽發現鍋里蟠著兩條三尺多長、滿身紅綠斑紋的蛇。街坊聽到驚叫,趕來幫著打蛇。可是那位兒子忙攔住說“別打,別打”,廣開大門,把蛇放走。林奶奶的喪事如此結束。鍋里蟠兩條蛇,也不知誰惡作劇;不過,倒真有點像林奶奶干的。 一九八四年四月 楊絳作品集_楊絳文集 楊絳:小吹牛 楊絳:我們仨分頁:123
專注:用少量時間達成大目標 之前,我寫了有關于我最喜歡的時間管理的秘訣的內容:也就是說,你要認識到時間的使用是一種選擇。那么多的日子和那么多個禮拜都只是張白紙。如果你不喜歡你所選擇的填滿它們的方式,那么,隨著時間的推移,你可以選擇不同的方式。 有幾位讀者給我寫了信,他們讓我知道,雖然這個想法在抽象的層面上來說是非常好的,但是他們現在的生活依然還是老樣子。而眼下,他們只是東有幾分鐘時間西有幾分鐘時間,卻有著大的目標要實現。因此,我能夠給身處在他們這種情況中的人們什么建議呢? 為了對這個問題提供幫助,我求助于了小說家卡米爾.諾埃.佩格(Camille Noe Pagán)。她的新小說《遺忘的藝術》--講述了兩個朋友以及他們是如何應對其中一個人的創傷性顱腦損傷(traumatic brain injury)的故事--已經由杜登出版社(Dutton)上市出版了。通常情況下,我們會認為作者們都是在某些被遺忘的高塔上長期進行著他們的創作。然而,諾埃.佩格卻是設法利用她的全職新聞工作和照顧她的兩個孩子(年齡分別是3歲和6個月)之間僅存的15分鐘來努力完成她的寫作的。如果你有一個大的目標要達成,卻有一個排滿了事項的日程安排的話,那就嘗試一下她的能充分利用你所擁有的任何時間的秘訣: 1、只要著手去做。"正像大多數的事情一樣,在很短的時間里進行工作是一項可以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被磨練出來的技能。"諾埃.佩格說,"我喜歡利用我可以投入進去的一小塊時間去完成任務--比如說,計算我的收支平衡或是為我所寫的最后一章的內容進行快速編輯。(勵志文章 www.lz13.cn)"如果你想要等待最佳時機,那它將永遠都不會到來。但是,如果你開始去做了,工作就會養育它自身。"開始一個項目需要某些非常強大的動力,所以,當你下一次坐下來再開始工作時,你知道了你并不是從零開始。這會破除掉你的心理障礙,"她說。 2、最少化讓你分心的事情并制定計劃。15分鐘對于寫些東西來說是足夠的,但它并不足夠你既進行寫作又查看你的臉譜社交網站(facebook)。"我是一名電子郵件成癮者,"諾埃o佩格說,"我喜歡閱讀并快速回復電子郵件。這就像是瞬間獲得的成就,這會讓我的收件箱不被未讀郵件填滿。"然而,"就和大多數人一樣,我可以一整天都坐在那里處理電子郵件卻仍然不能完整地停留在這件事上,因此,我訓練自己,當我想要完成某些事情的時候,就最小化或關掉我的電子郵件的窗口;否則,收到新的電子郵件的提示音會太過于迷人了。同樣地,我也會留出一些特定的時間,我知道我會利用這段時間去做一些分散注意力的活動;例如,我在工作日的午餐時間和下午3點左右有一段間歇時間,那時我會讓自己登錄上推特微博(Twitter)看看。" 3、給自己一枚金星。每次你很好地利用了不到15分鐘的一小塊時間時,就給你自己一份小小的獎勵。"我非常熱衷于使用復選框和圖表;我們對于查驗無誤在已完成的事情上做標記都有一種固有的內在動力,"諾埃.佩格說"就我的小說來說,我打印了80張紙,每張紙上都印著小小的代表了只能寫1000個字的'1ks'的字樣(8萬字是一部小書的平均長度),我把這些紙都放在一個箱子里,然后把這個箱子放在我的辦公桌上。我之后就這里寫200字又那里寫200字,這看上去好像并沒有多少內容,但是,我知道,每次我這樣做的時候,我讓自己距離完成那些1ks之一就又更近了一步。" 4、不要把完美作為目標。把完成該事項當作目標。當你擁有了世界上所有的時間時,你可能首先會做的并不是懷疑你自己。諾埃.佩格說,只有幾分鐘的時間可以幫助她"壓制我內在的批評欲",因此她能夠在不到五個月的時間里就寫出了小說的底稿。"當然,它需要再修改加工--所有的初稿都需要--但我已經清除了主要的障礙,這正是先把小說寫出來的主要意義,"她說。然后,就是利用小塊的空余時間對它進行編輯了。 你已經利用15分鐘的小塊時間實現了怎樣的大的目標?分頁:123
季羨林:二月蘭 轉眼,不知怎樣一來,整個燕園竟成了二月蘭的天下。 二月蘭是一種常見的野花。花朵不大,紫白相間。花形和顏色都沒有什么特異之處。如果只有一兩棵,在百花叢中,決不會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但是它卻以多勝,每到春天,和風一吹拂,便綻開了小花;最初只有一朵,兩朵,幾朵。但是一轉眼,在一夜間,就能變成百朵,千朵,萬朵。大有凌駕百花之上的勢頭了。 我在燕園里已經住了四十多年。最初我并沒有特別注意到這種小花。直到前年,也許正是二月蘭開花的大年,我驀地發現,從我住的樓旁小土山開始,走遍了全園,眼光所到之處,無不有二月蘭在。宅旁,籬下,林中,山頭,土坡,湖邊,只要有空隙的地方,都是一團紫氣,間以白霧,小花開得淋漓盡致,氣勢非凡,紫氣直沖云霄,連宇宙都仿佛變成紫色的了。 我在迷離恍惚中,忽然發現二月蘭爬上了樹,有的已經爬上了樹頂,有的正在努力攀登,連喘氣的聲音似乎都能聽到。我這一驚可真不小:莫非二月蘭真成了精了嗎?再定睛一看,原來是二月蘭叢中的一些藤蘿,也正在開著花,花的顏色同二月蘭一模一樣,所差的就僅僅只缺少那一團白霧。我實在覺得我這個幻覺非常有趣。帶著清醒的意識,我仔細觀察起來:除了花形之外,顏色真是一般無二。反正我知道了這是兩種植物,心里有了底,然而再一轉眼,我仍然看到二月蘭往枝頭爬。這是真的呢?還是幻覺?一由它去吧。 自從意識到二月蘭存在以后,一些同二月蘭有聯系的回憶立即涌上心頭。原來很少想到的或根本沒有想到的事情,現在想到了;原來認為十分平常的瑣事,現在顯得十分不平常了。我一下子清晰地意識到,原來這種十分平凡的野花竟在我的生命中占有這樣重要的地位。我自己也有點吃驚了。 我回憶的絲縷是從樓旁的小土山開始的。這一座小土山,最初毫無驚人之處,只不過二三米高,上面長滿了野草。當年歪風狂吹時,每次“打掃衛生”,全樓住的人都被召喚出來拔草,不是“綠化”,而是“黃化”。我每次都在心中暗恨這小山野草之多。后來不知由于什么原因,把山堆高了一兩米。這樣一來,山就頗有一點山勢了。東頭的蒼松,西頭的翠柏,都仿佛恢復了青春,一年四季,郁郁蔥蔥。中間一棵榆樹,從樹齡來看,只能算是松柏的曾孫,然而也枝干繁茂,高枝直刺入蔚藍的晴空。 我不記得從什么時候起我注意到小山上的二月蘭。這種野花開花大概也有大年小年之別的。碰到小年,只在小山前后稀疏地開上那么幾片。遇到大年,則山前山后開成大片。二月蘭仿佛發了狂。我們常講什么什么花“怒放”,這個“怒”字用得真是無比地奇妙。二月蘭一“怒”,仿佛從土地深處吸來一股原始力量,一定要把花開遍大千世界,紫氣直沖云霄,連宇宙都仿佛變成紫色的了。 東坡的詞說:“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此事古難全。”但是花們好像是沒有什么悲歡離合。應該開時,它們就開;該消失時,它們就消失。它們是“縱浪大化中”,一切順其自然,自己無所謂什么悲與喜。我的二月蘭就是這個樣子。 然而,人這個萬物之靈卻偏偏有了感情,有了感情就有了悲歡。這真是多此一舉,然而沒有法子。人自己多情,又把情移到花,“淚眼問花花不語”,花當然“不語”了。如果花真“語”起來,豈不嚇壞了人!這些道理我十分明白。然而我仍然把自己的悲歡掛到了二月蘭上。 當年老祖還活著的時候,每到春天二月蘭開花的時候,她往往拿一把小鏟,帶一個黑書包,到成片的二月蘭旁青草叢里去搜挖薺菜。只要看到她的身影在二月蘭的紫霧里晃動,我就知道在午餐或晚餐的餐桌上必然彌漫著薺菜餛飩的清香。當婉如還活著的時候,她每次回家,只要二月蘭正在開花,她離開時,她總穿過左手是二月蘭的紫霧,右手是湖畔垂柳的綠煙,匆匆忙忙走去,把我的目光一直帶到湖對岸的拐彎處。當小保姆楊瑩還在我家時,她也同小山和二月蘭結上了緣。我曾套宋詞寫過三句話:“午靜攜侶尋野菜,黃昏抱貓向夕陽,當時只道是尋常。”我的小貓虎子和咪咪還在世的時候,我也往往在二月蘭叢里看到她們:一黑一白,在紫色中格外顯眼。 所有這些瑣事都是尋常到不能再尋常了。然而,曾幾何時,到了今天,老祖和婉如已經永遠永遠地離開了我們。小瑩也回了山東老家。至于虎子和咪咪也各自遵循貓的規律,不知鉆到了燕園中哪一個幽暗的角落里,等待死亡的到來。老祖和婉如的走,把我的心都帶走了。虎子和咪咪我也憶念難忘。如今,天地雖寬,陽光雖照樣普照,我卻感到無邊的寂寥與凄涼。回憶這些往事,如云如煙,原來是近在眼前,如今卻如蓬萊靈山,可望而不可即了。 對于我這樣的心情和我的一切遭遇,我的二月蘭一點也無動于衷,照樣自己開花。今年又是二月蘭開花的大年。在校園里,眼光所到之處,無不有二月蘭在。宅旁,籬下,林中,山頭,土坡,湖邊,只要有空隙的地方,都是一團紫氣,間以白霧,小花開得淋漓盡致,氣勢非凡,紫氣直沖霄漢,連宇宙都仿佛變成紫色的了。 這一切都告訴我,二月蘭是不會變的,世事滄桑,于它如浮云。然而我卻是在變的,月月變,年年變。我想以不變應萬變,然而辦不到。我想學習二月蘭,然而辦不到。不但如此,它還硬把我的記憶牽回到我一生最倒霉的時候。在十年浩劫中,我自己跳出來反對北大那一位“老佛爺”,被抄家,被打成了“反革命”。正是在二月蘭開花的時候,我被管制勞動改造。有很長一段時間,我每天到一個地方去撿破磚碎瓦,還隨時準備著被紅衛兵押解到什么地方去“批斗”,坐噴氣式,還要挨上一頓揍,打得鼻青臉腫。可是在磚瓦縫里二月蘭依然開放,怡然自得,笑對春風,好像是在嘲笑我。 我當時日子實在非常難過。我知道正義是在自己手中,可是是非顛倒,人妖難分,我呼天天不應,叫地地不答,一腔義憤,滿腹委屈,毫無人生之趣。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成了“不可接觸者”,幾年沒接到過一封信,很少有人敢同我打個招呼。我雖處人世,實為異類。 然而我一回到家里,老祖、德華她們,在每人每月只能得到恩賜十幾元錢生活費的情況下,殫思竭慮,弄一點好吃的東西,希望能給我增加點營養;更重要的恐怕還是,希望能給我增添點生趣。婉如和延宗也盡可能地多回家來。我的小貓憨態可掬,偎依在我的身旁。她們不懂哲學,分不清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人視我為異類,她們視我為好友,從來沒有表態,要同我劃清界限。所有這一些極其平常的瑣事,都給我帶來了無量的安慰。窗外盡管千里冰封,室內卻是暖氣融融。我覺得,在世態炎涼中,還有不炎涼者在。這一點暖氣支撐著我,走過了人生最艱難的一段路,沒有墮入深澗,一直到今天。 我感覺到悲,又感覺到歡。 到了今天,天運轉動,否極泰來,不知怎么一來,我一下子成為“極可接觸者”,到處聽到的是美好的言辭,到處見到的是和悅的笑容。我從內心里感激我這些新老朋友,他們絕對是真誠的。他們鼓勵了我,他們啟發了我。然而,一回到家里,雖然德華還在,延宗還在,可我的老祖到哪里去了呢?我的婉如到哪里去了呢?還有我的虎子和咪咪一世到哪里去了呢?世界雖照樣朗朗,陽光雖照樣明媚,我卻感覺異樣的寂寞與凄涼。 我感覺到歡,不感覺到悲。 我年屆耄耋,前面的路有限了。幾年前,我寫過一篇短文,叫《老貓》,意思很簡明,我一生有個特點:不愿意麻煩人。了解我的人都承認。難道到了人生最后一段路上我就要改變這個特點嗎?不,不,不想改變。我真想學一學老貓,到了大限來臨時,鉆到一個幽暗的角落里,一個人悄悄地離開人世。 這話又扯遠了。我并不認為眼前就有制定行動計劃的必要。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而且我的健康情況也允許我去做。有一位青年朋友說我忘記了自己的年齡。這話極有道理。可我并沒有全忘。有一個問題我還想弄弄清楚哩。按說我早已到了“悲歡離合總無情”的年齡,應該超脫一點了。然而在離開這個世界以前,我還有一件心事:我想弄清楚,什么叫“悲”?什么又叫“歡”?是我成為“不可接觸者”時悲呢?還是成為“極可接觸者”時歡?如果沒有老祖和婉如的逝世,這問題本來是一清二白的,現在卻是悲歡難以分辨了。我想得到答復。我走上了每天必登臨幾次的小山,我問蒼松,蒼松不語;我問翠柏,翠柏不答。我問三十多年來親眼目睹我這些悲歡離合的二月蘭,這也沉默不語,兀自萬朵怒放,笑對春風,紫氣直沖霄漢。 1993年6月11日寫完 季羨林作品_季羨林散文集 季羨林語錄 季羨林:開卷有益分頁:123
ACC711CEV55CE
台中大雅電商稅務諮詢
台中北區會計及薪資委外 台中中區遺產規劃 暫繳稅額怎麼計算
下一則: 台中大里公司投資及併購 台中西屯營業登記會計師事務所 算薪水了,員工勞、健保負擔部份該怎麼扣呢
限會員,要發表迴響,請先登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