蟬的多數年月活在幽暗濕冷的土壤下,承受著壓力、孤單;直等到多年後時日滿足,復活重生,用新生的身體飛向天際。
清晨五點,房間內擠滿了陰鬱與寒意,幽暗的靜謐包裹著世界,只剩風聲在耳邊低語。
手機鬧鈴敲碎一切,沒有猶豫,身體果決地從被窩中破繭而出。我打開燈,換穿上班服裝,簡單盥洗後便出門。
昏黃路燈映照雨絲斜飛的軌跡,拉緊風衣帽兜,雨珠在防水層表面凝聚成一層薄霧。即便坐進駕駛座,用力關上車門,吐出的白霧依舊昭示著清晨的寒冷。機械沒有生命,卻承載著唯一清醒的靈魂,目的地是教會,要在六點前抵達。

生命此前未曾如此虔誠,只因遭遇無法解決的難題,偶然間聽到見證,說晨禱能幫助渡過生命低谷,便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情,開始了晨禱生活。
第一次晨禱,沒堅持兩週就放棄了。
嘗試過清晨讀經禱告,但總是昏昏欲睡,於是跟隨教會的在線晨禱。影片能在網路平台重播,為何非得要清晨起床?
提早起床,晨禱卻索然無味。
三個月後的某天,我讀到了撒母耳記,哈拿在禱告中交託困難,把淚水留在昨日,在信靠中生活。如果自己能有這樣的信心就好了,這段時間就是用工作填塞時間,研讀艱澀的專業書籍,藉此來麻痹曠野時光。
隔天清晨六點半醒來,慵懶地躺在床上玩手機,看到了教會的晨禱直播。牧師正導讀哈拿的禱告,「哈拿付上代價來禱告,弟兄姊妹們,你們也要付上代價來晨禱。清晨的禱告,神必睜眼看、側耳聽。」
隔天,我便開始第二次晨禱。
駛離郊區,駛向市區,世界靜谧得只剩下詩歌和禱告。白日裡喧囂的街道,此刻彷彿沉睡的嬰孩,令人陌生。
少數人開始了一天的忙碌,車輛間保持著友好的速度和距離,都是難得早起,沒有爭競的必要。
自己不是熱衷禱告的人,宿舍的在線晨禱只是便宜行事。安靜禱告和詩歌敬拜時,我不是在賴床就是在盥洗,等牧師開始導讀經文,才穿著睡衣坐下來;等牧師帶領結束禱告時,便起身換衣,準備上班。
常常將手機放在枕頭旁,用閉目養神的方式聽晨禱,多是半夢半醒、昏昏沉沉。
好了,有晨禱,盡力了。
這就是每天的晨禱態度。

三個月後,牧師突然宣佈,晨禱開始進入新活動,號召一百間教會、一萬人來連線晨禱,連續一百天不間斷、不休息。
沒有考慮太久便決定參加。
身陷困境泥淖已經太久,自前妻提出離婚訴求後,季節便走進寒冬。
我認識哲哲的時間足以讓一個嬰孩長大成人。前段時間,他走進了家庭風暴的低潮。他用習慣的強硬態度處理問題,卻讓自己逐步走向萬劫不復。他和教會同時向我尋求協助。
能做的只有陪伴。聽他那好為人師的詭異價值觀,陪伴他在憤怒與懺悔的情緒間反覆波動。時間到了便離開,然後忘掉。
在教會及多方努力下,哲哲的問題解決了,但他從此和教會劃清界線,再未邀請我去他家做客。實體晨禱是在距離宿舍十四公里的小教會。那裡剛植堂兩個月,以網路連線的方式參與晨禱,並開放會堂。實體晨禱完全是順服牧師的呼籲:「主喜悅你們在清晨時分,攻克己身,付上代價到聖殿來朝見主面。」
接待我的是一對夫妻。弟兄平日在工地當鐵工,常常晨禱到一半就先離開去工地了。兩人晚上在神學院進修,平常就我們三人晨禱,牧師則是隔週出現。
會堂擺滿了椅子,卻只坐了三兩人。連線教會多是雷同景況,牧師帶著師母開門、開燈,一同往祭壇添加柴火,持守不懈怠。
等紅燈時,我給珮珮撥了通電話,提醒她起床晨禱。電話接通便掛斷,沒有多餘的寒暄。我與世界格格不入,始終保持距離。珮珮是晨禱時認識的姊妹,年輕卻患有早發性帕金森氏症。前段時間,她媽媽因新冠肺炎重症確診而住進加護病房,她發起迫切代禱,也請我為她母親代禱錄音。
過程雖然痛苦難受,結果卻是美好。珮珮媽媽在過年前痊癒返家,主治醫生說這是神蹟。
想起哲哲在妻兒即將回家前,有天晚上邀請我去他家吃飯。他臉帶潮紅,喝著清酒,得意地表達感受和想法,以過來人的角度給予意見,暢所欲言,而我保持沉默,平靜接受,然後忘掉。
後來他沒再找我去家裡吃飯,我也沒聯絡他。
因著共用的軟弱,我們相濡以沫,也因為難處消失而相忘於江湖。為什麼他們都能離開困境,就我持續深陷泥淖中,腳踩不到盡頭?

自分居開始,宿舍生活變得蜷曲,每到放假就擔心被同事發現自己沒有回家,開始低調生活。隨著時間和持續變壞的狀況,積累的情緒產生化學反應,千頭萬緒開始變質,我在鏡子中看到未曾見過的自己,滿是絕望與哀傷。
我自覺與教會、小組格格不入,像是癌症患者和感冒患者組成病友會,卻要彼此分享病況、互相代禱。我逃離開來,卻被師母教訓:「十字架的一豎是人與神的關係,一橫是人與人的關係,所以你要學習和不同的人相處。」
憂鬱不像冰塊,只要含在口裡遲早會融化。
有天晨禱結束,牧師約大家一起吃早餐,也簡單認識彼此。我語帶保留沒有訴說太多,與外界保持著防疫距離。這並不是我的風格,而是分居後衍生的保護措施。我無法與外人共用軟弱,決不讓人看見自己的低谷,我竭力表現出堅毅剛強,這不困難,就像自拍只需善用角度和工具。
我為自己所寫的人生劇本沒有如期上演,氣急敗壞地破口大駡。世界的霸凌是如此強大,讓人生不出一絲積極來正面迎擊。
世界對我報以老拳,而我卻無力抵抗。
痛苦震耳欲聾,盼望卻輕聲細語。
有天晨禱進行到一半,同工姊妹突然站起身來說:「我去後面趴一下。」
「啊?」
「我忙到三點才睡,想休息一下。」、
姊妹就趴在桌上睡著了,我自己一人安靜完成晨禱,再輕手躡腳收拾會堂,確認所有電器都關閉,這才叫醒姊妹。「筆電我收起來了,電源也全都關好了。我要上班了,你早點回家休息。」我站在騎樓上看著姊妹走出教會,這才放心離去。
教會、家庭、工作、學業,夫妻兩人就在不輕鬆的四角來回兜轉。我不知道他們的生活有無難處,自己能做的就是陪伴、禱告。曾在週五晚上特意提前告知,隔天不過去晨禱了,心想同工週六就會休息,但在連線時看到的依舊是同工一人在堅持晨禱的畫面。
我很想對同工說:「你們休息吧! 是否因為我有參加實體晨禱的需要,你們才決定早起開門?我一個人要晨禱很簡單,我可以回到之前在宿舍晨禱的生活,但我實在不願意看到你們這麼辛苦。有許多教會已經退出連線晨禱,如果太忙、太辛苦,是否請你們考慮一下?」體貼肉體的話語沒有出口,等候是最積極的作為。
在聽完我的建議後,牧師說:「教會還是會持守晨禱,也尊重你的感受,我很高興同工能有你陪伴。」
其實我很累。但我說不出口,常常我五點醒來躺在床上,千頭萬緒盡是不要去教會。我開始刻意留在宿舍晨禱,但同工卻鼓勵我要持續到教會晨禱,說這是新信心的操練,神都紀念,要努力維持。當時間到了,同工還沒來開門,我便站在會堂外,隔著玻璃仰望十字架安靜禱告,用手機連線直到晨禱結束;若同工仍沒出現,我會很高興,她睡過頭了。

開始晨禱後,我和教會的關係不再是只有主日,而是每日。
每日連結我和教會、肢體的,不是華麗的會堂和渲染的影音,而是共用的軟弱與共同的掙扎。
車子繼續行駛在幽暗的街道。車頭燈照亮路面前方,雨絲在擋風玻璃上點點成形,輪胎劃過地面,彈奏出黑夜的終曲。
每天兩點一線地前往,在天色昏暗時出發,結束時天都亮了。再藉口要趕去上班,向同工匆忙道別。因為支離破碎,我變得不善交際,只能與共用軟弱的主內肢體互動。
無論白天遭遇怎樣的攻擊,內心怎樣委屈,只要在瀕臨崩潰前爬上床,用棉被狠狠纏裹身體,緊握拳頭,想著只要睡一覺,明天清晨就能到教會晨禱了,便得了安慰。
開始學習安靜,在晨禱後的駕駛途中回顧內容,在城市甦醒前與神對話,在繁忙的車陣裡痛哭,再收拾心情面對生活。
我像那坐在椅子上,讓美髮師修剪頭髮的客人。神修剪了在鏡子前看得到的頭髮,要我低頭,開始修剪後腦勺那看不到的頭髮。我只能以信心來順服,積極等候,直等聽到神說「好了」,便可抬起頭來,在鏡中看到修剪後的模樣,同神相視微笑。
蟬的多數年月活在不見天日、幽暗濕冷的土壤底下,以樹根的汁液為食,承受著壓力、孤單;直等到多年後的盛夏來臨,這才金蟬脫殼,在陽光最為熾焰的盛夏,用新生的身體、移動方式,飛向天際,一鳴驚人。
忍受孤單、壓力的環境,但卻是委身、扎根的靜默階段。無論環境如何,在環境之下是磐石,在環境之上是天父,這是不變的事實。唯有老我褪去,人才會以嶄新的面貌重生,不用再背負、忍受,不用再匍匐於不為人知的寒土底下,展翅飛翔,用生命來讚美敬拜,讓世界感歎讚美是如此撼天震地。
不知自己是否已經預備好,在這過程中經歷。

車子行駛到了教會外,雨勢持續變大,黎明已在聖殿等候。我拉上手刹,將車子熄火,在駕駛座深呼吸,好好整理情緒,下車前將過去的愁苦隨手往車窗外丟,不帶進聖殿。
沒有人一出生就是重度近視,度數都是在貪玩中日益加深,佩戴一副永恆眼光,才能在積極等候中凝視遠方。
不明白為何堅守婚姻最終的結局仍不敵現實,三月法院判離、賠錢,四月前妻到戶政事務所申報離婚登記。
同時間,我在清明時節與晨禱夥伴取得聯繫。她曾是我婚姻的代禱者,有著共用的軟弱。在神恩典奇妙的帶領下,我們於復活節確定關係,五月兩人再次走進婚姻,瞬間低谷躍為高山,經歷翻轉,超乎想像。
我從後照鏡看著自己,那憂鬱眼影已不存在,解開安全帶,下車快步走進暴風圈中。縱使洪水泛濫淹過視線,我仍看見亮光中有寶座上的身影;聖殿已座無虛位,但仍保留我的位置。我在門口吸水墊上用力踏腳,將鞋上的攔阻和淚水作簡單清理,再用雙手推開大門。
「大家平安,大家早安!」
-END-
作者簡介
林友仁
第一代基督徒,平凡的上班族,孜孜以求的中年大叔。在第一個為己而活40年即將結束時受洗,剛開始第二個為祂而活的40年。40歲以前追求靈感,40歲以後追求感動。
圖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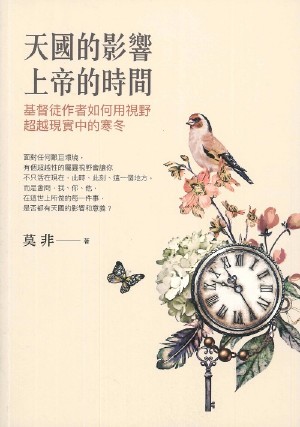
《天國的影響 上帝的時間》
莫非 著
超越,
不只活在此時、此刻、
這一個地方,
而是會問,
我、你、他,
在這世上
所做的每一件事,
是否都有
天國的影響和意義?
購買資訊:
台灣:橄欖華宣 https://www.cclm.com.tw/book/19317
北美:gcwmi622@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