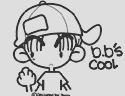虐待了過貓的原味。但這是我個人的偏見,有識者或以為,蕨者,性寒,熱炒正好綜合其性,易於胃部的蠕動和消化。我卻主觀認定,那寒意還是得保留,方能感受其本質。
由此推論,讀者當知,汆燙者,乃我喜愛的處理方式。過個滾水,去掉多數黏味澀感後,迅速冰鎮,無疑是處理過貓最微妙的箇中技巧。經過如此冷藏,柔軟、清脆,進而泛著碧綠色澤的嫩芽,絕對是上品。再從冰箱開啟時,自有森冷之氣,常讓接觸者彷彿進入了蔥蘢的森林。日本料理店何以端出蕨菜,作為開胃小菜,想必有此細膩的心思。
冰鎮的過貓,再蘸以適宜的醬料,比如好一點的麻油和鹽巴,就足以嚼出美味。若是挑剔一些,嚴選那細緻的岩鹽,搭配北港黑麻油。每口過貓一進入嘴裡,都彷彿麋鹿咬到今年初春,雪地裡冒出的第一撮新芽。
當然,其他醬料亦能充當精采的輔佐。關鍵在吃者,自己得摸索醬料的調配經驗,從中研發出獨家口味和美學。過貓仿若一幅勾勒妥線條的風景,但看食者如何上色,彩繪出其動人的樣貌。冷食之道,最忌諱胡亂地摻以重口味的醬料,諸如美乃滋這類,蠻橫地搶奪了主角的表現。台灣常見的辦桌,第一道拼盤,美乃滋最常扮演的,便是這種倒盡胃口的主秀。
有些西方旅行者初次咀啖過貓,彷彿在雨林世界有了豔遇,總愛誇大形容,它的肥碩、青綠,美味如蘆筍。其實,若嚴格評品,那風味接近北美洲的鴕蕨(Ostrich Fern)。當我們走訪北美森林,初次在野地吃到後者,相信那種少見多怪的情緒,也會有相似的勾動。著名的紐約餐館老板George Rector對過貓曾有理性的形容,「簡單、美麗,如靈魂之春。」這樣的謹慎描述,較合乎我的認知。
我對過貓的興趣,也不止在摘食,更在乎其生長環境。過貓喜歡生長於陽光明亮潮溼的環境。在台灣和西雙版納旅行時,邂逅這種蕨類,往往在潮溼的沼澤環境。無論是穿著亮麗服飾之傣族婦女,或者頭戴包巾斗笠的台灣農婦,輕快地走進草地,在明亮的陽光下,摘食嫩葉和嫩芽,那風景常教人心生溫暖。
晚近,我也喜愛在台灣荒廢的農村田埂間尋覓,邂逅殘留的過貓。以此驗證,一個區域溼地的存在範圍,懷想著早年的自然環境。
沒有溼地,就沒有過貓。日本的過貓為何稀少,有些地方甚至瀕臨滅絕,除了分布偏北,生存不易,另一原因便是溼地的過度濫墾。無獨有偶,台灣也遇到這樣的情形,野生的過貓愈來愈少。
過去,野生的很容易看見,意味著溼地環境到處可見。但生長零星下,摘食者還是得花上一大段時間,才能摘好炒食的分量。在吃法上,因而就比較捨不得浪費,不僅摘嫩芽食用,連六七公分長的嫩葉也會挑撿,並且聲稱比較好吃。
如今大量人工栽培,在傳統菜市場,常看到肥碩的過貓嫩芽,一大把一大把包裝零售。這種內容,很顯然地,在採摘過程裡,割捨了嫩葉部分,只保留城市人愛吃的嫩芽部位。這是一般鄉下農婦難以想像的,相信傣族的婦人看到台灣如此浪費,恐怕也會吃驚。
在馬來半島旅行時,吃到了當地的餐飲,或也能略知溼地的一二狀況。他們有一道名菜叫「馬來風光」,內容主要為蝦醬空心菜。但以前的主要食材卻是Pucuk Paku。為何呢?原來,早年Pucuk Paku隨處可見,路上隨便一處潮溼之處,信手拈來,就摘個一大把,但後來溼地愈來愈少,Pucuk Paku不容易採摘,才改成空心菜。如此情形,不用任何數據,光是這個食材的變遷,就充分說明了,馬來西亞的溼地環境消失,也相當嚴重了。
從Pucuk Paku到過貓,從喜馬拉雅山腳到太平洋諸島,這一明亮的溼地之蕨,其分布和採食,沒什麼大事蹟,卻給了我如是啟發。(下)
劉克襄近況
十幾年前就習慣六點起床。現在更早了,五點出頭,眼便澄明,心亦清淨地出門,在小學的操場健走。至於例假日,選定的漫遊地方不再遙遠,山路也走得愈來愈隨興。很喜歡半路上邂逅農家田園,就賴在那兒,改變了預定的行程。
倒是買菜這工作,愈來愈挑剔,專挑那偏遠山腳的市集,看看自己是否有足夠的福氣,遇到更多奇野的蔬果。
最近,還試圖搶救辛亥隧道南邊出口的蓊鬱森林,聽說附近的山坡環評通過,即將蓋公寓大樓,那兒比富陽森林公園,更隱藏著自然公園的內涵,卻少人重視。此外,即將完成的貓空纜車,對二格山系的影響,也持續觀察著。環境保護的工作,常讓人心力交瘁,但習慣了,就不以為苦,像早起一樣。
散文觀
每個階段裡生活的自然理念和實踐,若不能透過文字表達時,對我而言,散文書寫就荒涼了。再延伸論之,一個熟悉的地域,若無人文風物的多方消化,我更興不起持續執筆的熱情。
反之,這等文以載道的標竿既已豎立,若不能用文字愉悅而美麗地表達,我亦消受不起。
如此嚴格規範自己,許多稿子完成時,往往便按捺著不發,百般審視。等到滿意了,寄出去的稿子,少說都放了半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