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征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是台中中區工廠登記會計師事務所最佳稅務後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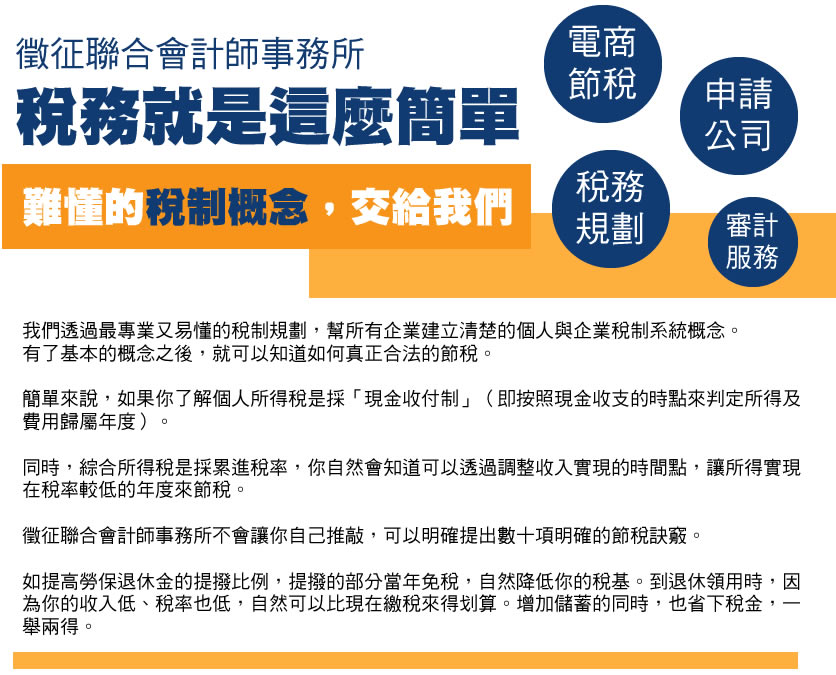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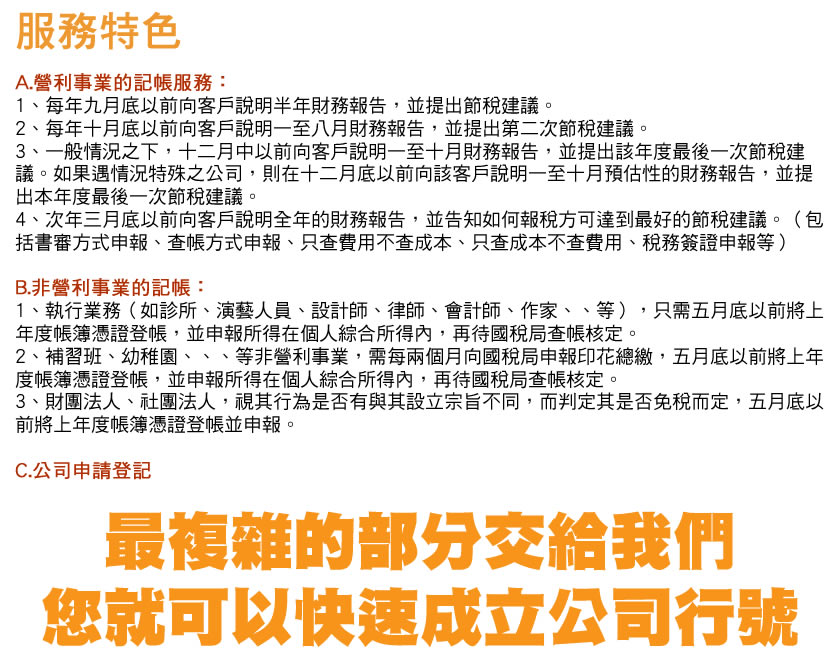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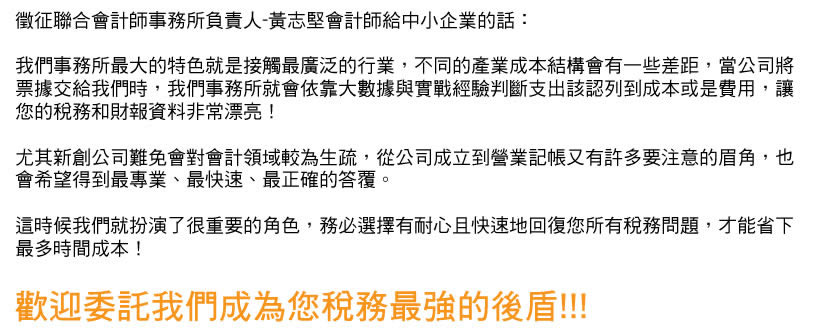
台中西屯稅務管理與諮詢, 台中潭子合作社稅務諮詢, 台中推薦確信會計服務推薦
孫犁:某村舊事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投降,我從延安出發,十月到渾源,休息一些日子,到了張家口。那時已經是冬季,我穿著一身很不合體的毛藍粗布棉衣,見到在張家口工作的一些老戰友,他們竟是有些“城市化”了。做財貿工作的老鄧,原是我們在晉察冀工作時的一位詩人和歌手,他見到我,當天夜晚把我帶到他的住處,燒了一池熱水,叫我洗了一個澡,又送我一些錢,叫我明天到早市買件襯衣。當年同志們那種同甘共苦的熱情,真是值得懷念。 第二天清晨,我按照老鄧的囑咐到了攤販市場。那里熱鬧得很,我買了一件和我的棉衣很不相稱的“綢料”襯衣,還買了一條日本的絲巾圍在脖子上,另外又買了一頂口外的貍皮冬帽戴在頭上。路經宣化,又從老王的床鋪上扯了一條粗毛毯,一件日本軍用黃呢斗篷,就回到冀中平原上來了。 這真是勝利歸來,揚揚灑灑,連續步行十四日,到了家鄉。在家里住了四天,然后,在一個大霧彌漫的早晨,到蠡縣縣城去。 冬天,走在茫茫大霧里,像潛在又深又冷的渾水里一樣。 但等到太陽出來,就看見村莊、樹木上,滿是霜雪,那也真是一種奇景。那些年,我是多么喜歡走路行軍!走在農村的、安靜的、平坦的道路上,人的思想就會像清晨的陽光,猛然投射到披滿銀花的萬物上,那樣閃耀和清澈。 傍晚,我到了縣城。縣委機關設在城里原是一家錢莊的大宅院里,老梁住在東屋。 梁同志樸實而厚重。我們最初認識是一九三八年春季,我到這縣組織人民武裝自衛會,那時老梁在縣里領導著一個劇社。但熟起來是在一九四二年,我從山地回到平原,幫忙編輯《冀中一日》的時候。 一九四三年,敵人在晉察冀持續了三個月的大“掃蕩”。 在繁峙境,我曾在戰爭空隙,翻越幾個山頭,去看望他一次。 那時他正跟隨西北戰地服務團行軍,有任務要到太原去。 我們分別很久了。當天晚上,他就給我安排好了下鄉的地點,他叫我到一個村莊去。我在他那里,見到一個身材不高管理文件的女同志,老梁告訴我,她叫銀花,就是那個村莊的人。她有一個妹妹叫錫花,在村里工作。 到了村里,我先到錫花家去。這是一家中農。錫花是一個非常熱情、爽快、很懂事理的姑娘。她高高的個兒,顏面和頭發上,都還帶著明顯的稚氣,看來也不過十七八歲。中午,她給我預備了一頓非常可口的家鄉飯:煮紅薯、炒花生、玉茭餅子、雜面湯。 她沒有母親,父親有四十來歲,服飾不像一個農民,很像一個從城市回家的商人,臉上帶著酒氣,不好說話,在人面前,好像做了什么錯事似的。在縣城,我聽說他不務正業,當時我想,也許是中年鰥居的緣故吧。她的祖父卻很活躍,不像一個七十來歲的老人,黑干而健康的臉上,笑容不斷,給我的印象,很像是一個牲口經紀或賭場過來人。他好唱昆曲,在我們吃罷飯休息的時候,他拍著桌沿,給我唱了一段《藏舟》。這里的老一輩人,差不多都會唱幾口昆曲。 我住在這一村莊的幾個月里,錫花常到我住的地方看我,有時給我帶些吃食去。她擔任村里黨支部的委員,有時也征求我一些對村里工作的意見。有時,我到她家去坐坐,見她總是那樣勤快活潑。后來,我到了河間,還給她寫過幾回信,她每次回信,都談到她的學習。我進了城市,音問就斷絕了。 這幾年,我有時會想起她來,曾向梁同志打聽過她的消息。老梁說,在一九四八年農村整風的時候,好像她家有些問題,被當做“石頭”搬了一下。農民稱她家為“官鋪”,并編有歌謠。錫花倉促之間,和一個極普通的農民結了婚,好像也很不如意。詳細情形,不得而知。乍聽之下,為之默然。 我在那里居住的時候,接近的群眾并不多,對于干部,也只是從表面獲得印象,很少追問他們的底細。現在想起來,雖然當時已經從村里一些主要干部身上,感覺到一種專橫獨斷的作風,也只認為是農村工作不易避免的缺點。在錫花身上,連這一點也沒有感到。所以,我還是想:這些民憤,也許是她的家庭別的成員引起的,不一定是她的過錯。至于結婚如意不如意,也恐怕只是局外人一時的看法。感情的變化,是復雜曲折的,當初不如意,今天也許如意。很多人當時如意,后來不是竟不如意了嗎?但是,這一切都太主觀,近于打板搖卦了。我在這個村莊,寫了《鐘》、《藏》、《碑》三篇小說。 在《藏》里,女主人公借用了錫花這個名字。 我住在村北頭姓鄭的一家三合房大宅院里,這原是一家地主,房東是干部,不在家,房東太太也出去看望她的女兒了。陪我做伴的,是他家一個老傭人。這是一個在農村被認為缺個魂兒、少個心眼兒、其實是非常質樸的貧苦農民。他的一只眼睛不好,眼淚不停止地流下來,他不斷用一塊破布去擦抹。他是給房東看家的,因而也幫我做飯。沒事的時候,也坐在椅子上陪我說說話兒。 有時,我在寬廣的庭院里散步,老人靜靜地坐在台階上; 夜晚,我在屋里地下點一些秫秸取暖,他也蹲在一邊取火抽煙。他的形象,在我心里,總是引起一種極其沉重的感覺。他孤身一人,年近衰老,尚無一瓦之棲,一壟之地。無論在生活和思想上,在他那里,還沒有在其他農民身上早已看到的新的標志。一九四八年平分土地以后,不知他的生活變得怎樣了,祝他晚境安適。 在我的對門,是婦救會主任家。我忘記她家姓什么,只記得主任叫志揚,這很像是一個男人的名字。丈夫在外面做生意,家里只有她和婆母。婆母外表黑胖,頗有心計,這是我一眼就看出來的。我初到鄭家,因為村干部很是照顧,她以為來了什么重要的上級,親自來看過我一次,顯得很親近,一定約我到她家去坐坐。第二天我去了,是在平常人家吃罷早飯的時候。她正在院里打掃,這個庭院顯得整齊富裕,門窗油飾還很新鮮,她叫我到兒媳屋里去,兒媳也在屋里招呼了。我走進西間里,看見婦救會主任還沒有起床,蓋著耀眼的紅綾大被,兩只白晰豐滿的膀子露在被頭外面,就像陳列在紅絨襯布上的象牙雕刻一般。我被封建意識所拘束,急忙卻步轉身。她的婆母卻在外間吃吃笑了起來,這給我的印象頗為不佳,以后也就再沒到她家去過。 有時在街上遇到她婆母,她對我好像也非常冷淡下來了。 我想,主要因為,她看透我是一個窮光蛋,既不是騎馬的干部,也不是騎車子的干部,而是一個穿著粗布棉衣,挾著小包東游西晃遛遛達達的干部。進村以來,既沒有主持會議,也沒有登台講演,這種干部,叫她看來,當然沒有什么作為,也主不了村中的大計,得罪了也沒關系,更何必巴結鉆營? 后來聽老梁說,這家人家在一九四八年冬季被斗爭了。這一消息,沒有引起我任何驚異之感,她們當時之所以工作,明顯地帶有投機性質。 在這村,我遇到了一位老戰友。他的名字,我起先忘記了,我的愛人是“給事中”,她告訴我這個人叫松年。那時他只有二十五、六歲,瘦小個兒,聰明外露,很會說話,我愛人只見過他一兩次,竟能在十五、六年以后,把他的名字沖口說出,足見他給人印象之深。 松年也是鄭家支派。他十幾歲就參加了抗日工作,原在冀中區的印刷廠,后調阜平《晉察冀日報》印刷廠工作。我倆人工作經歷相仿,過去雖未見面,談起來非常親切。他已經脫離工作四、五年了。他父親多病,娶了一房年輕的繼母,這位繼母足智多謀,一定要兒子回家,這也許是為了兒子的安全著想,也許是為家庭的生產生活著想。最初,松年不答應,聲言以抗日為重。繼母遂即給他說好一門親事,娶了過來,枕邊私語,重于詔書。新媳婦的說服動員工作很見功效,松年在新婚之后,就沒有回山地去,這在當時被叫做“脫鞋”——“妥協”或開小差。 時過境遷,松年和我談起這些來,已經沒有慚怍不安之情,同時,他也許有了什么人生觀的依據和現實生活的體會吧,他對我的抗日戰士的貧苦奔波的生活,竟時露嘲笑的神色。那時候,我既然服裝不整,夜晚睡在炕上,鋪的蓋的也只是破氈敗絮。(因為房東不在家,把被面都擱藏起來,只是炕上扔著一些破被套,我就利用它們取暖。)而我還要自己去要米,自己燒飯,在他看來,豈不近于游僧的斂化,饑民的就食!在這種情況下面,我的好言相勸,他自然就聽不進去,每當談到“歸隊”,他就借故推托,揚長而去。 有一天,他帶我到他家里去。那也是一處地主規模的大宅院,但有些破落的景象。他把我帶到他的洞房,我也看到了他那按年歲來說顯得過于肥胖了一些的新婦。新婦看見我,從炕上溜下來出去了。因為曾經是老戰友,我也不客氣,就靠在那折疊得很整齊的新被壘上休息了一會。 房間裱糊得如同雪洞一般,陽光照在新糊的灑過桐油的窗紙上,明亮如同玻璃。一張張用紅紙剪貼的各色花朵,都給人一種溫柔之感。房間的陳設,沒有一樣不帶新婚美滿的氣氛,更有一種脂粉的氣味,在屋里彌漫…… 柳宗元有言,流徙(www.lz13.cn)之人,不可在過于冷清之處久居,現在是,革命戰士不可在溫柔之鄉久處。我忽然不安起來了。當然,這里沒有冰天雪地,沒有烈日當空,沒有跋涉,沒有饑餓,沒有槍林彈雨,更沒有入死出生。但是,它在消磨且已經消磨盡了一位青年人的斗志。我告辭出來,一個人又回到那冷屋子冷炕上去。 生活啊,你在朝著什么方向前進?你進行得堅定而又有充分的信心嗎? “有的。”好像有什么聲音在回答我,我睡熟了。 在這個村莊里,我另外認識了一位文建會的負責人,他有些地方,很像我在《風云初記》里寫到的變吉哥。 以上所記,都是十五、六年前的舊事。一別此村,從未再去。有些老年人,恐怕已經安息在土壤里了吧,他們一生的得失,歡樂和痛苦,只能留在鄉里的口碑上。一些青年人,恐怕早已生兒育女,生活大有變化,愿他們都很幸福。 1962年8月13日夜記 孫犁作品_孫犁散文 孫犁:石子 孫犁:北平的地台戲分頁:123
鐵凝:米子和明喜 洋花的成色好,使花主們更看重花。三伏天缺水,花主扔下大莊稼不管,凈澆花地。井水浸著干渴的土壟溝,土壟溝滲水,水頭像是不動彈。可水在流,流進花地,漫過花畦,花打起精神,葉子像張開的巴掌。花桃湛綠,硬邦邦打著澆花人的小腿。 花主明喜在看水。明喜躺在花葉下睡,花搭搭的陰影在他光著的胸脯上晃。明喜不真睡,他估摸著水勢,畦滿了,便從花葉惦記他的花地,他盼花地今年比往年好,他盼大莊稼快倒了。那時他就會有一個看花的窩棚,那時他就從媳婦炕上卷起一套新被新褥。明喜愿意看花,雖然看花要離開媳婦,媳婦又是新娶的。可媳婦知道這花地的嬌貴。知道這事不能攔,索性就不攔,還把新被褥給明喜準備出來。新被褥是娘家的陪送,洋花紡線、鬼子綠、鬼子紫、煮青和槐米染線,四蓬繒織布。 明喜要看花了,媳婦總是和明喜恩愛著一夜不睡,就像明喜要出征,要遠行,要遇到不測風云,那不測風云就是窩棚里的事。她知道現在丈夫對她的熱情都是提前給予她的歉意。明喜和媳婦高興一陣,翻個身,嘆口氣,像在說:看花,祖輩傳下來的,我又不能不去。要看花,莫非還能不搭窩棚,還能不抱被褥,還能不離開你,還能……他不再想,仿佛不想就不再有下文。 明喜八月抱走被褥,十月才抱回家。那時媳婦看看手下這套讓人揉搓了兩個月的被褥,想著發生在褥子上面、被子底下的事,不嫌寒磣,便埋頭拆洗,拆洗干凈等明年。 誰都知道米子鉆窩棚掙花,也不稀罕。這事也不光米子,不光本地人。還有外路人,外路女人三五結伴來到百舍,找好下處,晝伏夜出。 花主們都有這么個半陰半陽含在花地里的窩棚。搭時,先在地上埋好樁子,樁子上綁竹弓,再搭上箔子、草苫,四周戮起谷草,培好土。里面鋪上新草、新席和被褥。這窩棚遠看不高不大,進去才覺出是個別有洞天:幾個人能盤腿說話,防雨、防風、防霜。 花主們早早把窩棚搭起來,直到霜降以后滿街喊抬花時,還拖著不拆。拖一天是一天,多一夜是一夜。就是寶聚用糖鑼敲醒的那種夜。 寶聚用糖鑼宣布了夜的開始,曠野里也有了糖鑼聲。曠野里的糖鑼比寶聚的糖鑼打出的花點多,但更喑啞,像是帶著夜這個不能公開的隱私在花地里游走。糖鑼提醒你,提醒你對這夜的注意;糖鑼又打擾著你,分明打擾了你的夜。它讓你焦急讓你心跳,你就盼望窩棚不再空曠。 在曠野敲糖鑼的人叫“糖擔兒”,但他們不挑擔兒,只一只柳編大籃,籃子系兒上綁個泡子燈。 籃里也擺著寶聚車上的貨, 煙比寶聚的好,除了“雙刀”、“大孩兒”還有“哈德門”、“白炮台”。他們用好煙、大梨給窩棚“雪里送炭”,他們知道,窩棚里的人在高興中要“打茶圍”。 有個糖擔兒每天都光臨明喜的窩棚,明喜的窩棚里每天都有米子。糖擔兒來了,挑簾就迸,那簾子叫草苫兒,厚重也隔音,人若不挑開,并不知里面有舉動。糖擔兒挑開了明喜的草苫兒,泡子燈把窩棚里照得赤裸裸。明喜在被窩里罵:“狗日的,早不來晚不來。”他用被角緊捂米子。米子說:“不用捂我,給他個熱鬧看,吃他的梨不給他花。”糖擔兒掀掀被角,確信這副溜溜的光肩膀是米子的,便說:“敞開兒吃,哪兒賺不了倆梨。”他把一個涼梨就勢滾入米子和明喜的熱被窩。明喜說:“別他媽鬧了,涼瘆瘆的。”米子說:“讓他鬧。你敢再扔倆進來?”糖擔兒果然又扔去兩個,這次不是扔,是用手攥著往被窩里送。送進倆涼梨,就勢摸一把長在米子胸口上的那倆熱梨,熱咕嘟。米子不惱,光吃吃笑。明喜惱了,坐起來去揪糖擔兒的紫花大祆。米子說:“算了,饒了他吧,叫他給你盒好煙。”明喜說:“一盒好煙,就能沾這么大的便宜?”米子說:“那就讓他給你兩盒。”明喜不再說話,明喜老實,心想兩盒煙也值二斤花,這糖擔兒頂著霜天串花地也不易,算了,哪知米子不干,冷不丁從被窩里躥出來,露出半截光身子,劈手就從糖擔兒籃子里拿。糖擔兒說:“哎哎,看這事兒,這不成了砸明火。”米子說:“就該砸你。叫你動手動腳,臘月生的。”說著,抓起兩盒“白炮台”就往被窩里掖。糖擔兒伸手搶,米子早蹴到被窩底,明喜就勢把被窩口一摁,糖擔兒眼前沒了米子。糖擔兒想,你搶走我兩盒“白炮台”,我看見了你的倆饞饞①,不賠不賺。誰讓你自顧往外躥。我沒有花地,沒有窩棚,不比明喜。看看也算開了眼。 ① 饞饞,乳房。 明喜見糖擔兒不再動手動腳,說:“算了,天也不早了,你也該轉游轉游了。我這兒就有幾把笨花,拿去吧。”明喜伸手從窩棚邊上夠過一小團笨花,交給糖擔兒。糖擔兒在手里掂掂分量、看看成色說:“現時笨花沒人要。還沾著爛花葉。留給你媳婦絮被褥吧。”明喜說:“算了,別來這一套了,我不信二斤笨花值不了仨梨兩盒煙。”糖擔兒不再賣關子,接過花摁進籃子,沖著被窩底說:“米子,我走了,別想我想得睡不著。趕明兒我再來看你。”明喜說:“還不快走。”糖擔兒這才拱起草苫兒,投入滿是星斗的霜天里。明喜披上衣服跟出來,他看見糖擔兒的燈順著干壟溝在飄。看看遠處,遠處也有燈在飄。他想起老人說的燈籠鬼兒,他活了二十年還從來沒見過燈籠鬼兒什么樣。可老人們都說見過,說那東西專在花地里跑。 糖擔兒用糖鑼敲著花點,嘴里唱著“嘆五更”。 明喜見糖擔兒已經走遠,鉆回窩棚。米子在被窩底蹴著。明喜掀開被窩對著里面說:“米子,出來吧,糖擔兒走了。”米子不出來,只伸出一條白胳膊拽明喜,讓明喜也蹴到被窩底。明喜先把腿伸進被窩,摸黑兒在枕頭上坐一會兒,然后褪下大襖向下一溜,也溜到被窩底。米子早用頭頂住了他的小肚子,頂得明喜想笑。明喜把本子推開,米子打個挺兒舒展開身子說:“你頂我還不行。”明喜不說話,也用頭去頂米子。米子說:“扎死我。”說著扎,她捶著明喜的背,摟著明喜的脖子。明喜的臉貼著米子的身子一愣:我操!敢情米子的身上這么光滑,我怎么這會兒才知道。明喜覺著自己手糙、臉糙、身上也糙,米子生是和明喜的糙身子滾……兩人覺出身上冷才知道被窩敞了許多,明喜歪起身子掖被窩,米子說:“我該走了,也省了你左掖右掖了。”明喜說:“這就走?”米子說:“你也乏了,睡吧。”明喜說:“看你說的,別把我看扁了。”米子說:“扁不扁的吧,莫非你聽不見你的呼嚕?”明喜不說話了。米子早已摸黑穿好了棉褲棉襖,又摸到自己的鞋,跪在明喜身邊說:“你睡吧,我走了。” 明喜躺著不動,只說:“外邊有洋花,干草擋著哩,你自己抓吧。哎,可不許你再到別處串了,干草底下的花你盡著抓。你聽見沒有?” 米子答應一聲,從窩棚頂上拽下她掖在那兒的空包袱皮,洪開了草苫兒。明喜聽見她在揪干草抓花。 米子把明喜捂在干草底下(www.lz13.cn)的洋花盡摁入包袱,系上包袱便松心地蹲在花壟里撒尿,尿滋在干花葉上豁啷啷地響,明喜被這響聲驚醒,知道米子還沒走,披上大祆拱出窩棚兩步邁在米子跟前,米子從花壟里站起來挽腰系褲說:“又起來干什么?”明喜說:“我還得囑咐你一句,你聽了別煩。可不許你再往別處去了,快回家吧。”米子說:“我不是答應過了!”明喜說:“我沒聽見。”米子說:“那是你沒聽見。”米子把一包捶布石大小的棉花掄上了肩,她覺得,明喜留給她的花還真有些分量哩。 米子望望四周,糖擔兒的泡子燈又跳出了一個窩棚,糖鑼打著花點。她邁過幾條花壟,跨進一條干壟溝。明喜盯著米子的背影,看見米子并沒有朝村里走。米子只朝村里走了一小截就斜馬著拐了回來。明喜想,說話不算數,還鉆。趕明兒看我還給你留好花。 趕明兒米子來了。明喜問:“怎么總是說話不算話,不是說回村么?”米子說:“是回村了。”明喜說:“得了吧,別哄我了,走了一小截就往回拐,又串了幾處?”米子說:“你愿意聽?”明喜說:“不。”米子說:“不愿意聽還問。”明喜說:“問是得問,不問問還能給你留好花?”米子說:“就那幾把洋花,也有臉說。你別給我留了,你娶了我吧。娶了我,就不要你的花了,還讓你敞開兒打我。” 鐵凝作品_鐵凝散文集 鐵凝:小鄭在大樓里 鐵凝:米子和寶聚分頁:123
八句話,看透職場 職場盡管復雜,但也有一些規律可言,下面這句話把職場就說的明明白白: 1、職場不是一個講理的地方,而是一個講結果的地方——你的理再多,沒有結果,照樣不會有什么晉升的機會。 2、你在這家單位做不好,到另外一家單位通常也做不好,因為你的習慣不改變的話,換再多的單位都避免不了犯同樣的錯誤。 3、當你職場上無依無靠的時候,就拼了命的去拼業績,只有這個能讓你快速的脫穎而出,當然,你有關系和背景的話,可以不那么辛苦。 4、職場從來就是不一個講苦勞的地方,再多的苦勞也沒有用,沒有價值轉換的苦勞越多,單位效率越低,你越是應該被干掉,單位還沒有把你干掉,只是講點面子而已。 5、職場快速升遷的三個秘籍——業績、關系和一張破嘴。 6、你承認也好,不承認也罷,跳槽都是最快的晉升方式,在一家單位或許需要三五年,但跳槽可能半年就夠了。 7、如果在職場上五年以上你沒有得到晉升,不需要去懷疑單位和你同圍的人,最值得懷疑的就是你自己,一定是自己的問題,如果不改變自己,下一個五年是這個五年翻版。 8、你在職場最核心的競爭力就是你曾犯過的各種各樣的錯誤,而不是大家說的能力有多強,你在職場上能干技術含量多高的活,絕大部分都是日常的工作罷了,一般人都能干。 想要職場飛黃騰達,就要搞定別人搞不定的問題 職場新人如何快速成長?四招讓你少走彎路 別太脆弱,職場不相信眼淚分頁:123
ACC711CEV55CE
台中潭子政治獻金稅務諮詢
行動通訊產業節稅方式 塗鍍鋼捲產業節稅方式 營業稅制度介紹
下一則: 台中西屯資本簽證 台中大里公司投資及併購 可扣抵與不可扣抵之進項?怎麼蒐集進項憑證?有效合宜節稅?
限會員,要發表迴響,請先登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