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征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是台中北屯企業重塑最佳稅務後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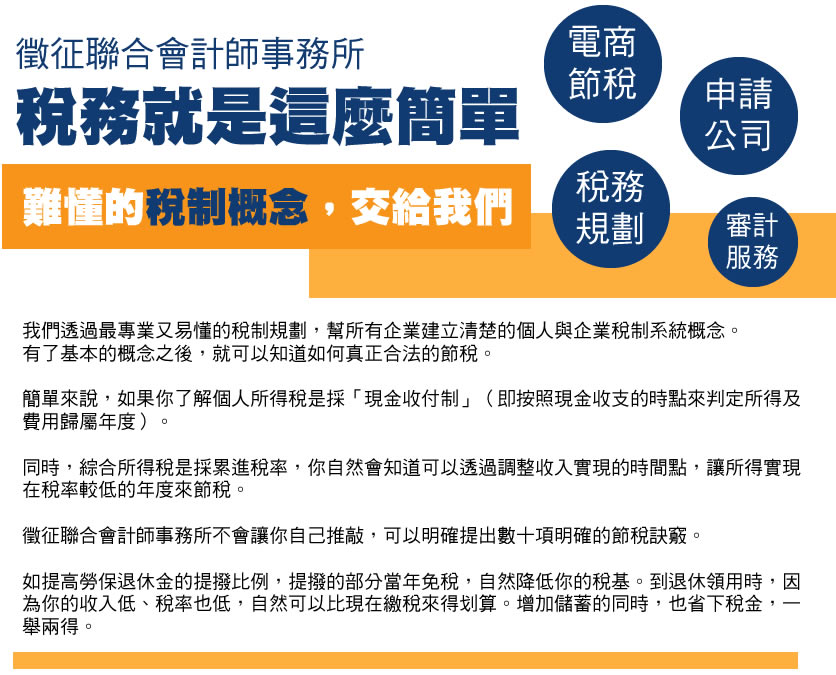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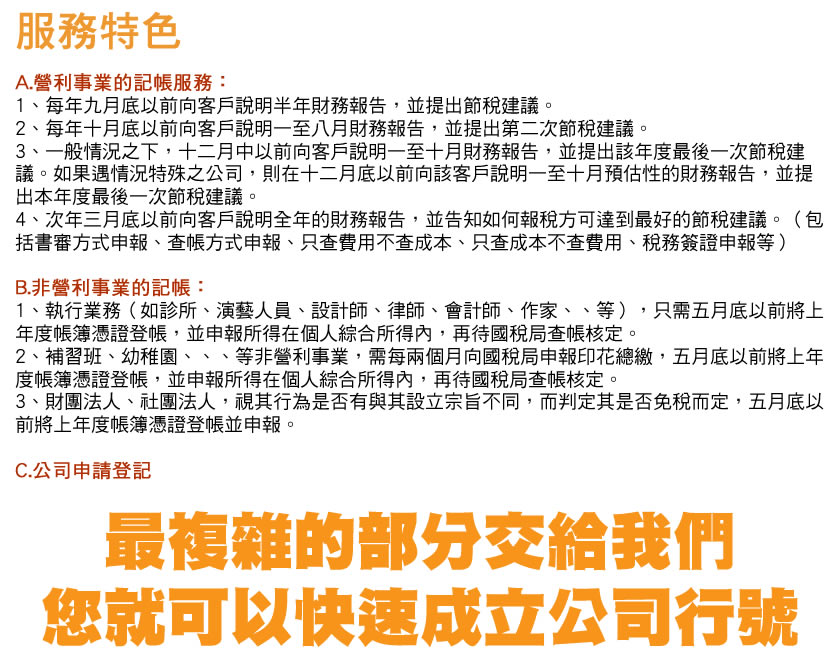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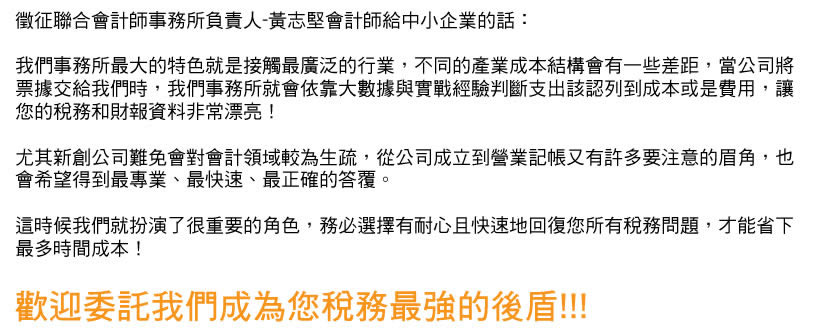
台中潭子報稅諮詢, 台中中區公司設立會計服務推薦, 台中北區金融業稅務諮詢
羅蘭:幾種友誼 一份豪縱,一份猖狂,一份不羈,一份敏細,加上一份無從捉摸的飄忽,就織成那樣一種令人系心的性格。我欣賞那種來去自如的我行我素,欣賞當談話時,忽然提起與話題全不相干的天外事;也欣賞那點對新鮮事物的好奇與窮究不舍的興致。 對一切的才華,我都有一種發自光大的向慕。我沉迷海頓的音樂,那份歡樂感情與幸福感,通過百年的歲月,帶來對人生的頌贊。某鋼琴家的一首短曲令我系念至今。柴可夫斯基的胡桃鉗,鮑洛汀的中央亞細亞曠原,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以至于電影《未終之歌》里的音樂和愛情,都令我難忘。 我愛放翁的詩,愛那份高傲——“揮袖上西峰,孤絕去天無尺”,“零落成泥碾做塵,只有香如故”;我愛李白的豪縱——“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蘇軾的曠達——“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朱希真的瀟灑——“免被花迷,不為酒困,到處惺惺地”,“老屋穿空,幸有無遮蔽”;稼軒的超脫放逸——“都將今古無窮事,放在愁邊,放在愁邊,卻自移家向酒泉”,及“若教王謝諸郎在,未抵柴桑陌上塵”。 我也喜歡朋友C的性格。喜歡他那種年紀的讀書人所特有的那份書卷氣。那是未被五四完全攔截掉,而又沐了近在身邊的五四的、那么一種雖新實舊,雖舊而又極新的書卷氣,那種既擁有中國文人的種種特色,而又極其認真地探索過西方文學的書卷氣。因此,在舉止上從容悠閑,在見解上超逸深透,在態度上卻是樸實、含蓄,而又謙虛。 才華有如一片肥沃的園地,種種可愛的性格是這片園地上的花朵。“唯大英雄能本色”,猖狂、敏細、曠達、不羈、瀟灑、放逸,以至于樸實與謙虛都是真性情的流露,因此而引人激賞,惹人牽系,或可說是一種更廣義、更真摯的感情的傳遞吧? 時常,當我有什么事遲疑不決時,就打個電話問問朋友D。他會在電話那邊把問題條分縷析一番之后,為我下一個清清爽爽的決定。 對朋友D,我有一份信賴。信賴他清晰冷靜的思路,與誠懇認真的性格。他既不會像現代一般人那樣的自顧不暇,也不像另一些老于世故的人那般的圓滑虛偽。他不會亂捧我的為人或做事,如果他認為某些地方不好,那是真的不好;因此如果他說好,我才會相信他不是敷衍或客套。有時我有事情請他幫忙,如果他說“樂為之”,我就一定可以相信他不會一面做,一面抱怨我剝奪了他的時間,因為如果他真是沒有時間,他會告訴我他忙。 他并不善于處理事務。但是他那不善處理事務的建議也正可以使我放寬心情,相信如果在事務上失敗,在金錢上吃虧,你仍可感謝上帝給了你另外那厚厚一份,而不想向上帝索討得太多。 我遇事容易激動,感情常常走在理智前面,因此徒增許多困擾。我就更喜歡有一些像D君這樣的朋友,冷靜、堅定、能高瞻遠矚視野遠闊,如同廣播發射台的塔架;使我也能學習嘗試用他們那樣冷靜而堅定的眼光去分析問題、辯論事理,而又始終使自己置身事外,保持超然。 有些朋友是在精神領域上相接近的、可以談詩文,論音樂。講人生悟境。另有些朋友不是互相談心的,那是另一種友誼,有另一種可愛可敬處。 比如說,今年早春某天,讀高中的老大忽然堅持要去山中露營。而他剛剛兩天前還在感冒發燒,我不允他去,他執意要去,說感冒已愈,不必過分小心,并且已經與同學約好,不能失信。當下使我大感為難,無奈之下想起做醫生的朋友E,撥了個電話給他,問他要主意。他在電話那邊立刻用堅決的語氣說: “開玩笑!不能去!” 于是,我把朋友E的決定告訴老大——醫生的話當不是毫無根據,不能再說我過分小心了吧? 老大雖深怪E君多事,但卻取消了原有的計劃。 能有幾個人肯如此為你負責地下如此的決定呢?就因為現在鄉愿式的人太多,人人都知道為別人下決定是大難事,也是最不易討好的事,因此我們日常多聽到依違兩可、不負責任的話。直言諍諫,明知道會惹人不高興的事,誰肯做呢?何況他是醫生,以目前把賺錢放在醫德之上的風氣來說,你得了肺炎,我才有生意可做呢!何必挨罵不討好? 老大先是怨他,繼而服他、敬他。這才是我的朋友,他的長輩。這才是真關心,不顧自己被抱怨,而只想到你的安全。 像這樣的朋友,(www.lz13.cn)而且還不止一位。 別看我平時常為別人分析問題,但輪到我自己有些生活上的實際事務須待解決時,卻常舉棋不定。如女兒報考高中,某些學校要不要去考考看呢?有事要去高雄,是買坐臥兩用的觀光號票,還是買對號車的臥鋪票呢?請客的時候,怎樣請才最省事呢?熱水器要哪一種呢?有朋友要搬到家里來住,可以不可以呢? 諸如此類,只要我問到朋友F,他總會給你一個迅速而肯定的抉擇。“你要帶她去考才對。”“對號臥鋪好得多了。”“請吃蒙古烤肉算啦!”“買個電熱水器吧!我家用的那個牌子就好。”“誰要搬到你家里來住?女的呀?不行!” 簡單明了,連理由都不用說,就這么決定。我真的由衷感謝這種快刀斬亂麻式的決斷。就好像你原來置身在一個嘈雜混亂的場所,忽然有人把電鈕一關,一切都在瞬間歸于寧靜,使你立覺神清氣爽。你發現,原來剛才的一番混亂只是一種幻覺,而你那認為不可終日的煩心的問題,原來如此簡單的一句話即可解決。這種“有人為你負責”的輕快心情,常伴隨著無限的感動以俱來。 不是嗎?這年頭,能有多少人肯如此真誠地、有擔當地來為朋友決定問題呢? 羅蘭作品_羅蘭散文集 羅蘭:夜闌人靜 羅蘭:春曉分頁:123
老舍:番表——在火車上 我倆的臥鋪對著臉。他先到的。我進去的時候,他正在和茶房搗亂;非我解決不了。我買的是順著車頭這面的那張,他的自然是順著車尾。他一定要我那一張,我進去不到兩分鐘吧,已經聽熟了這句:“車向哪邊走,我要哪張!”茶房的一句也被我聽熟了:“定的哪張睡哪張,這是有號數的!”只看我讓步與否了。我告訴了茶房:“我在哪邊也是一樣。” 他又對我重念了一遍:“車向哪邊走,我就睡哪邊!”“我翻著跟頭睡都可以!”我笑著說。 他沒笑,眨巴了一陣眼睛,似乎看我有點奇怪。 他有五十上下歲,身量不高,臉很長,光嘴巴,唇稍微有點包不住牙;牙很長很白,牙根可是有點發黃,頭剃得很亮,眼睛時時向上定一會兒,象是想著點什么不十分要緊而又不愿忽略過去的事。想一會兒,他摸摸行李,或掏掏衣袋,臉上的神色平靜了些。他的衣裳都是綢子的,不時髦而頗規矩。 對了,由他的衣服我發現了他的為人,凡事都有一定的講究與規矩,一點也不能改。睡臥鋪必定要前邊那張,不管是他定下的不是。 車開了之后,茶房來鋪毯子。他又提出抗議,他的枕頭得放在靠窗的那邊。在這點抗議中,他的神色與言語都非常的嚴厲,有氣派。枕頭必放在靠窗那邊是他的規矩,對茶房必須拿出老爺的派頭,也是他的規矩。我看出這么點來。 車剛到豐台,他囑咐茶房:“到天津,告訴我一聲!” 看他的行李,和他的神氣,不象是初次旅行的人,我納悶為什么他在這么早就張羅著天津。又過了一站,他又囑咐了一次。茶房告訴他:“還有三點鐘才到天津呢。”這又把他招翻:“我告訴你,你就得記住!”等茶房出去,他找補了聲:“混帳!” 罵完茶房混帳,他向我露了點笑容;我幸而沒穿著那件藍布大衫,所以他肯向我笑笑,表示我不是混帳。笑完,他又拱了拱手,問我“貴姓?”我告訴了他;為是透著和氣,回問了一句,他似乎很不愿意回答,遲疑了會兒才說出來。待了一會兒,他又問我:“上哪里去?”我告訴了他,也順口問了他。他又遲疑了半天,笑了笑,定了會兒眼睛:“沒什么!”這不象句話。我看出來這家伙處處有譜兒,一身都是秘密。旅行中不要隨便說出自己的姓,職業,與去處;怕遇上綠林中的好漢;這家伙的時代還是《小五義》的時代呢。我忍不住的自己笑了半天。 到了廊房,他又囑咐茶房:“到天津,通知一聲!”“還有一點多鐘呢!”茶房了了他一眼。 這回,他沒罵“混帳”,只定了會兒眼睛。出完了神,他慢慢的輕輕的從鋪底下掏出一群小盒子來:一盒子飯,一盒子煎魚,一盒子醬菜,一盒子炒肉。叫茶房拿來開水,把飯沖了兩過,而后又倒上開水,當作湯,極快極響的扒摟了一陣。這一陣過去,偷偷的夾起一塊魚,細細的咂,咂完,把魚骨扔在了我的鋪底下。又稍微一定神,把炒肉撥到飯上,極快極響的又一陣。頭上出了汗。喊茶房打手巾。吃完了,把小盒中的東西都用筷子整理好,都聞了聞,鄭重的放在鋪底下,又叫茶房打手巾。擦完臉,從袋中掏出銀的牙簽,細細的剔著牙,剔到一段落,就深長飽滿的打著響嗝。 “快到天津了吧?”這回是問我呢。 “說不甚清呢。”我這回也有了譜兒。 “老兄大概初次出門?我倒常來常往!”他的眼角露出輕看我的意思。 “噯,”我笑了:“除了天津我全知道!” 他定了半天的神,沒說出什么來。 查票。他忙起來。從身上掏出不知多少紙卷,一一的看過,而后一一的收起,從衣裳最深處掏出,再往最深處送回,我很懷疑是否他的胸上有幾個肉袋。最后,他掏出皮夾來,很厚很舊,用根雞腸帶捆著。從這里,他拿出車票來,然后又掏出個紙卷,從紙卷中檢出兩張很大,蓋有血絲胡拉的紅印的紙來。一張寫著——我不準知道——象蒙文,那一張上的字容或是梵文,我說不清。把車票放在膝上,他細細看那兩張文書,我看明白了:車票是半價票,一定和那兩張近乎李白醉寫的玩藝有關系。查票的進來,果然,他連票帶表全遞過去。 下回我要再坐火車,我當時這么決定,要不把北平圖書館存著的檔案拿上幾張才怪! 車快到天津了,他忙得不知道怎好了,眉毛擰著,長牙露著,出來進去的打聽:“天津吧?”仿佛是怕天津丟了似的。茶房已經起誓告訴他:“一點不錯,天津!”他還是繼續打聽。入了站,他急忙要下去,又不敢跳車,走到車門又走了回來。剛回來,車立定了,他趕緊又往外跑,恰好和上來的旅客與腳夫頂在一處,誰也不讓步,激烈的頂著。在頂住不動的工夫,他看見了站台上他所要見的人。他把嘴張得象無底的深坑似的,拚命的喊:“鳳老!鳳老!” 鳳老搖了搖手中的文書,他笑了;一笑懈了點勁,被腳夫們給擠在車窗上繃著。繃了有好幾分鐘,他鉆了出去。看,這一路打拱作揖,雙手扯住鳳老往車上讓,仿佛到了他的家似的,擠撞拉扯,千辛萬苦,他把鳳老拉了上來。忙著倒茶,把碗中的茶底兒潑在我的腳上。 坐定之后,鳳老詳細的報告:接到他的信,他到各處去取文書,而后拿著它們去辦七五折的票。正如同他自己拿著的番表,只能打這一路的票;他自己打到天津,北寧路;鳳老給打到浦口,津浦路;京滬路的還得另打;文書可已經備全了,只須在浦口停一停,就能辦妥減價票。說完這些,鳳老交出文書,這是津浦路的,那是京滬路的。這回使我很失望,沒有藏文的。張數可是很多,都蓋著大紅印,假如他愿意賣的話,我心里想,真想買他兩張,存作史料。 他非常感激鳳老,把文(www.lz13.cn)書車票都收入衣服的最深處,而后從枕頭底下搜出一個梨來,非給鳳老吃不可。由他們倆的談話中,我聽出點來,他似乎是司法界的,又似乎是作縣知事的,我弄不清楚,因為每逢鳳老要拉到肯定的事兒上去,他便了我一眼,把話岔開。鳳老剛問到,唐縣的情形如何,他趕緊就問五嫂子好?鳳老所問的都不得結果,可是我把鳳老家中有多少人都聽明白了。 最后,車要開了,鳳老告別,又是一路打拱作揖,親自送下去,還請鳳老拿著那個梨,帶回家給小六兒吃去。 車開了,他扒在玻璃上喊:“給五嫂子請安哪!”車出了站,他微笑著,掏出新舊文書,細細的分類整理。整理得差不多了,他定了一會兒神,喊茶房:“到浦口,通知一聲!” 載一九三六年十月《談風》第一期 老舍作品_老舍散文集 老舍:八太爺 老舍:戀分頁:123
三毛:吉屋出售 飛機由馬德里航向加納利群島的那兩個半小時中,我什么東西都咽不下去。鄰座的西班牙同胞和空中小姐都問了好多次,我只是笑著說吃不下。 這幾年來日子過得零碎,常常生活在哪一年都不清楚,只記得好似是一九八四年離開了島上就沒有回去過,不但沒有回去,連島上那個房子的鑰匙也找不到了。好在鄰居、朋友家都存放著幾串,向他們去要就是了。 那么就是三年沒有回去了。三年內,也沒有給任何西班牙的朋友寫過一封信。 之所以不愛常常回去,也是一種逃避的心理。加納利群島上,每一個島都住著深愛我的朋友,一旦見面,大家總是將那份愛,像洪水一般的往人身上潑。對于身體不健康的人來說,最需要的就是安靜而不是愛。這一點他人是不會明白的。我常常叫累,也不會有人當真。 雖然這么說,當飛機師報告出我們就要降落在大加納利島的時候,還是緊張得心跳加快起來。 已是夜間近十點了,會有誰在機場等著我呢?只打了電話給一家住在山區鄉下的朋友,請他們把我的車子開去機場,那家朋友是以前我們社區的泥水匠,他的家好大,光是汽車房就可以停個五輛以上的車。每一回的離去,都把車子寄放在那兒,請他們有空替我開開車,免得電瓶要壞。這一回,一去三年,車子情況如何了都不曉得,而那個家,又荒涼成什么樣子了呢? 下了飛機,也沒等行李,就往那面大玻璃的地方奔去。那一排排等在外面的朋友,急促的用力敲窗,叫喊我的名字。 我推開警察,就往外面跑,朋友們轟一下離開了窗口向我涌上來。我,被人群像球一樣的遞來遞去,泥水匠來了、銀行的經理來了,電信局的局長來了,他們的一群群小孩子也來了,直到我看見心愛的木匠拉蒙那更胖了的笑臉時,這才撲進他懷里。 一時里,前塵往事,在這一霎間,涌上了心頭,他們不止是我一個人的朋友,也曾是我們夫婦的好友。“好啦!拿行李去啦!”拉蒙輕輕拍拍我,又把我轉給他的太太,我和他新婚的太太米雪緊緊的擁抱著,她舉起那新生的男嬰給我看,這才發覺,他們不算新婚,三年半,已經兩個孩子了。 我再由外邊擠進隔離的門中去,警察說:“你進去做什么?”我說:“我剛剛下飛機呀!進去拿行李。”他讓了一步,我的朋友們一沖就也沖了進去,說:“她的脊椎骨有毛病,我們進去替她提箱子——”警察一直喊:“守規矩呀!你們守守規矩呀……”根本沒有人理他。 這個島總共才一千五百五十八平方公里,警察可能就是接我的朋友中的姻親、表兄、堂哥、姐夫什么的,只要存心拉關系,整個島上都扯得出親屬關系來。 在機場告別了來接的一群人,講好次日再連絡,這才由泥水匠璜杠著我的大箱子往停車場走去。 “你的車,看!”璜的妻子班琪笑指著一輛雪白光亮的美車給我看,夜色里,它像全新的一樣發著光芒。他們一定替我打過蠟又清洗過了。 “你開吧!”她將鑰匙交在我手中,她的丈夫發動了另外一輛車,可是三個女孩就硬往我車里擠。 “我們先一同回你家去。”班琪說,我點點頭。這總比一個人在深夜里開門回家要來得好。而那個家,三年不見了,會是什么樣子呢? 車子上了高速公路,班琪才慢慢的對我說:“現在你聽了也不必再擔心了,空房子,小偷進去了五次,不但門窗全壞了,玻璃也破了,東西少了什么我們不太清楚,門窗和玻璃都是拉蒙給你修的。院子里的枯葉子,在你來之前,我們收拾了二十大麻袋,叫小貨車給丟了。” “那個家,是不是亂七八糟了?”我問。 “是被翻成了一場浩劫,可是孩子跟我一起去打掃了四整天,等下你自己進去看就是了。” 我的心,被巨石壓得重沉沉的,不能講話。 “沒有結婚吧?”班琪突然問。 我笑著搖搖頭,心思只在那個就要見面的家上。車子離開了高速公路,爬上一個小坡,一轉彎,海風撲面而來,那熟悉的海洋氣味一來,家就到了。 “你自己開門。”班琪遞上來一串鑰匙,我翻了一下,還記得大門的那一只,輕輕打開花園的門,眼前,那棵在風里沙沙作響的大相思樹帶給了人莫名的悲愁。 我大步穿過庭院,穿(www.lz13.cn)過完全枯死了的草坪,開了外花園的燈,開了客廳的大門,這一步踏進去,那面巨大的玻璃窗外的海洋,在月光下撲了進來。 璜和班琪的孩子沖進每一個房間,將這兩層樓的燈都給點亮了。家,如同一個舊夢,在我眼前再現。 這哪里像是小偷進來過五次的房子呢?每一件家具都在自己的地方等著我,每一個角落都給插上了鮮花,放上了盆景,就是那個床吧,連雪白的床罩都給鋪好了。 我轉身,將三個十幾歲的女孩子各親了一下,她們好興奮的把十指張開,給我看,說:“你的家我們洗了又洗,刷了又刷,你看,手都變成紅的了。” 三毛作品_三毛散文集 三毛:我要回家 三毛:我先走了分頁:123
ACC711CEV55CE
台中中區行號設立會計服務推薦
台中南屯資本簽證 家庭用紙產業節稅方式 營所稅是什麼?營所稅制度介紹
限會員,要發表迴響,請先登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