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征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是台中大里繼承稅務諮詢最佳稅務後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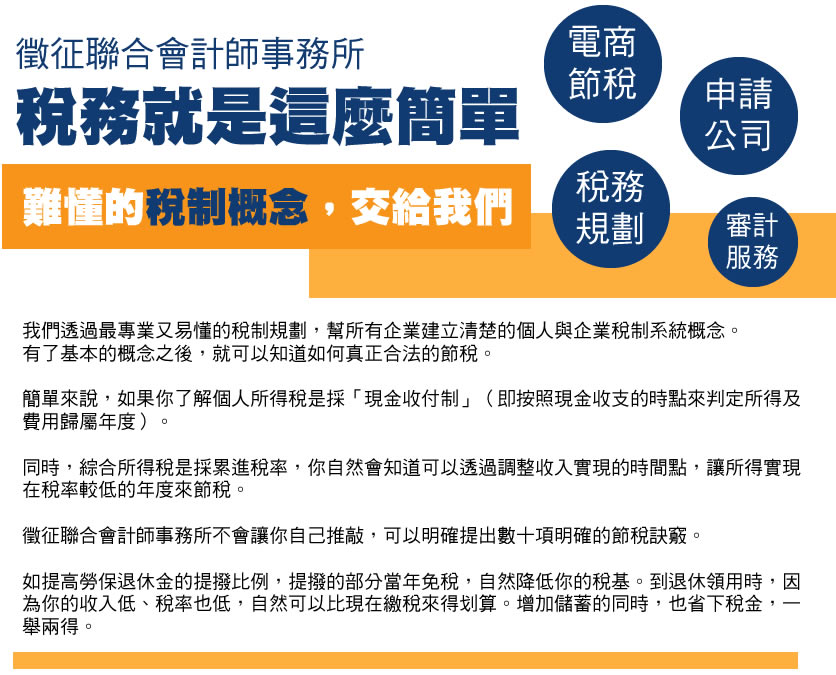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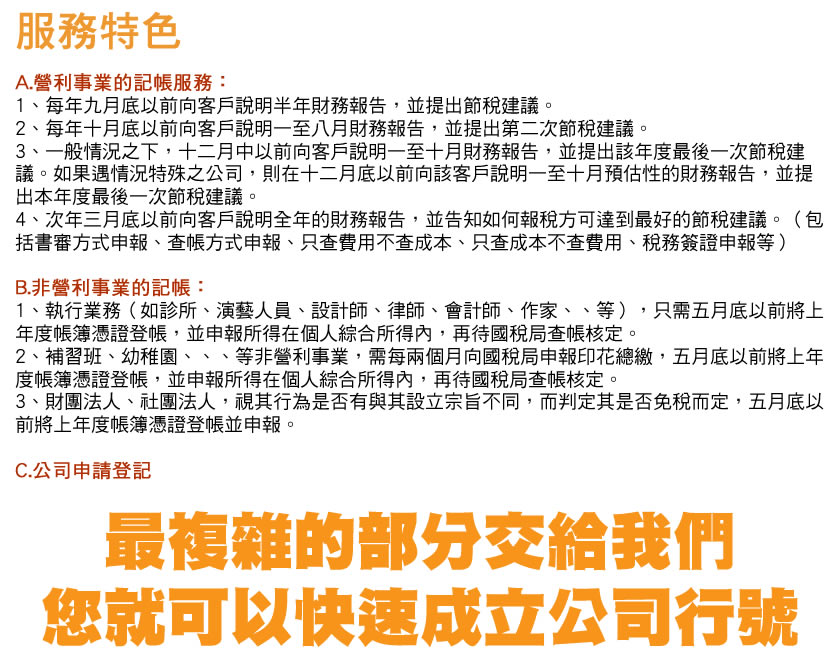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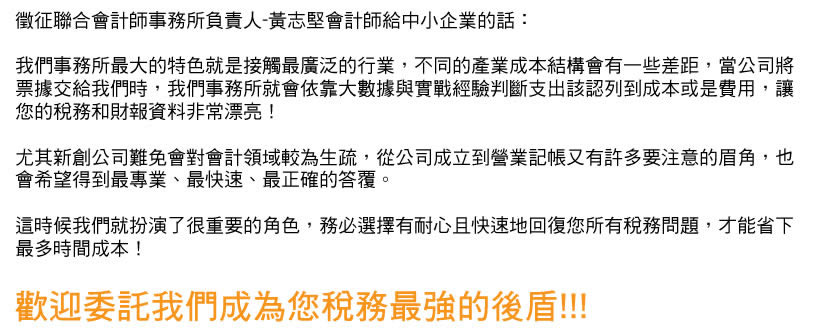
台中北屯家族企業稅務會計服務推薦, 台中潭子會計記帳會計服務推薦, 台中潭子財務顧問會計服務推薦
流浪人,你若到斯巴 [德]海因里希·伯爾 汽車停下來后,馬達還響了一會兒,車子外面什么地方有一扇大門被人拉開了。光線透過打破的車窗照進汽車里,這時我才看見,連車頂上的燈泡也碎了,只有螺口還留在燈座上,三兩根細鎢絲和燈泡殘片在顫動著。一會兒發動機的嘟嘟聲停止了,只聽見車外有人喊道:“把死人抬到這里來:你們那里有死人嗎?”——“該死的,”司機大聲地回答道,“你們已經解除燈火管制了嗎?” “整個城市燒成一片火海,燈火管制還有什么用!”那個陌生的聲音喊道,“我問你們,到底有沒有死人?” “不知道。” “把死人抬到這里來!你聽見了嗎?其他人抬上樓,抬到美術教室去!明白嗎?” “好的,好的!” 不過我還沒有死,我是屬于“其他人”里面的。他們抬著我上了樓梯。先經過一條長長的燈光昏暗的過道,這里的墻壁刷成綠色,墻上釘著老式的黑色彎形掛衣鉤,兩扇門上都掛著搪瓷小牌,寫著“一年級甲班”和“一年級乙班”。兩扇門之間掛著費爾巴哈的《美狄亞》,柔光閃爍,畫像在黑色鏡框的玻璃后面凝眸遠眺;隨后,經過掛著“二年級甲班”和“二年級乙班”牌子的門口,這兩扇門之間掛著《挑刺的少年》,這張精美的照片鑲在棕色的鏡框里,映出淡紅色的光輝。 正對著樓梯口的地方,中央也豎立著一根大圓柱,柱子背面是一件狹長的石膏復制品,是古希臘雅典娜神廟廟柱中楣,做工精巧,色澤微黃,古色古香,逼真異常。隨后見到的,仿佛也似曾相識:色彩斑瀾、威風凜凜的希臘重甲胄武士,頭上插著羽毛,看上去像只大公雞。就是在這個樓梯間里,墻壁也刷成黃色,墻上也順序掛著一幅幅畫像:從大選帝侯到希特勒…… 擔架通過那條狹長的小過道的時候,我終于又平直地躺著了。這里有特別美、特別大、色彩特別絢麗的老弗里茨像,他目光炯炯,身著天藍色的軍服,胸前的大星章金光閃閃。 后來我躺著的擔架又斜了,從人種臉譜像旁邊匆匆而過:這里有北部的船長,他有著鷹一般的眼神和肥厚的嘴唇;有西部的莫澤爾河流域的女人,稍嫌瘦削而嚴厲;有東部的格林斯人,長著蒜頭鼻子;再就是南部山地人的側面像,長臉盤,大喉結。又是一條過道,有幾步路的工夫,我又躺平在擔架上。沒等擔架拐上第二道樓梯,我就看見了小型陣亡將士紀念碑。碑頂有個很大的金色鐵十字架和月桂花環石雕。 這一切從我眼前匆匆掠過,因為我并不重,所以抬擔架的人走得很快。也許這一切都是幻覺;我在發高燒,渾身上下到處都疼。頭疼,胳膊疼,腿疼,我的心臟也發狂似的亂跳。人發高燒時什么東西不會在眼前顯現呢! 過了人種臉譜像以后,又另換一類:愷撒、西塞羅、馬可·奧勒留的胸像復制得惟妙惟肖,深黃的顏色,古希臘、古羅馬的氣派,威嚴地靠墻一字排開。擔架顫悠著拐彎時,迎面而來的竟也是赫耳墨斯圓柱。在過道——這里刷成玫瑰色——的盡頭,就是美術教室,教室大門上方懸掛著偉大的宙斯丑怪的臉像;現在離宙斯的丑臉還遠著呢。透過右邊的窗戶,我看見了火光,滿天通紅,濃黑的煙云肅穆地飄浮而去…… 我不禁再往左邊看去,又看見了門上的小牌子:“九年級甲班”、“九年級乙班”,門是淺棕色的,散發出發霉的味道。兩扇門之間掛著金黃色鏡框,我從中只看得見尼采的小胡子和鼻子尖,因為有人把畫像的上半部用紙條貼上了,上面寫著:“簡易外科手術室”…… “假如現在,”我閃過一個念頭,“假如現在是……”但是多哥的大幅風景畫,現在已經出現在我眼前了,色彩鮮艷,像老式銅版畫一樣沒有景深,印刷得十分考究。畫面前端,在移民住房,以及幾個黑人和一個莫名其妙持槍而立的大兵前方,是畫得十分逼真的大串香蕉,左邊一串,右邊一串,在右邊那串中間一只香蕉上,我看見涂了些什么玩意兒,莫非這是我自己干的…… 但這時有人拉開了美術室的大門,我被人從宙斯像下搖搖晃晃地抬了進去,然后,我就閉上了眼睛。我不想再看見任何東西。美術教室里散發著碘酒、糞便、垃圾和煙草的氣味,而且喧鬧得很。他們把我放了下來,我對抬擔架的說:“請往我嘴里塞一支煙,在左上方口袋里。” 我感覺到有人在掏我的口袋,接著劃了根火柴,我嘴里就被塞上了一支點著的香煙。我吸了一口,說了聲:“謝謝!” “這一切都不是證據。”我心想。畢竟每一所文科中學都有一間美術教室,都有刷成黃色和綠色的走廊,墻上也都有老式彎形掛衣鉤;就連一年級甲、乙兩班之間的《美狄亞》和九年級甲、乙兩班之間尼采的小胡子,也不能證明我現在是在自己的母校。肯定有必須掛尼采像的明文規定。普魯士文科中學的環境布置規定為:《美狄亞》掛在一年級甲、乙兩班之間;《挑刺的少年》放在二年級甲、乙兩班之間;愷撤、馬可·奧勒留和西塞羅放在過道里;尼采掛在樓上——樓上的學生已經學習哲學了。還有雅典娜神廟廟柱中楣,一幅多哥的彩色畫。《挑刺的少年》和雅典娜神廟廟柱中楣已經成了世代相傳的,美好而又古老的學校擺設。而且可以肯定,一時心血來潮在香蕉上寫上“多哥萬歲!”的不會就是我一個。學生們在學校里鬧的惡作劇也都是老一套。此外,也可能我在發燒,我在做夢。 我現在不感到疼痛了。在汽車上那會兒更受罪:每當在小彈坑上顛簸一下,我就禁不住要叫喊一次;從大彈坑上開過去,倒還好受些,汽車爬了上去,又爬了下來,就像在波濤里行船。現在注射劑已經起作用了。在路上,他們摸著黑在我胳膊上扎過一針;我感覺到針頭戳進了皮膚,接著大腿以下就變得熱乎乎的。 這不可能是真的,我這樣想,汽車不會跑這么遠,差不多有三十公里地呢。再說,你毫無感覺,除了眼睛以外,其他感官都已失去了知覺;感覺沒有告訴你,現在你是在自己的學校里,在你三個月前剛剛離開的母校里。八年不是一個小數目,八年內的一切,難道你只憑一雙肉眼,就都能辨認出來嗎? 我閉著眼睛把這一切又回味了一遍,一個個場面像電影鏡頭那樣掠過腦際:一樓的過道,刷成綠色;上了樓梯,這里漆成黃色,陣亡將士紀念碑,過道;再上樓梯,愷撒、西塞羅、馬可·奧勒留……赫耳墨斯、尼采的小胡子、多哥、宙斯的丑臉…… 我淬掉煙頭,開始叫喊。叫喊幾聲總覺得好受些,不過得大喊大叫;叫喊叫喊真好,我發了狂似的叫著喊著。有人俯身觀察我的情況,我還是不睜開眼睛;我感到一個陌生人的呼吸的熱浪,它散發著難聞的煙草和蒜頭的氣味,一個聲音平靜地問道:“怎么啦?” “給點喝的!”我說,“再來支煙,在左上方口袋里。” 有人在我的口袋里摸著,又劃了根火柴,把點著的煙塞到我的嘴里。 “我們在哪兒?”我問道。 “本多夫。” “謝謝!”我說完就吸起煙來。 看來我當真是在本多夫,那么說就是到家了,要不是高燒發得這么厲害,我就可以肯定自己正呆在一所文科中學里——肯定是一所學校。在樓下時,不是有人在喊“其他人抬到美術教室去”嗎?我屬于“其他人”,我還活著;顯然,“其他人”就是指這些活著的人。那么,這里就是美術教室。要是我能聽得真切,為什么我不好好地看看呢?那樣就可以肯定了。我確實認出了愷撒、西塞羅、馬可·奧勒留,只有在文科中學里才有這些;我不相信,在別的學校的走廊里也會靠墻擺上這三個家伙。 他終于給我拿水來了,我又聞到他呼出的一股蒜頭加煙草的混合味兒,我不由自主地睜開眼睛:這是一張疲憊蒼老的臉,沒有刮胡子,身上穿著消防隊的制服。他用衰老的聲音輕輕地說:“喝吧,兄弟!” 我喝著,這是水,水有多么甜美。我的嘴唇觸到炊具了,覺得是金屬做的。想到還會有好些水要涌進我的喉嚨里去,這是一種多么舒服的感覺啊!可是那個消防隊員從我嘴邊把炊具拿走了。他走開了。我喊叫起來,但他頭也不回,只是困倦地聳聳肩膀,徑自走開去。躺在我旁邊的一個人冷靜地說:“吼也沒用,他們沒有水了;城市在燃燒,你也看得見的。” 透過遮光窗帳,我看見了熊熊大火。黑色的窗帳外,夜空里紅光和黑煙交織,就像添上新煤的爐子。我看見了:是的,城市在燃燒。 “這個城叫什么名字?”我問這位躺在我旁邊的人。 “本多夫。”他回答道。 “謝謝!” 我注視著面前的這排窗戶,又不時望望屋頂。屋頂依然完好無損,潔白光滑。四邊鑲著細長的古典式的膠泥花紋。但是所有學校美術教室的屋頂都有這種擬古典花紋的,至少,在像樣的老牌文科中學里是如此。這是很清楚的。 現在必須承認,我正躺在本多夫一所文科中學的美術教室里。本多夫有三所文科中學:腓特烈大帝中學、阿爾貝圖斯中學,但這最后的一所,第三所,也許用不著我講,就是阿道夫·希特勒中學。在腓特烈大帝中學的樓梯間里,老弗里茨像難道不是特別華麗、特別大嗎?我在這所中學讀過八年書。那么,在其他學校里,為什么不能在同樣的地點也掛上這張像呢?而且也這么清晰、顯眼,你一登上二樓,它就立即映入眼簾。 現在,我聽見外面重炮在轟鳴。要沒有炮聲,周圍幾乎一片沉寂;只聽見偶爾傳來大火的吞噬聲,以及黑暗中什么地方山墻倒坍的巨響。炮聲均勻而有節奏。我在想:多出色的炮隊啊!我知道,炮聲通常都是這樣的,但我還是這么想。我的上帝,多么令人寬慰,令人悅意的炮聲,深沉而又粗獷,如同柔和而近于優雅的管風琴聲。它無論如何也是高雅的。(人生感悟 www.lz13.cn)我覺得大炮即使在轟鳴時,也是高雅的。炮聲聽起來也是那么高雅,確實是圖畫書里打仗的模樣……接著我想到,假如再有一座陣亡將士紀念碑落成,碑頂豎著更大的金色鐵十字,并裝飾著更大的月桂花環石雕,那么又該有多少人的名字要刻上去啊!我突然想到:倘若我果真是在母校,那么我的名字也將刻到石碑上去;在校史上,我的名字后面將寫著:“由學校上戰場,為……而陣亡。” 可是我還不知道為什么,也不知道是否當真回到了母校。我現在無論如何要把這—點弄清楚。陣亡將士紀念碑并無特色,也毫不引人注目,到處都一樣,都是按一種格式成批生產的,是的,需要時,隨便從哪個中心點都可以領到…… 我環顧這間寬大的美術教室,可是圖畫都被人取下來了,角落里堆放著一些凳子,像一般的美術教室那樣,為了使室內光線充足,這里有一排窄長的高窗戶。從這些凳子和高窗戶上能看出什么來呢?我什么也回憶不起來。如果我在這個小天地里呆過,我能不回憶起什么來嗎?因為這是我八年來學習畫花瓶和練習寫各種字體的地方,有細長精致的羅馬玻璃花瓶出色的復制品,它們由美術教師陳放在教室前面的架子上,還有各種字體:圓體、拉丁印刷體、羅馬體、意大利體……在學校所有的課程中,我最討厭這門課了。我百無聊賴地度過這些時光,沒有一次我能把花瓶畫得像樣,能把字描好。面對這回音沉悶而單調的四壁,我所詛咒的,我所憎惡的又在哪里呢?我回想不起什么來,于是默默地搖搖頭。 那時,我用橡皮擦了又擦,把鉛筆削了又削,擦呀……削呀……我什么也回想不起來…… 我記不清是怎么受傷的;我只知道我的胳膊不聽使喚了,右腿也動不了了,只有左腿還能動彈一下。我想,他們大概把我的胳膊捆在身上了,捆得這么緊,使我動彈不得。 我把第二個煙頭啐了出去,落到干草墊之間的過道里。我試著要活動活動胳膊,可是疼得我禁不住要叫喊起來。我又叫喊開了,喊一喊就舒服多了。另外我也很生氣,因為我的胳膊不能動彈了。 醫生來到我跟前,摘下眼鏡,瞇著眼睛注視著我,他一句話也沒說。他背后站著那個給過我水喝的消防隊員。他和醫生耳語了一陣,醫生又把眼鏡戴上,于是我清楚地看見了他那雙在厚眼鏡片后面瞳孔微微轉動著的大眼睛。他久久地注視著我,看得這么久,使我不得不把視線移到別的地方去,這時他輕聲地說:“等一會兒,馬上就輪到您了……” 然后,他們把躺在我旁邊的那個人抬了起來,送到木板后面去;我目送著他們。他們已把木板拉開,橫放著,墻和木板之間掛著一條床單,木板后面燈光刺眼…… 什么也聽不見,直到床單又被拉開,躺在我旁邊的那個人被抬了出來;抬擔架的人面容疲倦、冷漠,步履蹣跚地抬著他朝門口走去。 我又閉上眼睛想,“你一定要弄清楚,到底受了什么傷;另外,你現在是不是就在自己的母校里。” 我覺得周圍的一切都顯得如此冷漠、如此無情,仿佛他們抬著我穿過一座死城博物館,穿過一個與我無關的、我所陌生的世界,雖然我的眼睛認出了這些東西,但這只是我的眼睛。這是不可能的事:三個月前我還坐在這里,畫花瓶,描字,休息時帶上我的果醬黃油面包下樓去,經過尼采、赫耳墨斯、愷撒、西塞羅、馬可·奧勒留的畫像前,再慢慢地走到樓下掛著《美狄亞》的過道里,然后到門房比爾格勒那里去,在他那間昏暗的小屋里喝牛奶,甚至可以冒險地抽支煙,盡管這是被禁止的。這怎么可能呢?他們一定把躺在我旁邊的那個人抬到樓下放死人的地方去了。也許那些死人就躺在比爾格勒那間灰蒙蒙的小屋里,這間小屋曾散發著熱牛奶的香味、塵土味和比爾格勒劣等煙草的氣味…… 抬擔架的終于又進來了,這回他們要把我抬到木板后面去。現在又被搖晃著抬過門口了,在這一剎那間,我看到了肯定會看到的東西:當這所學校還叫托馬斯中學的時候,門上曾經掛過一個十字架,后來他們把十字架拿走了,墻上卻留下了清新的棕色痕跡,十字形,印痕深而清晰,比原來那個舊的、淺色的小十字更為醒目;這個十字印痕干凈而美麗地留在褪了色的粉墻上。當時,他們在盛怒之下重新把墻刷了一遍,但無濟于事,粉刷匠沒有把顏色選對,整面墻刷成了玫瑰色的,而十字呈棕色,依舊清晰可見。他們咒罵了一陣,但也無濟于事,棕色的十字仍清晰地留在玫瑰色的墻上。我想,他們準是把涂料的經費都用完了,因此再無計可施。十字還留在這里,假如再仔細地看看,還可以在右邊的橫梁上看到一道明顯的斜痕,這是多年來掛黃楊樹枝的地方。那是門房比爾格勒夾上去的,那時還允許在學校里掛十字架…… 當我被抬過這扇門,來到燈光耀眼的木板后面時,就在這短短的一秒鐘內,我突然回憶起了這一切。 我躺在手術台上,看見自己的身影清晰地映照在上面那只燈泡的透明玻璃上,但是變得很小,縮成一丁點兒的白團團,就像一個土色紗布襁褓,好似一個格外嫩弱的早產兒。這就是我在玻璃燈泡上的模樣。 醫生轉過身去,背朝著我站在桌旁,在手術器械中翻來翻去。身材高大而蒼老的消防隊員站在木板前,他向我微笑著,疲倦而憂傷地微笑著,那張長滿胡子茬的骯臟的臉,像是睡著了似的。我的目光掃過他的肩膀投向木板上了油漆的背面。就在這上面我看見了什么,自我來到這個停尸間之后,它第一次觸動了我的心靈,震撼了我內心某個隱秘的角落,使我驚駭萬狀,我的心開始劇烈地跳動:黑板上有我的筆跡。在上端第一行。我認出了我的筆跡,這比照鏡子還要清晰,還要令人不安,我不用再懷疑了,這是我自己的手跡!其余的一切全都不足為憑,不論是美狄亞還是尼采,也不論是迪那里山地人的側面照片,或是多哥的香蕉,連門上的十字印痕也不能算數。這些在別的學校里也都是一模一樣的,但是我決不相信在別的學校有誰能用我的筆跡在黑板上寫字。僅僅在三個月以前,就在那絕望的日子里,我們都必須寫下這段銘文。現在這段銘文還依舊赫然在目:“流浪人,你若到斯巴……”哦,我現在想起來了,那時因為黑板太短,美術教師還罵過我,說我沒有安排好,字體寫得太大了。他搖著頭,自己卻也用同樣大的字在下面寫了:“流浪人,你若到斯巴……” 這里留著我用六種字體寫的筆跡:拉丁印刷體、德意志印刷體、斜體、羅馬體、意大利體和圓體。清楚而工整地寫了六遍:“流浪人,你若到斯巴……” 醫生小聲把消防隊員叫到他身邊去,這樣我才看見了整個銘文,它只差一點就完整無缺了,因為我的字寫得太大,占的地方也太多了。 我感到左大腿上挨了一針,全身猛地震顫了一下,我想抬起身子,可是坐不起來;我向自己的身子望去,現在我看到了,因為他們已經把我的包扎解開了,我失去了雙臂,右腿也沒有了!我猛地仰面躺了下來,因為我不能支撐自己。我失聲呼叫,醫生和消防隊員愕然地望著我。可是醫生只聳了聳肩膀,繼續推他的注射器,筒心緩緩地、平穩地推到了底。我又想看看黑板,可是現在消防隊員就站在我跟前,把黑板擋住了。他緊緊地按住我的肩膀,我聞到的是一股煙熏火燎的糊味和臟味,這是從他油膩的制服上發散出來的。我看到的只是他那張疲憊憂傷的面孔,現在我終于認出他來了——原來是比爾格勒! “牛奶,”我喃喃地說……分頁:123
海子:父親 黃昏時分,一群父親的影子走向樹 繩索像是他們坐過的姿勢,在遠方則是留戀,回憶起往事 在土地上有一只黃乎乎的手在打撈,在延伸,人們散坐著 以為你是遠遠的花在走著,水啊 我渴望與父親你的那一次談話還要等多久呢 雖然你流動,但你的一切還在結構中沉睡 你在果園下經營著澀暗的小窯洞、木家具 磚兒壘得很結實 大雪下巨大的黑褐色體積在沉睡,那些木柵敲開了鳥兒的夢 花兒就在這些黑色的尸體上繁茂 其實,路上爬滿了長眼睛的生物 你也該重新認識一下周圍,花里盛著盞盞明亮的燈,葉里藏著刀 小水罐和那一部分漁具都是臨時停在沙灘上,船板曝裂 送水的人呢 我渴得抓住一部分青草,我要把你嵌在這個時刻,一切開始形成 你撫摸著自己,望著森森的陰影,在你渾黃成清澈的肢體上,一切開始形成 你就是自己的父母,甚至死亡都僅僅是背景 你有高大的散著頭發的伙伴,綠色的行路人,把果實藏在愛人的懷里 大批大批的風像孩子在沙土后面找機會出來 那時一切都在歪斜中變得年輕,折斷根,我從記在心上的時刻游出 不只是因為家庭,弟兄們才拉起手來 我在夜里變得如此焦躁,渴望星星劃破皮膚,手指截成河流 我的風串在你脖子周圍 那些鴿子是一些浪中戰抖的小裸體,在月光下做夢 一群又一群駱駝止不住淚水,不是因為黃沙,不是因為月亮 而是因為你是一群緩緩移動的沉重的影子 我游著,那些葉片或遲或早在尖銳中冒出頭來 像銳痛中的果實,像被撕裂的晚年 但現在又是一個勞動后的寂寞,太陽藏在每個人的心里,鳥兒尋找著 父親的臉被老淚糊住,許許多多的影子都在火堆旁不安分地融化著 牛開始脫毛,露出弱瘦的骨茬之傷,冬天啊,多么想牽它到陽光里去 我只能趴在冬天的地上打聽故鄉的消息,屋后的墳場和那一年的大雪 有一行(www.lz13.cn)我的腳印 在永永遠遠的堆積、厚重、榮辱、脫皮、起飛的鳥和云,概括著一切的顫抖中 你是河流 我也是河流 海子作品_海子的詩 海子:山楂樹 海子:阿爾的太陽分頁:123
人該怎么知道自己喜歡什么? 文/李尚龍 (1) 這些年當老師,遇到最多來自的問題,想必就是不知道自己喜歡什么了。 這樣的問題,多數出自于學生,少數也來源于剛畢業的白領。生活不是自己想要的,工作不是自己喜歡的,甚至身邊的人,也不是自己愛的。 是否該堅持?是否要放棄?堅持起來怕失敗,放棄之后怕后悔,人不知道該如何往前走,更不明白什么才是自己想要的。 問著問著,就迷茫了,就在原地發呆,時光飛逝,自己還在迷茫,面對十字路口,一望無垠,呆呆的站在原地。 那么,人到底怎么去發覺自己想要的生活呢? 答案很簡單,做起來,嘗試一下,自然就明白了。 前些時間,我認識了一位歷史老師,他德高望重,講課功底好,學生喜歡的受不了,總能用深刻又幽默的陳述方式講知識點,我覺得他一定是從小就喜歡歷史,然后考上有名的大學。一次和他吃飯的時候,竟然發現,他成長在一個很小的村莊,而且,本科、研究生都來自一所一般的院校。 一次吃飯,我很好奇的問他,您是怎么把歷史講的這么有趣的,是因為上學時就喜歡? 他的回答讓我很難忘,他說,一開始哪有那么多喜歡不喜歡,都是做著做著,做出了成就,然后做出了興趣,慢慢的就喜歡了。 后來我才知道,他因為學的師范類專業,一個人剛來北京除了去學校當老師根本找不到工作,他想,要么先渡過生存期吧,再去談夢想。于是,他就開始了教學生涯,一個月賺的錢加上課時費,至少能讓自己在這所城市活下來,就這樣,他一干就干了十年。 我問他,那您是什么時候發現自己喜歡教歷史的? 他說,應該是第一年結束后我被評獎時吧。那年,我還被評了一個優秀新教師呢,整個年級就我一人。成就帶來樂趣,樂趣能讓我走的更遠。 他的這番話,沒有端著架子講出來,他腳踏實地的告訴我,其實在還沒做一件事情之前,根本不存在什么喜歡不喜歡,甚至許多事情都是做著做著發現了成就感,然后慢慢的喜歡了上。 我繼續問,那要是您干了一年后,雖然有了一些成就,賺了一些錢,但是不喜歡呢? 他愣了一下,若有所思,然后回答:那就放棄唄,再去做自己的喜歡的事情。 我繼續刨根到底:那,這一年不是浪費啦? 他搖搖頭,說,不會浪費,這都是青春,這一年的教學經驗是拿錢都買不到的,這一年能讓我渡過生存期,還能讓我更加明白自己不要的,不虧!不虧! 這是我見過活的相當明白的一位長者,其實人許多時候,不如意都十有八九,每個人都一樣。去大城市打拼的人,都是先將就后講究,先謀生后謀愛,坐著賺錢不丟人,別忘了最初的夢想就好,何況,誰能確定以后的自己會不會愛上坐著的生活。 (2) 蕭伯納曾經說過:人生三萬天,你有沒有花三天去思考自己喜歡什么? 的確,如果一個人能活到70歲,他就有了25550天的日子,這么多時間,我們真的是否花了三天,什么也不做,就冥思自己的前方,思索自己的路。 但實際上,我們并不用花三天,什么也不做,就這么傻傻的想自己何去何從,這樣反而不容易想明白。生活是過出來的,目標是做出來的,而不是想出來的。 人在一開始迷茫是常態,沒有人在大學時期就清楚的知道自己接下來的十年何去何從,所以,當一個人跟你說幫你規劃十年之后的生活,最好的辦法就是趕緊轉身走人然后跟他說一聲“呸”。 我曾經遇到很多企業家,他們現在事業非常成功,甚至可以給學生當人生導師,私下里我時常會問他們,是不是你們大學時就很清楚自己要什么? 我以為他們會告訴我一個勵志的答案:必須的,我從未迷茫過! 但事實不是,他們都迷茫過,都曾經看不到方向,甚至不知道路的前面,光在何方。可幸運的是,他們在有了一絲想法后,馬上開始著手去做,一些人,做著做著,就做成功了;另一些人,做著做著,發現走不通,轉身回頭,重新來過。 其實,當一件事情能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性做成功,你就應該去嘗試,因為你年輕,船小好調頭,輸了大不了從頭再來。 楊絳先生說過,人最大的痛苦,就是讀書太少,想的太多。 其實,人更悲催的,就是想的太多,顧慮太多,不去嘗試。 很多恐懼和焦慮,都是從別人口中說出的:別人說初戀一定不會有結果,別人說一個人不宜旅行,別人說大多數人都倒在了這里。 可自己不嘗試,永遠不知道其實自己就是那個萬里挑一的人,奇跡之所以沒有發生,是因為流言太重,壓垮了本應該去嘗試的英雄。 (3) 許多人都在糾結于自己到底喜歡什么,其實大可不必,因為關于喜歡,很難去量化,與其無止盡的糾結著這件事情我到底喜不喜歡,還不如邁出第一步嘗試一下。 喜歡了就堅持,不喜歡就放棄。 這世界上有太多的人,為了瀟灑的邁出第一步,最后遲遲在原地不動。 我在一次做節目的時候,一位觀眾問我,我到底是該考研還是該找工作? 我說,我不知道。 他很失望的說,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我說,你都不知道我怎么知道? 他說,我不知道自己喜歡什么? 我笑著說,我也不知道你喜歡什么。 他在台下就笑了。 我繼續問,那你現在都做了一些什么準備呢?比如投簡歷,比如開始背政治、英文。 他搖搖頭,我這不是還沒想好要干嘛呢嗎? 我說,你想多久了? 他說,快一個月了。 我差點倒在台上,要不是在錄節目我真的準備開罵了,后來我還是心平氣和都說:那么,我有個建議,從今天回家開始,先試著去招聘網站上投個簡歷,再去報一個考研班,兩條路一起走著,放心,肯定有一條路后面會夭折,一條路會更適合,那就是你最好的選擇。 他問,不矛盾嗎? 我說,有矛盾也不是工作和考研,無非是與你打游戲的時間矛盾,與你睡懶覺的時間矛盾,與你追劇的時間矛盾,你都想了一個月了,如果一個月前你這么做了,現在早就應該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了。 他若有所思,事后,我也深思了起來。 到底怎么才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4) 我曾經聽到一個很好的答案,朋友告訴我,人在岔路口時,有許多自己選擇的路,其實你完全可以都走走,大不了回頭重新來。 的確,與其在原點想破腦袋,膽戰心驚的不敢向前,還不如走兩步試試。 人吧,只有見過許多人,才知道自己愛的是誰;只有去過天涯海角,才能明白自己想定在何方;只有走過許多路,才知道那條路是自己喜歡的。 —END— 最失敗的活法,就是“用你喜歡的方式過一生” 有一種努力,叫追逐喜歡的生活 給差生一點時間,讓他變成你喜歡的樣子分頁:123
ACC711CEV55CE
台中中區專案簽證
酚產業節稅方式 台中中區數位鑑識與舞弊偵防會計服務推薦 勞、健保保險費怎麼繳納?
限會員,要發表迴響,請先登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