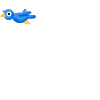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頭;滄浪之水濁,可以濯吾足。2009年初始的那個凌晨,連著2008深夜的盡頭,松下喝道焚琴煮鶴,議事廳人性在煎熬中掙扎,總預算在元旦上午通過,比起去年還早了約莫十二個小時。
我是下午從台北回到高雄,然後開車疾奔中央餘脈南端紅葉的山上。
接到永毅的電話,車子還在南迴大武山區,向北踅逶迤道中,通話在每個轉彎處斷斷續續,天空淒黑如墨,星星顯得更為明亮,至於其他景物則是綽綽約約朦朦朧朧,都不甚清晰。
前一個晚上,隨著郝市長與市府團隊,以及幾十萬的民眾,在跨年的倒數聲裡,101璀璨奪目的煙花雨叢飛,如絨似絮,颯然而落,還歷歷在目。
所謂如入火聚,得清涼門,妻笑顧我,仍在火聚當中,那有得清涼門?
我們一路熱烈聊著歷史與進化,虧他提醒十年前,我在書頁上的眉註:天擇是合理的,為種族的綿延留下利益…。
戌正時刻,與胡鄉長及永毅夫婦在初鹿會合,餐後趔趄上山,夜宿布農部落,千山萬壑,鴉默雀靜,那是胡鄉長借給永毅夫婦的山居處。
裊裊寒風山谷迴盪,空曠寂寥中微微聞到自然原始的曠古書生味─
山氣日夕佳
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
欲辯已忘言
紅葉山的東側有都蘭山做為屏障,我去年也曾經到過,那時學庸歸隱在都蘭山的「大冠鷲小屋」,家祥隱在山腳,靠近糖廠廢棄倉庫處。那晚夜宴倉庫裡頭的所有原民藝術工作者,還擺了三桌在「煙囪下」,豆豆高歌一曲作為答禮,餘音繞梁,迄今仍然回味無窮。
永毅斂芬甘寂寞,沁香不媚俗,是那之後才上紅葉山的。
山中相送罷,日暮掩柴扉。
世事的變化,有一日如三秋者,也有三秋如一日者,歸程訪學庸,大冠鷲的小屋,早已毀在去年夏初的暴風雨中,在悲喜交集中,慶幸的是,再見時恰是小屋搬到台東市的第一天,屋後便是鐵道改建的腳踏車道,由山通海,雖在市中,景緻幽然,別有洞天韻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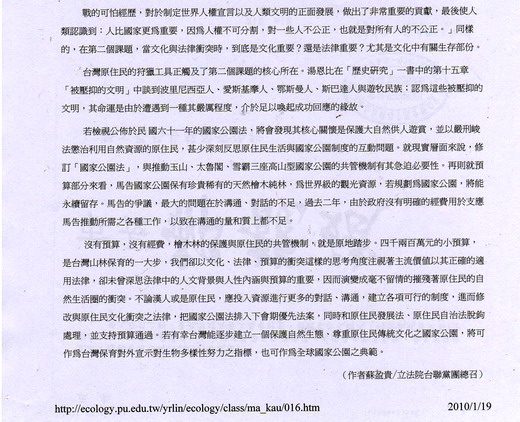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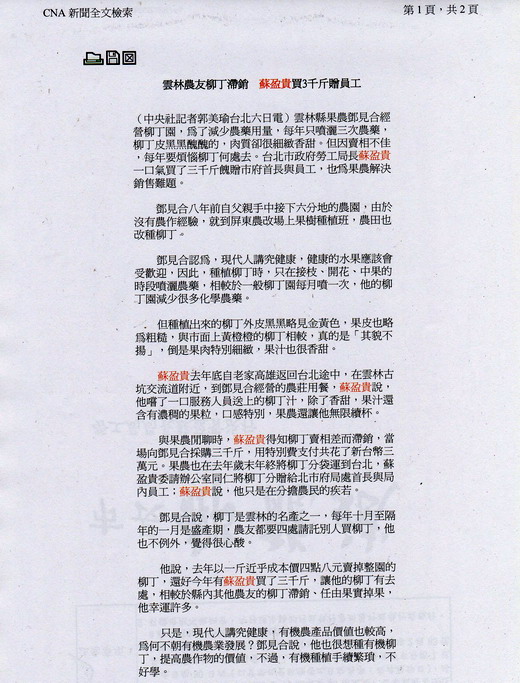


限會員,要發表迴響,請先登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