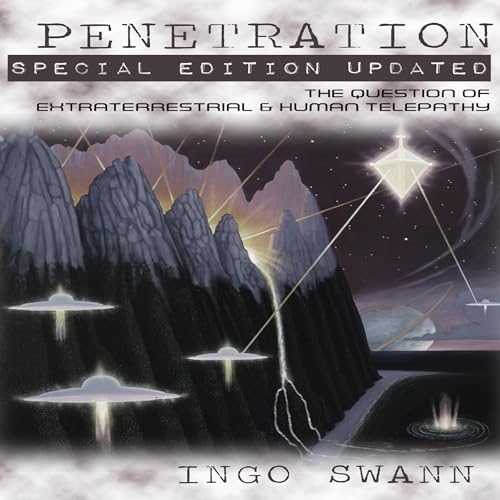
本文摘自此書內容
該機構的章程看似簡單:月球上的UFO和外星人,以及對外星人心靈感應/精神控制能力的擔憂。
該機構極度隱秘,沒有任何書面記錄,因此也沒有書面保密協議。只有口頭協議,而英戈的協議幾年前就失效了。
如今,在這個UFO「公開性」蓬勃發展的時代,他講述了在華盛頓特區附近一個秘密地下設施舉行的會議,以及被帶到北極圈附近一個偏遠地區,目睹一架巨大的UFO預計將降落在阿拉斯加湖面上的故事。
本書探討了尚未開發的人類心靈感應,並將其與可能存在的成熟外星心靈感應進行了對比,後者可能具有多種不同的形式。
英戈·斯旺也探討了這樣一個事實:我們對月球的官方認知遠遠超過我們承認的程度——包括它的起源、大氣層、居住者以及許多其他不尋常的特徵。
《滲透》一書探討了我們能夠更瞭解地球之外之人(反之亦然)的途徑之一——心靈感應。
我們是否有辦法回答許多人長期以來一直在追問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問題?本書將解答其中一些問題。
此外…在最近發現的關於他對火星進行心靈探測的缺失章節(“9”)中,英戈斷言,還有一個更大的問題在起作用——
“為什麼具有群體意識的人類,可以說,幾乎是群體意識地‘合謀’迴避*某些問題,並且始終如此?”
這個問題,英戈深藏於意識之中,他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直到2013年去世。

作者: 著名靈媒研究員英戈·斯旺(Ingo Swann)揭露了一系列長期秘密的與“深黑”機構的經驗。
就在那次邂逅發生幾天後,我返回紐約,試圖靠著重新回到研究中來舒緩心神。我有點害怕、又有點期待阿克塞爾羅德先生會不會打電話過來。結果我還真的沒有久等。
一天晚上,我的電話突然響起,對方是一個女人,她用愉快的聲音問道:
“是斯旺先生嗎?”
我回答:“是的。”
“你的一個朋友想跟你談談。”
“好的。”
“他想用另一部電話跟你溝通。你能在今晚七點半準時抵達大中央總站嗎?”
“我想沒問題。”我說。
“非常好。到時請在中央大廳的詢問處附近等候,直到你看見認識的人出現。”
中央總站
然後我的電話忽然就斷電了!沒有一句再見或謝謝,沒有嘶嘶聲、靜電聲或撥號音——就好像它壞掉了一樣。過了一會兒,我再次拿起話筒:它還是無法使用。於是我搭上地鐵來到大中央總站,擠進熙來攘往的人群,在那座宏偉的大廳旁的詢問處等待。

詢問處有一個很大的時刻表,原來我早到了五分鐘。五分鐘過去了,然後十分鐘也過去了。我心想隨便吧,接著就去附近的商店買了一杯咖啡,又點了一支雪茄(那時公共場所還沒有禁止吸煙)。
這時,在大約十英呎遠的方向,我突然看見了一個熟悉的身影,我想我可能之前就已經注意到他了,但卻沒有放在心上。當然,這次又是其中一個雙胞胎,但他的穿著打扮讓他看起來就像無家可歸、在中央總站裡閒晃的流浪漢。發現我認出他後,他將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我猜是示意我不要輕舉妄動。不知何故我的手有點顫抖。我喝了口咖啡。他花了大約十分鐘的時間在那裡仔細觀察總站內的旅客們的行李。
最後他向我輕輕點了頭,便朝拱廊東邊的方向走去,離開了大廳。我想這是要我跟上去。他走向一條通往萊辛頓大道的走廊。這條走廊曾經有、且現在仍有一些可以通往地鐵入口的樓梯。確認我有跟上來後,他就繼續走下去。我一直跟在後面。
然後他停在一排電話亭旁邊(它們現在已經被拆掉了),並走進去,我可以透過玻璃看見他正在撥打電話(以前的電話亭是沒有門的)。
我保持著一定的距離,但我確定他沒有對話筒說過一個字。接著他把話筒放在檯子上,就出來了。我知道該是我接電話的時候了。
話筒的另一頭十分安靜,我不知道該說什麼,所以我只好打聲招呼:“你好。”
“斯旺先生?”又是那位開朗的女士。
“是的。”
“你右手上的那個東西是什麼?”
“哦,你是說我的刺青?”
“它是什麼顏色的?”
“主要是綠色的,”我回答。
“很好,請稍候,連線需要一些時間。”
連線?什麼意思?接下來出現了一連串嘟嘟聲、噪音和不同形式的靜電雜訊。
最後,阿克塞爾羅德先生的聲音終於出現了。
“我很抱歉不得不如此大費周章,”他說:“但我們必須讓你接這通電話,我們的談話要很小心,並且你正在被監視。”
我正準備打招呼,可是阿克塞爾羅德的聲音卻變得非常嚴厲。
“除了回答我的問題之外,什麼也別說。”
我想他十之八九是要來問我發生在夢幻之城的那件事,於是我安靜得像隻老鼠。
“我也許顯得有些咄咄逼人,”阿克塞爾說:“但我們必須弄清楚,你為什麼會出現在洛杉磯的那家超市裡?”
“我那時跟幾個朋友住在一起,我們決定要煮一頓大餐。我想要做橘子果凍、煎羊排,然後再加入些洋薊。所以我們去買食材。”
另一頭是一陣沉默。然後:
“沒有別的原因了?”
“沒有。”
“沒有。”
又是一陣沉默。“你為什麼要一直盯著她?”
“好吧,天哪,她看起來很性感,她的衣服都快要掉下來了。我本來站在她後面,所以我想靠近點偷瞄她幾眼。她當時正在翻找洋薊。”
“你確定沒有其它原因。”
“我確定。”
經過一陣更長的沉默後:
“你對她有什麼想法?”
現在輪到我沉默片刻了。
“嗯,我不知道為什麼——但我就是覺得她跟我們不太一樣。”
“你覺得她是什麼?”
這個字差點就噎在我的嘴裡。
“外星人!”
“你為什麼會這麼想?”
“我也不知道,就只是一種感覺。她引起了某種共鳴之類的東西。她讓我感到背脊發涼,我脖子後面的寒毛都豎起來了。”
“你覺得你以前有見過像她這樣的人嗎?”
“如果你的意思是我以前有沒有見過外星人,答案是沒有。當然,我見過不少奇怪的人,但從來沒有人像她那麼奇怪。”
“你為什麼要急著跑走?”
“我發現雙胞胎在那裡,我意識到事情似乎不太妙。我有點被嚇壞了。”
“好吧,”阿克塞爾羅德停頓了一下,然後說:“我姑且相信你。你認為她有察覺到你的感應嗎?”
“我不知道。她一直在翻找洋薊。整件事發生得太快了。她自始自終都沒有看過我一眼,但我不能保證,因為她戴著那副奇怪的紫色太陽眼鏡。”
“請仔細回想!”阿克塞爾很堅持。“這非常重要。她有沒有注意到你?”
我開始有點發抖。“沒有...我覺得她沒有。”
“是你先到那裡,還是她先到的?”
“嗯,是她先到的。我一開始是在走道上看見她,然後才決定走上前去看個清楚。”
“你確定?”
“確定什麼?”
“那麼,她有沒有試圖接近你,還是你試圖接近她?”
我很想脫口而出,他為什麼不直接去問那對雙胞胎,畢竟他們全程一直在監視她。
“我認為她根本沒有注意到我,當我走過去的時候她已經在那裡了!”
我的語氣充滿了絕望。
一陣沉默。太好了。
“好的。我有義務告訴你,她非常危險,如果你再次見到她,尤其是當她主動接近你的時候,請務必盡力保持你與她之間的距離。但要表現得自然點,要自然地去做。”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所以我一句話也沒說。
“你明白嗎?”
“不完全是,”我小聲說道:“但我想我理解了。”
“很好。你在SRI的遙視研究進展如何?”
這時,汗水已經從我的腋下流下來了。
話題的改變著實讓我鬆了一口氣。
“非常好。我們取得了很不錯的成績,我每天都有新的發現。我的目標是要讓整體的準確率達到至少65%。”
“嗯,”阿克塞爾吐了口氣。“這真的做得到嗎?”
“有可能,但坦白說,不是每次都很順利。我們所有人,包括我們的客戶,都對這個目標很感興趣。”
又是一陣長長的沉默。“他肯定會感興趣...我們有一項特別的任務...你能在真的做到65%的時候知會我們嗎?你認為需要多長時間?”
“呃,我們會盡量努力,否則明天可能就拿不到更多預算了。”
更多的沉默,這次的沉默十分漫長。我握著話筒的手已經出汗了。最後:
“你的辦公室裡有一張桌子,對吧?”
“是的。”
“當你成功達到65%的時候,拿一張普通的銅版紙,寬八英吋、長十一吋,在上面寫下65,然後把它放在吸墨紙下面。”
他怎麼知道我在SRI的辦公桌上有吸墨紙呢?
“好的,”我說。
“很好。然後我們就會與你聯絡,明白了嗎?”
當然沒有。我什麼也不明白。但我還是回答:
“明白。”
“我想,”阿克塞爾繼續說道:“你應該理解我的意思...不能讓任何人知道這一切?”
“我瞭解。這些事情很嚴重——而且‘危險’,對吧?”
我覺得最好還是不要將我們在洛杉磯的晚餐談話告訴他,顯然我的朋友們早已對性感的外星人見怪不怪了。
“就是這樣。”
阿克塞爾羅德掛斷了電話。這些傢伙,無論他們到底是誰,總是一句再見或謝謝都不會說。線路暫時不通了,因為“連線”(不管它是什麼意思)已經被斷開。但撥號音很快就又恢復了。雙胞胎看見我掛上電話,當我從電話亭走出來時,他若無其事地拿著一個紙杯朝我走來,彷彿是在乞討施捨。
杯子上面貼著一張小卡片:
“直接前往萊辛頓,叫輛計程車。我們會在後面保護你。不要回頭。”
我非常緊張,但又覺得這麼做似乎挺合適,所以我大膽地掏出一枚二十五美分硬幣,扔進他手上的杯子裡,裡面還有其它硬幣。我走向萊辛頓大道,快速地攔了輛計程車,期間完全沒有回頭。但我沒有直接回家,而是前往第八街和第三大道的拐角,並在那裡徘徊了一陣子,想確認我是否在被跟蹤。
我去了附近最喜歡的一家酒吧,喝了好幾杯便宜的啤酒。我的腦子正在不停胡思亂想。在這之後有一段時間裡,我一直深陷在偏執的恐懼情緒中。我總覺得彷彿到處都有外星人和/或阿克塞爾的手下或特務。
更何況呢?這個阿克塞爾羅德和他的手下究竟是何方神聖?
我花了幾天、幾個星期的時間仔細思索各種可能性。CIA、KGB、摩薩德、MI5,還是一些絕頂機密的軍事單位?
最糟糕的可能性是,或許他們其實也是外星人。
也許一場太空歌劇正在上演,兩派不同的外星人正在地球上進行某種戰爭——同時雙方都想確保人類永遠不會發現他們的存在、發現自己的心靈能力。很荒唐,對吧?這可以說是最異想天開的天邊!甚至連這個天邊到底有沒有一個邊都很難說。
最糟的是我無法,當然也不敢跟任何人談論這些東西。我確信我已經踏入了一個超出自己能力所及的世界。我很害怕我可能會被殺害或被綁架——成為失蹤人口——最終在月球的礦坑裡挖礦。即便我現在寫下這些,我相信很多人仍會覺得這一切實在太令人難以置信,對此我也無法反駁...
大約過了一年後,即1977年6月,我將那張寫著65的紙壓在了SRI辦公桌的筆記本下,而這是一個非常安全、戒備森嚴的場所。我的辦公室大門設有密碼。密碼只有我知道,它只存在我的腦海中。就這樣三個月過去了,我每天下午都會檢查吸墨紙有沒有異狀。有一天早上,我拿起吸墨紙,手上的寒毛再次豎起。下面那張紙不見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像粉筆的痕跡,上面潦草地寫著幾個字:“等待聯絡。”我把粉筆灰掃進垃圾桶,然後坐下,感到異常緊張。我與阿克塞爾羅德及其團隊的下一次見面將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不開玩笑!如果說我本來還對“聯絡”抱有任何懷疑的話,它們也很快就會被徹底驅散。
我甚至差點在這個過程中喪命。
長途旅行
說好的聯絡終於在1977年7月的一天發生了,也就是我發現那些粉筆字的幾天後。
史丹佛研究所的“校園”中有一間非常漂亮的餐廳,我經常與同事一起去那裡吃午餐,尤其是在有“貴賓”來拜訪的時候。 要去餐廳得先穿越一個寬敞的大廳,大廳的其中一側聳立著一顆直徑約六英呎的巨大地球儀。
我已不記得那天星期五我們是與誰一起共進午餐,但就在我們穿越擁擠的大廳要前往餐廳的時候,阿克塞爾羅德先生居然就站在那裡,他站在那顆地球儀的旁邊,顯得並不起眼。
當他注意到我看到他時(我其實已經停下腳步),他便快步走進了隔壁的男廁。
所以我只好照著他的意思跟上去。我向同事表示道歉,說我想去一趟小便。為此,我還得從負責餐廳的女士那裡拿取廁所的鑰匙。由於與五角大樓的聯繫可能會讓這裡成為恐怖分子的目標,因此SRI的所有東西平時都是上鎖的。
我一進入男廁,阿克塞爾就迅速用鑰匙鎖上了門,並在我耳邊悄悄說道:
“你現在方便立刻去度過週末假期嗎?我想帶你去一個地方,給你看看一些東西?只要點頭或搖頭就好。”
我點頭答應。
“大廳外的停車場有一輛車,我在那兒等你。編一個逼真的故事給你的朋友們,因為你可能得離開四天的時間。”
然後他就打開門出去了。我一邊回去找朋友,一邊快速思索著我該怎麼編出一個“逼真的故事”。但我滿腦子其實只有阿克塞爾羅德怎麼會有男廁鑰匙。
我告訴我的同事們,我剛才忽然想起自己與舊金山的一些朋友有約,所以我快速和他們道了別。
停在外面的那輛“車”是一輛車輪很大的吉普車,司機就是阿克塞爾本人。
我們一語不發地離開了SRI的停車場。阿克塞爾開上高速公路,朝著聖荷西的方向前進。
然後:
“你曾經看過UFO嗎?”他問。
“我想是的。”
“能描述一下嗎?”
“嗯,那是在我還在猶他州的圖埃勒(Tooele)上高中的時候,我經常爬到那裡的一座大山的山頂上,不過人們都叫它小山丘。
從山丘上可以俯視整片伯納維爾山谷(Bonneville Valley),還有更北邊的大鹽湖(Great Salt Lake)。湖裡有面有一座很大的島。那片景色真是美極了。
我經常在傍晚的時候跑去那裡小睡片刻,但有一天,我忽然注意到在鹽湖城的上空有一顆非常高的光點。
它正在向西飛行,一開始我以為只是一架正在快速噴射的飛機。
但它卻在飛到一半的途中突然往下彎了一個直角,不是轉了一個彎,而是剛剛好彎了一個九十度。
它直直地往下墜落,似乎是進入了那座島或山脈的陰影裡面,因為當時太陽正在西邊沒下,所以影子是往東的。
我趕緊站起來,我以為那架飛機是爆炸或墜毀了。
可是就在那個時候,那東西居然又直接從陰影中升起。
它上升到原來的高度,大概是三萬五千或四萬英呎高,然後就消失在西邊了,其速度之快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我對它到底是什麼始終毫無頭緒,但在多年後,當我得知有些UFO會進行直角轉彎後,現在我可以肯定它一定就是UFO。
它所做的事情完全超出了我的理解。整個上升下降與加速度的過程都是在不到一分鐘的時間內完成的。不過,我真正看到的其實也只是一顆光點而已。”
阿克塞爾羅德什麼話也沒說。那天天氣很熱,吉普車裡沒有冷氣。
然後..
“我也許可以讓你近距離觀察一架UFO。你有興趣嗎?”
在阿克塞爾羅德可以準備的所有驚喜中,恐怕沒有什麼可以比這更令我驚訝得下巴都快掉下來了。
“你是說這附近就有一個!你們捕獲了一架UFO?”
“哦,不是的。我們必須出一趟遠門。然後步行前往一個人煙罕至的地方。你願意嗎?”
開什麼玩笑!我怎麼可能不願意。
阿克塞爾羅德最後把車子開到了聖荷西機場,他把吉普車停在一個航站大樓的“禁止停車區”,然後我們穿過大廳,走到了一架已經等候多時的李爾噴射機旁。過去也曾有其他人坐著類似的噴射機來接我,他們大多是有錢人,想要利用心靈能力來發現失落的寶藏和石油礦藏。我喜歡這些噴射機優雅的外型,它們就像是地位與權力的象徵,是代表一個人已經成功“飛黃騰達”的身份證明之一。

在噴射機旁邊等候的又是其中一位無處不在的雙胞胎,這次他穿著橄欖綠連身褲並戴著頭盔——典型的“軍人”打扮。
大約三分鐘後我們就升上了高空。駕駛噴射機的是另一位雙胞胎。
上升到空中後,雙胞胎遞來了一些三明治,阿克塞爾說:
“我們要去一個很偏僻的地方,那裡的環境非常寒冷且惡劣。
但我們會提供你需要的一切,包括你的雪茄(他笑著說),吃完飯後你不妨稍微睡一會。這趟飛行大概要五個小時左右。
等我們到達那裡的時候,天應該已經黑了,然後我們還要再開大約兩小時的車。
別問我們要去哪裡,因為我不能告訴你——而且(他顯得有些猶豫),你還是別知道為好。”
“你知道的,阿克塞爾,”我說:“如果能讓我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我就可以更好地使用能力。”
阿克塞爾皺了眉,盯著他正在吞嚥的三明治。
“好吧,我不能告訴你太多,否則對我們的任務有危險,甚至對你也有危險。
但讓我來問你吧,你覺得到底發生了什麼...?”
典型的“阿克塞爾羅德先生”單方面反問式對話又來了。
“嗯,我想你們,不管你們到底是誰,都正在面臨一個大麻煩,要我說的話,也許地球正受到某種包圍。
UFO簡直無處不在,有成千上萬的人們都看過。
然而,它們十分難以捉摸,卻又令人不得不警惕,所以你試圖將所有碎片拼湊在一起。我認為你實在是沒有其它辦法了,所以才只能向靈媒求助。”
“你瞧,”阿克塞爾笑著說。“我根本什麼都不用告訴你,不是嗎?”
行不通。所以我只好作罷,試著睡覺,我本來以為肯定睡不著,結果卻睡得挺香的。阿克塞爾羅德叫醒了我。“繫好安全帶,待會我們就要著陸了。”我朝窗外看了一眼,外頭一片漆黑,完全沒有燈光。
但很快地,我們就在完全沒有燈光引導的情況下順利著陸了。
“不是沒有引導燈嗎?”我忍不住說。
“這是一架非常先進的飛機,”阿克塞爾說。“它只是看起來像普通的李爾噴射機。”
著陸後,從飛機上下來的我們瞬間就置身在一片不是涼爽,而是應該用寒冷來形容的空氣中,而且還能聞到松樹的氣味。我們唯一擁有的照明就是雙胞胎手上的手電筒。
附近有一輛類似貨車的交通工具,上面塗有迷彩。我可以看見不遠處有一棟不大的建築物,但裡面似乎空無一人,至少沒有燈光。
然後我們上了車:
“穿上這件連身衣,”阿克塞爾說。
“它有保溫的效果,而且很輕便。你必須脫掉所有衣物,身上不能有任何金屬物品。
我知道你的牙齒裡有金屬填充物,那個就算了,連身衣的所有扣件,還有兜帽和手套都是用木頭與皮革製成的。”
我迅速穿好了連身衣,並發現衣服上的口袋剛好可以裝下雪茄。就在我換衣服的時候,雙胞胎已經發動了貨車,我們現在要前往下一個目的地。車程持續了大約兩個鐘頭。我們爬上幾座山峰,又通過一些陡峭的髮夾彎。大家都很安靜。
在漆黑的天空中,我可以看見高大的松樹,而在它們身後的是星羅棋布的美麗景象。我心想,我們一定是在遙遠的北方。貨車的引擎聲不知道從什麼時候就沒有了。可是貨車仍然在繼續行駛。我至今仍然想不通一輛貨車是如何在不發動引擎的情況下移動的。
最終,貨車停在了幾棵松樹的前面。
我們下車了。
“現在我們必須步行大約四十分鐘,”阿克塞爾低聲說道。
“務必要盡可能保持安靜。跟著我們走,不要發出聲音,也不要說話!還有不要抽雪茄!”
我們在幾乎伸手不見五指的環境中走著,但我們走得很趕。有時候,其中一位雙胞胎會扶著我,例如在跨過一條小溪或繞過看不見的岩石的時候。
他們似乎戴著某種護目鏡,我猜應該是夜視儀,真不明白為什麼他們不也給我一副。我們爬過幾座山脊,然後又向下走進了一片松樹繁茂的大平原。我們爬進了一個類似河溝的地方,接著又繼續走了幾英里,最後在大岩石後面厚厚的松針葉上坐了下來。
阿克塞爾悄悄地說:
“我們到了。我們的前面是一座小湖。等到黎明升起時,你會看見它就在松樹林的後面。我們現在要等待,但願我們命夠大吧。不要說話,不要發出任何聲音。”
“命夠大?”
那到底是什麼意思?
近距離接觸
除了東邊有黎明即將升起時的深藍綠色微光之外,我什麼也看不見。
我低聲對阿克塞爾羅德說:
“現在該做什麼?”
“安靜看著就好,我們待會再跟你解釋,”他回答說:“但從現在開始一定要保持安靜。除非我叫你,否則不要輕舉妄動。那些東西會偵測所有的熱源、噪音和動靜。”
我只能乖乖照做。
我們四個人像岩石一樣一動不動地坐在那裡。忽然,雙胞胎比了一個手勢。
“開始了,”阿克塞爾羅德用微弱的聲音說。“拜託,拜託,千萬不要發出聲音,除非我們叫你,否則不要移動。”
我努力轉動眼球,想弄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可是除了湖邊的方向似乎出現了一團灰色的霧氣之外,我根本看不出有什麼異狀。我以為那只是晨霧。這場霧持續了大約五分鐘,這時我突然“開始”看見了東西。
就在轉眼間,灰色的霧先是變成閃閃發亮的霓虹藍,接著又變成可怕的紫色。這時,阿克塞爾和其中一個雙胞胎用力地伸手按住我的肩膀,他們這麼做真是再正確不過了。這團“雲霧”正在從四面八方瘋狂射出紫色、紅色、黃色的閃電,要不是有人按住我,我肯定會當場嚇得跳起來。
然後,那東西出現了。起初它的輪廓還有點透明,但就在下一秒,就像淡入效果(fading-up,電影術語)一樣,它突然就出現在了那裡!現在我可以清楚看見它在湖面上的倒影。
而且它還在變得越來越大!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該預期會看見什麼,但非要說的話,也應該是像飛碟一樣的東西。可是出現在這裡的卻不是飛碟,寶貝。因為這東西是三角形的,而且它的頂角有點像是被翻開來過,所以從整體上看起來其實更接近於菱形。
就在我驚訝的時候,我們聽到一陣“風”吹過來,像是一種有形的磁場從我們身邊掠過,四週的松樹全都在沙沙作響,一些松果和樹枝還砸到了我們身上。按著我肩膀的兩隻手變得更用力了,這是在警告我千萬不要出於反射反應而移動。
與此同時,這個“東西”射出了具有紅寶石光澤的光束,令人不敢相信的是,它居然又變得更大了——且仍然在那片湖面上一動不動。
這時其中一位雙胞胎突然刻意壓低音量開口了,儘管他說出的話對我來說就像是晴天霹靂:
“該死!他們正在攻擊這個地方!他們遲早會發現我們!”
我根本沒有時間思考他的話。因為,幾棵松樹已經被那些紅色光束炸毀了!它們正在夷平一切!這個“東西”現在已經變大到了至少有九十英呎寬。這一切是在完全無聲的情況下發生的,甚至連電力流動的“劈啪”聲都沒有。
不過,現在可以聽見周圍樹木的爆炸聲,而且我還聽到了低頻脈衝的聲音。
“他們正在轟炸森林裡的鹿、豪豬或別的什麼東西,”阿克塞爾用平靜卻難掩緊張的語氣低聲說。“那光束能夠感應生物的體溫,它們肯定會發現我們。”
就在這時,我的肩膀被兩隻手緊緊抓住,將我直接拖到一旁,然後幾乎是用扔的將我丟進一條溝壑裡。我們剛才躲藏的地方發出了一聲響亮的“砰”,四週松樹的巨大樹枝開始像瀑布一樣傾瀉在我們身上。
這是我最後一次看見那個三角形物體,但就在這個時候,我看到湖水居然在向上流動——宛如一條逆流的瀑布,它們似乎正在被吸入那台“機器”裡面!


我的屁股重重地摔在地上,但我的腳還在被拖著,雙胞胎將我拉了起來,兩人一左一右抓著我跑了一小段路,接著猛然把我像一袋玉米一樣扔到了一座岩洞的下面。阿克塞爾幾乎是撲倒在我身上,我們四個人擠在一起,就像火柴盒裡的老鼠。
阿克塞爾和雙胞胎都吃力地呼吸著。
我幾乎無法呼吸,過了一陣子才意識到有石頭或樹枝劃破連身衣刺進了我的腿,傷口還在流血。
不過,我根本不需要指示,就知道現在要盡可能保持安靜。
我被一種完全無法用言語來形容的恐懼給嚇壞了。但同時我卻又感到莫名地激動。現在我真的親眼看到了!
我記得我們在那裡待了一段時間,可能有五分鐘也可能有五小時。就在這個時間近乎凍結的空間中,我聽到其中一位雙胞胎說“現在安全了”——這絕對是我這輩子聽過最可笑的一句話。如果說有什麼是清楚的話,那就是我什麼都搞不清楚。阿克塞爾問我有沒有受傷。
雙胞胎站了起來,冷靜地觀察週遭的情況。直到這時,我才注意到陽光已經出來了,松樹重新恢復了深綠色,鳥兒也正在啁啾啁啾。
我搖搖晃晃地站起來——然後吐了至少三次。
阿克塞爾連忙檢查我腿上的傷口(不是很嚴重,但出了很多血),我開始說著一些陰陽怪氣的話:
“是呀,是呀,”我哼了一聲:“不能把今天的事情說出去對吧,哼!”
“不,”阿克塞爾回答說。“我沒打算這麼說,總之那東西已經走了,一切都沒事了。”
我一臉不可置否地看著他,又隨便地說了一句:“那麼我可以抽支雪茄吧?”我從連身衣的口袋中拿出一包雪茄。雪茄都在剛剛被摔斷了,我只好坐在一塊岩石上,把其中一支雪茄接回去,然後開始吞雲吐霧。其中一位雙胞胎現在只能一瘸一拐地走路。
另一位在用一根小枝條不慌不忙地清理自己的指甲。至於我!一股難以遏止的憤怒湧上了我全身,我的雙手在止不住地顫抖。我既有的現實認知已經徹底被顛覆了。夢幻之城已經一去不復返。
最後,阿克塞爾說溪裡的水很好喝,其中一位雙胞胎搖了搖頭,似乎是在說我們該走了,我們就像剛結束了一趟遠足探險。
“那麼,”阿克塞爾邊走邊問道。“你有感應到什麼嗎?”
我立刻大笑起來:“你瘋了,阿克塞爾!我必須在非常冷靜、自在、鎮定且情緒穩定的狀態下才能感應任何東西。但你可以打賭你確實碰到了一個大麻煩,難道不是嗎!”
然後,我忽然有了一個不完全是來自理智、令人不安的想法:
“我覺得它是某種‘無人機’——沒有人在駕駛,是被遠端操控的——是這樣嗎?”
阿克塞爾皺起眉頭,盯著我們正在走的斜坡。
“它來到這裡做什麼?”他試探性地問。

“好吧,老天!當然是因為它口渴了!它顯然是為了打水而來,可能遠方某個地方的傢伙需要水...我想他們只是來打水的。
你甚至不需要心靈能力就能看出這一點!沒錯!就是這樣,這麼做是為了對他們在地球上的‘船艦’進行補給!就跟我們開車去購物,購買我們需要的東西一樣。”
我們一路安靜地走著,直到我們找到吉普車,再次開著它在崎嶇不平的路上行駛,車裡還有完好的雪茄和三明治。
“你知道,阿克塞爾,”我說:“如果他們真的是有意要攻擊‘鹿和豪豬’的話,我曾經讀過一些報導說UFO會把人燒死,這是真的嗎?”
我不指望得到答案,我知道我的問題不會被回答,我只是在自言自語。
“我想是吧。我想我們本來也會被炸死,不是嗎?你們好像已經習慣了,你們時不時就會碰上這種事嗎?”
當我們最終抵達機場時,我以為它是一座秘密機場,但我發現這裡擠滿了人:一架美國−阿拉斯加郵政航空飛機、三個穿著格子外套,頭戴牛仔帽的白人男子正懶洋洋地小茅屋旁邊的木凳上、一輛警用皮卡,車裡有兩個大腹便便的“警長”、十個我想應該是愛斯基摩人的女人。看來這裡肯定不是美國本土。
在距離飛機不遠處有個地方在販售所謂的夢幻之城特色菜餚:一輛架著橘藍色雨傘的熱狗車。
熱狗車是自助式的,其中一位雙胞胎走過去為了自己做了一份熱騰騰的熱狗。
“要來一份嗎?”阿克塞爾問。我確實餓了,實際上我要了三份,熱狗上淋滿了番茄醬與芥末。
“他們知道你是什麼人嗎?”我一邊問道,一邊向周圍的人們點頭致意。這次我可總算得到回答了!
“嗯,”阿克塞爾回答說:“他們以為我們是富有的環保主義者和賞鳥人士,來到這裡分析酸雨對環境的危害。”
“真是胡說八道,”我忍不住笑了。“他們肯定知道那裡發生了什麼。我想你們就是因為這些流言蜚語才注意到那輛地球購物特快車的。”
雙胞胎已經發動了飛機。當我們起飛時,我看見三個愛斯基摩人婦女推著熱狗車走向了小茅屋。大約十分鐘後,我們就越過了一座美麗的山巒,接著又是一座山,差不多過了四十分鐘後,我們已經離開海岸線,飛越了大海。
“我猜那裡是阿拉斯加,我剛剛看到了一架郵政航空飛機,”我並沒有期待被回答,只是在喃喃自語好解悶。
“你對那個物體憑空出現有什麼想法?”阿克塞爾問道。
我看著他,不禁噗哧笑了出來。他一定是在開玩笑!他居然說“物體”,老天。
“嗯,它一定是有某種‘空間轉換器’,但說真的阿克塞爾,我不知道。但我現在可以理解為什麼有些人即使在親眼目睹後卻還是不敢相信——以及為什麼沒有親眼目睹的人更是不可能相信它。”
阿克塞爾一言不發,只是一直盯著窗外。我繼續說:
“我記得,那東西並沒有‘傳送’它自己。它就是突然從它出現的地方冒出來的。
那東西是金字塔形的,而不是碟子形。我們總是在談論飛碟,我們以為這些東西應該是在天空中飛來飛去,而不會想到它們會直接憑空冒出來。”
阿克塞爾羅德打量著我,但我發現他正在不停冒汗。
“你是生病了還是怎麼了?”我問。
“噢,我想我在我們摔倒時斷了一根肋骨。沒事,這不要緊。你還有什麼見解嗎?”
“我們在研究遙視的時候發現,每當遙視者‘看見’他們不理解的東西時,他們就會自動以最符合他們認知的方式來對其進行詮釋。
舉例來說,如果有人從未看過原子反應爐,他們可能會說它是一個茶壺,因為兩者都是熱的且可以‘煮沸’。
我們將這個現象稱之為‘分析覆蓋’,意思是用認知中的心理圖像來描述未知、無法理解或不熟悉的事物。
遙視者在觀察原子反應爐時,就很有可能會用‘茶壺’或‘熔爐’來覆蓋眼前的印象,因為這些是最接近他們透過心靈能力感知到的東西的記憶圖像。
只要你先讓遙視者看過了原子反應爐及其周邊環境的照片,那麼下次當他們看到它時,就更有可能正確描述它,而不會把它說成是茶壺。
但總之,這就是人們一直以來所做的事情。每當碰到自己無法理解的事物,他們就會傾向於用符合既有認知的方式去詮釋它,結果就是他們的詮釋實際上已經與真實的對象差了十萬八千里遠。
換句話說,他們是在通過我所謂的‘現實跳躍器’來理解未知的事物,並設法想出一些符合自己現實認知的東西——但這就有可能會與他們的實際經歷產生脫節。
人們總是喜歡用符合他們認知的東西來理解未知。
最明顯的例子是,如果有五個人同時看到一些超出他們認知的事物,其中一個人可能會說他完全不知道這些東西是什麼。
但其他四個人卻可能會對此提出四種不同的詮釋。
比方說,你稱那個東西為‘物體’,但我看到的卻是一個能夠具現化、憑空冒出來的東西,我想它在我們從岩石和泥土上摔下去後就消失了。
它也許是在某一刻變成了有物質的形體,但在我看來這只是一種‘表象’,而不代表它真的就是一個物體。
這是一種會變化的表象。
問題的關鍵在於,這對我們來說已經是一個如何詮釋現實的問題。
那東西超出了我的現實認知,所以如果你非要問我感應到了什麼,我可能就會用自己經過分析覆蓋後的結論來回答你。
例如,我剛剛說了‘空間轉換器’,但其實我根本不知道那東西到底是什麼,或是用什麼製造的。”
阿克塞爾在座位上扭動身子,試著讓自己舒服一點。
“也就是說,”他說:“你只能根據自己過往的經驗來理解現在的經歷,是嗎?”
“差不多是這樣。當然,這樣的情況在遙視、透視,有時甚至是心靈感應實驗中比比皆是。
但這在心靈研究中早已廣為人知。唯一的問題是,世人尚未認真理解這一點。
如果人們能夠理解它,那麼就必須承認,大多數人所相信的事物其實只不過是他們的現實跳躍器對自己不理解的東西的‘詮釋’罷了。
我們只是在透過"自以為是的認知"來詮釋我們不理解的東西。
我當然不理解我在湖邊看到的是什麼,但光是承認這一點就是需要勇氣的。”
“好吧,好吧,”阿克塞爾苦笑道。“我明白了——所以現在有兩個問題。它們是什麼,以及我們的認知是怎麼詮釋它們的。”
“沒錯,”我咯咯笑著。“一位遙視新手可以研究一本介紹各種類型的原子反應爐的書。那麼你有沒有一本上面介紹了各種類型UFO的書呢?
如果你早點告訴我它是一個會具現化的、憑空出現的三角形物體,我或許就不會那麼吃驚,然後就可以更仔細地觀察它,而不會被我的現實跳躍器干擾。”
阿克塞爾笑了笑,隨即改變了話題。
“嗯,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讓你曝露在這個,噢,表象面前可能會很危險,我們實在沒有辦法這麼做。”
我笑了,同時也放鬆下來。“老天,阿克塞爾,我已經準備好再次出發了!誰會甘心就這樣放棄。”
“好吧,不過這大概無法如你所願了。我本來不該告訴你,但出於戰略安全考量,我們的任務很快就會解散,改由其他人接手。”
“我想其他人應該不會對與靈媒打交道有興趣,”我笑著說。
“確實如此。下星期一你得要去接受一次全面的體檢,表面上只是為了確保你們研究計畫中的相關人員的健康狀況。
我們只是想要確定你的身體沒有出現任何問題。屆時進行體檢的將是普通的醫生,他們不知道我們的存在。你能編出一個合理的藉口來解釋腿上的傷口嗎?”
“下星期我沒有時間。我們要去卡塔利娜島,用潛水艇進行水下遙視實驗。我沒事,我腿上的傷口很小,我不用向任何人解釋。”
我最後一次見到阿克塞爾羅德先生是在聖荷西機場,我與他的相遇以及他的超機密任務的故事就到這裡告一段落了。我無法證明這個故事中的任何一個字——因為這就是事實。
何況我本來根本沒有打算將它寫下來。
下圖:加州男子在後院創作外星岩石藝術「希望邀請外星人」來家裡

科頓飛船》地球過渡在加速 物極必反 臨界在即 逆轉會自動發生
美國"星門計畫"執行官坦承軍方通靈培訓內容: 遙視、出體、中陰、露食、雙腦同步
限會員,要發表迴響,請先登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