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征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是台中豐原會計稅務記帳會計師事務所最佳稅務後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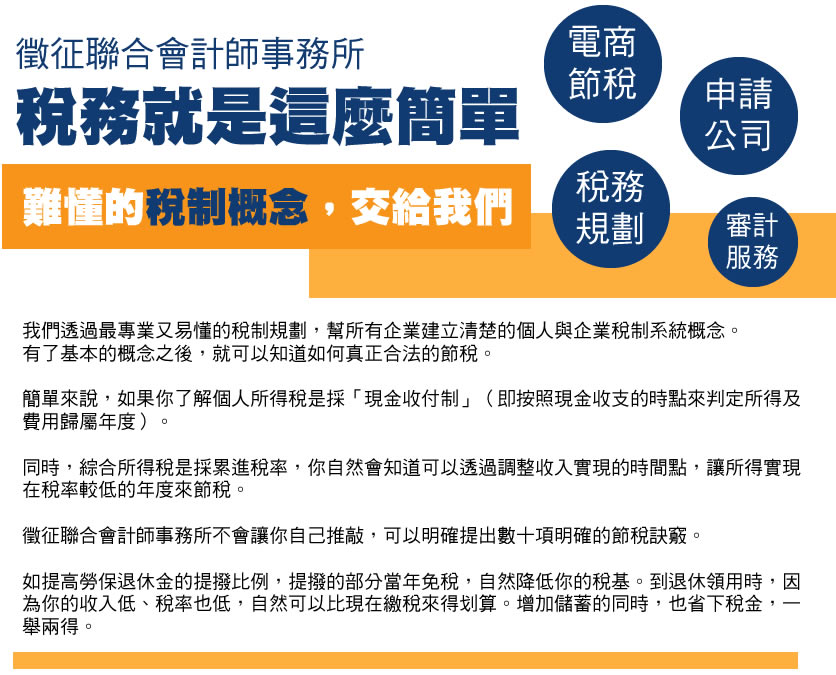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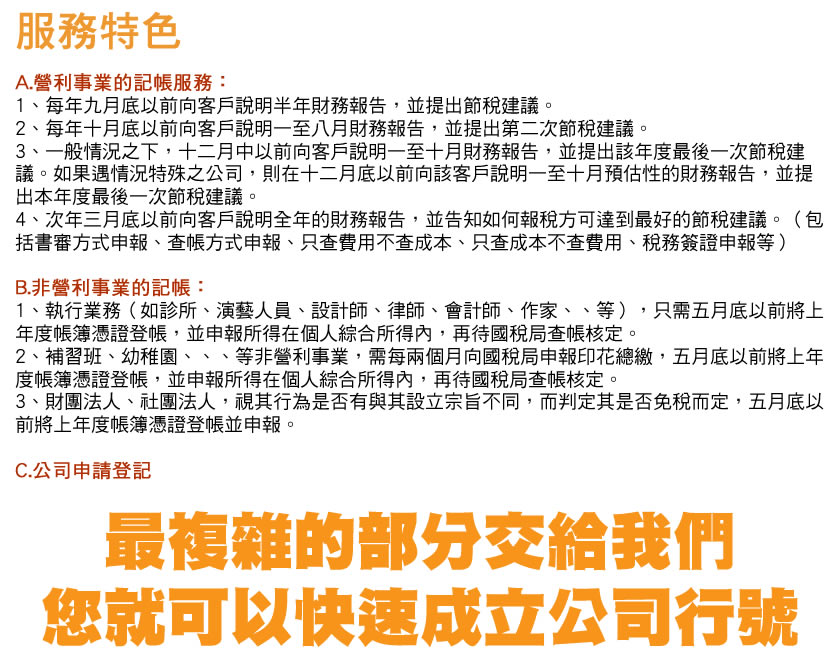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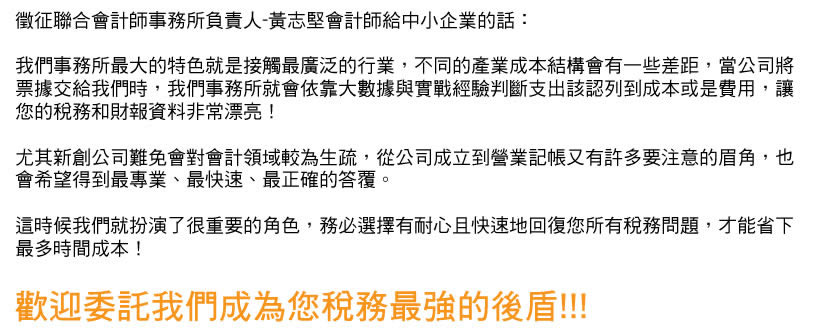
台中會計師執業, 台中南屯創業家移民會計服務推薦, 台中南屯首次公開募股(IPO)
12件能讓你開心的事 1.每天拍幾張照片 心理學家建議,每天用相機拍下一些身邊的人和事,如窗外的樹木、路邊的小花、鄰居家的孩子和朋友的婚禮。將這些隨時可能被遺忘的片段記錄起來,當你不定期整理照片時,你會覺得所有的細節都是美好回憶,沒什么可抱怨的,于是人會很容易變得快樂起來。 2.看悲傷的電影 看一部令人傷感的電影,如《當男人愛上女人》,情難自禁時,不妨盡情地放聲哭出來,然后安慰自己說,還好這只是電影情節,并不是真實的生活,心情便會大有改變。這是一種反向思考的方法,常運用在心理學中,協助人們換角度思考問題。 3.在周末的清晨做白日夢 不少能干的主婦,會從星期六一大早起床開始,馬不停蹄地做家務活,如收拾屋子,清洗馬桶等。這樣的習慣常常會讓人在星期六晚上疲憊不堪,并影響到星期日的睡眠。不妨暫時拋開那些瑣碎的家務活,在周末的清晨做一個美美的白日夢。不要自責,而應鼓勵自己說:“我工作那么辛苦,揮霍一下自己的休息時間,無可厚非。” 4.定期寫郵件 和相識多年的朋友定期以郵件的形式保持聯系。有寫日記習慣的人,只是在紙上隨手涂鴉或草草地寫上幾句,便能反映出潛意識中的心理狀態,寫郵件也是如此。而定期與朋友通郵件,聊聊最近的生活,不僅能協助你放下心里的事情,還能協助你拾起被淡漠的友情。 5.在水邊散步 有研究指出,因為在嬰兒時期便置身于羊水,因此人與生俱來就是親水的。在水邊散步,能有效地協助人放松身心,即便煩惱再多,在有綠樹有流水的環境中,你也能暫時拋開一切,為自己“偷”得頃刻悠閑。 6.偶爾吃一頓大餐 吃一頓大餐的美妙在于,不僅能享遭到美味可口的食物,還能讓你感覺自己遭到了特別禮遇。人在遭到與別人不同的照顧時,心情會不知不覺地變好。我們在小時侯都可能有類似這樣的經歷:當父母特意為你買了一只與其他孩子不一樣的、漂亮的碗,你會高高興興地吃下比平時多的食物,即便不愛吃的食物也變得“可愛”起來。 7.每星期做1次美甲 當看見自己又長又臟又難看的指甲時,沒人會有好心情。每星期做1次美甲,不僅能讓你的指甲看起來愈加整潔、漂亮,還能讓你有“一切盡在掌握”的滿足感,人也由此變得豁然開朗。 8.參加集體活動 雖然獨處也是調節心情的方法之一,但是不要吝嗇自己的休息時間,分出一部分給集體活動。登山、郊游、野餐、party、歌友會……鼓勵自己積極參加集體活動,你會在共同的玩樂中找到讓自己堅強、平和的力量。 9.定期游泳 游泳是最消耗體力的運動之一,但這種讓人精疲力竭的活動,能讓人擺脫煩惱,身心舒展。選擇一個人去游泳也不錯,被水包圍其中,再糟糕的心情也能被軟化。 10.一邊開車,一邊大聲歌唱 心情不好時,打開車上的收音機,調到較大音量,跟著里面播放的旋律大聲歌唱,完全不必在意別人投來異樣的眼神。也許此時的你在別人眼中有點傻乎乎的,但這確實是一種讓人快速釋放心情的好方法 11.一邊喝咖啡,一邊讀小說 挑一家出名的咖啡館,帶上一本近期最讓你感興趣的小說,選一個靠窗邊的位置,坐下來點一杯咖啡,邊喝邊讀……是的,這是電影里常常出現的“小資”鏡頭。(勵志一生 https://www.lz13.cn)但那又有什么關系,讓自己體驗一下電影中才有的浪漫鏡頭,你也會遭到氣氛的影響,得到真實的放松和享受。 12.給朋友寄卡片 挑選10——15張別致的卡片,放在包中隨身照顧,在等公共汽車、排隊結帳、等人時,隨手拿出一張寫上只字片語,如 “想念你”、“愿你的心情和今天的天氣一樣燦爛”、“一定要幸福喲”、“想起我們上大學的日子”等等,然后郵寄給你的朋友。當所有的卡片都被逐個寫完并郵寄出去后,一想到朋友們收到卡片時驚喜的表情,你會露出發自內心的誘人笑容。【閱讀了本文的用戶還閱讀下列精彩文章,你也看看吧!】[高三學生每天必做的“八件事”] [中國人一生最喜愛的三件事]分頁:123
許地山:解放者 大碗居前的露店每坐滿了車夫和小販。尤其在早晚和晌午三個時辰,連窗戶外也沒有一個空座。紹慈也不知到那里去。他注意個個往來的人,可是人都不注意他。在窗戶底下,他喝著豆粥抽著煙,眼睛不住地看著往來的行人,好象在偵察什么案情一樣。 他原是武清的警察,因為辦事認真,局長把他薦到這城來試當一名便衣警察。看他清秀的面龐,合度的身材,和聽他溫雅的言辭,就知道他過去的身世。有人說他是世家子弟,因為某種事故,流落在北方,不得已才去當警察。站崗的生活,他已度過八九年,在這期間,把他本來的面目改變了不少。便衣警察是他的新任務,對于應做的偵察事情自然都要學習。 大碗居里頭靠近窗戶的座,與外頭紹慈所占的只隔一片紙窗。那里對坐著男女二人,一面吃,一面談,幾乎忘記了他們在什么地方。因為街道上沒有什么新鮮的事情,紹慈就轉過來偷聽窗戶里頭的談話。他聽見那男子說:“世雄簡直沒當你是人。你原先為什么跟他在一起?”那女子說:“說來話長。我們是舊式婚姻,你不知道嗎?”他說:“我一向不知道你們的事,只聽世雄說他見過你一件男子所送的東西,知道你曾有過愛人,但你始終沒說出是誰。” 這談話引起了紹慈的注意。從那二位的聲音聽來,他覺得象是在什么地方曾經認識的人。他從紙上的小玻璃往里偷看一下。原來那男子是離武清不遠一個小鎮的大悲院的住持契默和尚。那女子卻是縣立小學的教員。契默穿的是平常的藍布長袍,頭上沒戴什么,雖露光頭,卻也顯不出是個出家人的模樣。大概他一進城便當還俗吧。那女教員頭上梳著琶琶頭,灰布袍子,雖不入時,倒還優雅。紹慈在縣城當差的時候常見著她,知道她的名字叫陳邦秀。她也常見紹慈在街上站崗,但沒有打過交涉,也不知道她的名字。 紹慈含著煙卷,聽他們說下去。只聽邦秀接著說:“不錯,我是藏著些男子所給的東西,不過他不是我的愛人。”她說時,微嘆了一下。契默還往下問。她說:“那人已經不在了。他是我小時候的朋友,不,寧可說是我的恩人。今天已經講開,我索性就把原委告訴你。” “我原是一個孤女,原籍廣東,哪一縣可記不清了。在我七歲那年,被我的伯父賣給一個人家。女主人是個鴉片鬼,她睡的時候要我捶腿搔背,醒時又要我打煙泡,做點心,一不如意便是一頓毒打。那樣的生活過了三四年。我在那家,既不曉得尋死,也不能夠求生,真是痛苦極了。有一天,她又把我虐待到不堪的地步,幸虧前院同居有位方少爺,乘著她鴉片吸足在床上沉睡的時候,把我帶到他老師陳老師那里。我們一直就到輪船上,因為那時陳老師正要上京當小京官,陳老師本來知道我的來歷,任從方少爺怎樣請求,他總覺得不妥當,不敢應許我跟著他走。幸而船上敲了鑼,送客的人都紛紛下船,方少爺忙把一個小包遞給我,雜在人叢中下了船。陳老師不得已才把我留在船上,說到香港再打電報教人來帶我回去。一到香港就接到方家來電請陳老師收留我。” “陳老師、陳師母和我三個人到北京不久,就接到方老爺來信說加倍賠了人家的錢,還把我的身契寄了來。我感激到萬分,很盡心地伺候他們。他們倆年紀很大,還沒子女,覺得我很不錯,就把我的身契燒掉,認我做女兒。我進了幾年學堂,在家又有人教導,所以學業進步得很快。可惜我高小還沒畢業,武昌就起了革命。我們全家匆匆出京,回到廣東,知道那位方老爺在高州當知縣,因為辦事公正,當地的劣紳地痞很恨惡他。在革命風潮膨脹時,他們便樹起反正旗,借著撲殺滿州奴的名義,把方老爺當牛待遇,用繩穿著他的鼻子,身上掛著貪官污吏的罪狀,領著一家大小,游遍滿城的街市,然后把他們害死。” 紹慈聽到這里,眼眶一紅,不覺淚珠亂滴。他一向是很心慈,每聽見或看見可憐的事情,常要掉淚。他盡力約束他的情感,還鎮定地聽下去。 契默象沒理會那慘事,還接下去問:“那方少爺也被害了么?” “他多半是死了。等到革命風潮稍微平定,我義父和我便去訪尋方家人的遺體,但都已被毀滅掉,只得折回省城。方少爺原先給我那包東西是幾件他穿過的衣服,預備給我在道上穿的。還有一個小繡花筆袋,帶著兩枝鉛筆。因為我小時看見鉛筆每覺得很新鮮,所以他送給我玩。衣服我已穿破了,惟獨那筆袋和鉛筆還留著,那就是世雄所疑惑的‘愛人贈品’。” “我們住在廣州,義父沒事情做,義母在民國三年去世了。我那時在師范學校念書。義父因為我已近成年,他自己也漸次老弱,急要給我擇婿。我當時雖不愿意,只為厚恩在身,不便說出一個‘不’字。由于輾轉的介紹,世雄便成為我的未婚夫。那時他在陸軍學校,還沒有現在這樣荒唐,故此也沒覺得他的可惡。在師范學校的末一年,我義父也去世了。那時我感到人海茫茫,舉目無親,所以在畢業禮行過以后,隨著便行婚禮。” “你們在初時一定過得很美滿了。” “不過很短很短的時期,以后就越來越不成了。我對于他,他對于我,都是半斤八兩,一樣地互相敷衍。” “那還成嗎?天天挨著這樣虛偽的生活。” “他在軍隊里,蠻性越發發展,有三言兩語不對勁,甚至動手動腳,打踢辱罵,無所不至。若不是因為還有更重大的事業沒辦完的原故,好幾次我真想要了結了我自己的生命。幸而他常在軍隊里,回家的時候不多。但他一回家,我便知道又是打敗仗逃回來了。他一向沒打勝仗:打惠州,做了逃兵;打韶州,做了逃兵;打南雄,又做了逃兵。他是臨財無不得,臨功無不居,臨陣無不逃的武人。后來,人都知道他的伎倆,軍官當不了,在家閑住著好些時候。那時我在黨里已有些地位,他央求我介紹他,又很誠懇地要求同志們派他來做現在的事情。” “看來他是一個投機家,對于現在的事業也未見得能忠實地做下去。” “可不是嗎?只怪同志們都受他欺騙,把這么重要的一個機關交在他手里。我越來越覺得他靠不住,時常曉以大義。所以大吵大鬧的戲劇,一個月得演好幾回。” 那和尚沉吟了一會,才說:“我這才明白。可是你們倆不和,對于我們事業的前途,難免不會發生障礙。” 她說:“請你放心,他那一方面,我不敢保。我呢?私情是私情。公事是公事,決不象他那么不負責任。” 紹慈聽到這里,好象感觸了什么,不知不覺間就站了起來。他本坐在長板凳的一頭,那一頭是另一個人坐著。站起來的時候,他忘記告訴那人預防著,猛然把那人摔倒在地上。他手拿著的茶杯也摔碎了,滿頭面都澆濕了。紹慈忙把那人扶起,賠了過失,張羅了一刻工夫。等到事情辦清以后,在大碗居里頭談話的那兩人,已不知去向。 他雖然很著急,卻也無可奈何,仍舊坐下,從口袋里取出那本用了二十多年的小冊子,寫了好些字在上頭。他那本小冊子實在不能叫做日記,只能叫做大事記。因為他有時距離好幾個月,也不寫一個字在上頭,有時一寫就是好幾頁。 在繁劇的公務中,紹慈又度過四五個星期的生活。他總沒忘掉那天在大碗居所聽見的事情,立定主意要去偵察一下。 那天一清早他便提著一個小包袱,向著沙鍋門那條路走。他走到三里河,正遇著一群羊堵住去路,不由得站在一邊等著。羊群過去了一會,來了一個人,抱著一只小羊羔,一面跑,一面罵前頭趕羊的伙計走得太快。紹慈想著那小羊羔必定是在道上新產生下來的。它的弱小可憐的聲音打動他的惻隱之心,便上前問那人賣不賣,那人因為他給的價很高,也就賣給他,但告訴他沒哺過乳的小東西是養不活的,最好是宰來吃。紹慈說他有主意,抱著小羊羔,雇著一輛洋車拉他到大街上,買了一個奶瓶,一個熱水壺,和一匣代乳粉。他在車上,心里回憶幼年時代與所認識的那個女孩子玩著一對小兔,他曾說過小羊更好玩。假如現在能夠見著她,一同和小羊羔玩,那就快活極了。他很開心,走過好幾條街,小羊羔不斷地在懷里叫。經過一家飯館,他進去找一個座坐下,要了一壺開水,把乳粉和好,慢慢地喂它。他自己也覺得有一點餓,便要了幾張餅。他正在等著,隨手取了一張前幾天的報紙來看。在一個不重要的篇幅上,登載著女教員陳邦秀被捕,同黨的領袖在逃的新聞,匆忙地吃了東西,他便出城去了。 他到城外,雇了一匹牲口,把包袱背在背上,兩手抱著小羊羔,急急地走,在驢鳴犬吠中經過許多村落。他心里一會驚疑陳邦秀所犯的案,那在逃的領袖到底是誰;一會又想起早間在城門洞所見那群羊被一只老羊領導著到一條死路去:一會又回憶他的幼年生活。他聽人說過沙漬里的狼群出來獵食的時候,常有一只體力超群、經驗豐富的老狼領導著。為求食的原故,經驗少和體力弱的群狼自然得跟著它。可見在生活中,都是依賴的份子,隨著一兩個領袖在那里瞎跑,幸則生,不幸則死,生死多是不自立不自知的。狼的領袖是帶著群狼去搶掠;羊的領袖是領著群羊去送死。大概現在世間的領袖,總不能出乎這兩種以外吧! 不知不覺又到一條村外,紹慈下驢,進入柿子園里。村道上那匹白騾昂著頭,好象望著那在長空變幻的薄云,籬邊那只黃狗閉著眼睛,好象品味著那在蔓草中哀鳴的小蟲,樹上的柿子映著晚霞,顯得格外燦爛。紹慈的叫驢自在地向那草原上去找它的糧食。他自己卻是一手抱著小羊羔,一手拿著乳瓶,在樹下坐著慢慢地喂。等到人畜的困乏都減輕了,他再騎上牲口離開那地方,頃刻間又走了十幾里路。那時夕陽還披在山頭,地上的人影卻長得比無常鬼更為可怕。 走到離縣城還有幾十里的那個小鎮,天已黑了,紹慈于是到他每常歇腳的大悲院去。大悲院原是鎮外一所私廟,不過好些年沒有和尚。到二三年前才有一位外來的和尚契默來做主持,那和尚的來歷很不清楚,戒牒上寫的是泉州開元寺,但他很不象是到過那城的人,紹慈原先不知道其中的情形,到早晨看見陳邦秀被捕的新聞,才懷疑契默也是個黨人。契默認識很多官廳的人員,紹慈也是其中之一,不過比較別人往來得親密一點。這大概是因為紹慈的知識很好,契默與他談得很相投,很希望引他為同志。 紹慈一進禪房,契默便迎出來,說:“紹先生,久違了。走路來的嗎?聽說您高升了。”他回答說:“我離開縣城已經半年了。現住在北京,沒有什么事。”他把小羊羔放在地下,對契默兌:“這是早晨在道上買的。我不忍見它生下不久便做了人家的盤里的肴饌,想養活它。”契默說:“您真心慈,您來當和尚倒很合式。”紹慈見羊羔在地下盡旨咩咩地叫,話也談得不暢快,不得已又把它抱起來,放在懷里。它也象嬰兒一樣,有人抱就不響了。 紹慈問:“這幾天有什么新聞沒有?” 契默很鎮定地回答說:“沒有什么。” “沒有什么!我早晨見一張舊報紙說什么黨員運動起事,因泄漏了機關,被逮了好些人,其中還有一位陳邦秀教習,有這事嗎?” “哦,您問的是政治。不錯,我也聽說來,聽說陳教習還押到縣衙門里,其余的人都已槍斃了。”他接著問,“大概您也是為這事來的吧?” 紹慈說:“不,我不是為公事,只是回來取些東西,在道上才知道這件事情。陳教習是個好人,我也認得她。” 契默聽見他說認識邦秀,便想利用他到縣里去營救一下,可是不便說明,只說:“那陳教習的確是個好人。” 紹慈故意問:“師父,您怎樣認得她呢?” “出家人哪一流的人不認得?小僧向她曾化過幾回緣,她很虔心,頭一次就題上二十元,以后進城去拜施主,小僧必要去見見她。” “聽說她丈夫很不好,您去,不會叫他把您攆出來么?” “她的先生不常在家,小僧也不到她家去,只到學校去。”他于是信口開河,說:“現在她犯了案,小僧知道一定是受別人的拖累。若是有人替她出來找找門路,也許可以出來。” “您想有什么法子?” “您明白,左不過是錢。” “沒錢呢?” “沒錢,勢力也成,面子也成,像您的面子就夠大的,要保,準可以把她保出來。” 紹慈沉吟了一會,便搖頭說:“我的面子不成,官廳拿人,一向有老例——只有錯拿,沒有錯放,保也是白保。” “您的心頂慈悲的,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一只小羊羔您都搭救,何況是一個人?” “有能救她的道兒,我自然得走。明天我一早進城去相機辦理吧。我今天走了一天,累得很,要早一點歇歇。”他說著,伸伸懶腰,打個哈欠,站立起來。 契默說:“西院已有人住著,就請在這廂房湊合一晚吧。” “隨便哪里都成,明兒一早見。”紹慈說著抱住小羊羔便到指定給他的房間去。他把臥具安排停當,又拿出那本小冊子記上幾行。 夜深了,下弦的月已升到天中,紹慈躺在床上,斷續的夢屢在枕邊繞著。從西院送出不清晰的對談聲音,更使他不能安然睡去。 西院的客人中有一個說:“原先議決的,是在這兩區先后舉行,世雄和那區的主任意見不對。他恐怕那邊先成功,于自己的地位有些妨礙,于是多方阻止他們。那邊也有許多人要當領袖,也怕他們的功勞被世雄埋沒了,于是相持了兩三個星期。前幾天,警察忽然把縣里的機關包圍起來,搜出許多文件,逮了許多人,事前世雄已經知道。他不敢去把那些機要的文件收藏起來,由著幾位同志在那里干。他們正在毀滅文件的時候,人就來逮了。世雄的住所,警察也偵查出來了。當警察拍門的時候,世雄還沒逃走。你知道他房后本有一條可以容得一個人爬進去的陰溝,一直通到護城河去。他不教邦秀進去,因為她不能爬,身體又寬大。若是她也爬進去,溝口沒有人掩蓋,更容易被人發覺。假使不用掩蓋,那溝不但兩個人不能并爬,并且只能進前,不能退后。假如邦秀在前,那么寬大的身子,到了半道若過不去,豈不要把兩個人都活埋在里頭?若她在后,萬一爬得慢些,終要被人發現。所以世雄說,不如教邦秀裝做不相干的女人,大大方方出去開門。但是很不幸,她一開門,警察便擁進去,把她綁起來,問她世雄在什么地方?她沒說出來。警察搜了一回,沒看出什么痕跡,便把她帶走。” “我很替世雄慚愧,堂堂的男子,大難臨頭還要一個弱女子替他,你知道他往哪里去嗎?”這是契默的聲音。 那人回答說:“不知道,大概不會走遠了,也許過幾天會逃到這里來。城里這空氣已經不那么緊張,所以他不致于再遇見什么危險,不過邦秀每晚被提到衙門去受秘密的審問,聽說十個手指頭都已夾壞了,只怕她受不了,一起供出來,那時,連你也免不了,你得預備著。” “我不怕,我信得過她決不會說出任何人,肉刑是她從小嘗慣的家常便飯。” 他們談到這里,忽然記起廂房里歇著一位警察,便止住了。契默走到紹慈窗下,叫“紹先生,紹先生”。紹慈想不回答,又怕他們懷疑,便低聲應了一下。契默說:“他們在西院談話把您吵醒了吧?” 他回答說:“不,當巡警的本來一叫便醒,天快亮了吧?”契默說:“早著呢,您請睡吧,等到時候,再請您起來。” 他聽見那幾個人的腳音向屋里去,不消說也是幸免的同志們,契默也自回到他的禪房去了,庭院的月光帶著一丫松影貼在紙窗上頭。紹慈在枕上,瞪著眼,耳鼓里的音響,與荒草中的蟲聲混在一起。 第二天一早,契默便來央求紹慈到縣里去,想法子把邦秀救出來。他掏出一疊鈔票遞給紹慈,說:“請您把這二百元帶著,到衙門里短不了使錢。這都是陳教習歷來的布施,現在我仍拿出來用回在她身上。” 紹慈知道那錢是要送他的意思,便鄭重地說:“我一輩子沒使人家的黑錢,也不愿意給人家黑錢使。為陳教習的事,萬一要錢,我也可以想法子,請您收回去吧。您不要疑惑我不幫忙,若是人家冤屈了她,就使丟了我的性命,我也要把她救出來。” 他整理了行裝,把小羊羔放在契默給他預備的一個筐子里,便出了廟門。走不到十里路,經過一個長潭,岸邊的蘆花已經半白了。他沿著岸邊的小道走到一棵柳樹底下歇歇,把小羊羔放下,拿出手中擦汗。在張望的時候,無意中看見岸邊的草叢里有一個人躺著。他進前一看,原來就是邦秀。他叫了一聲:“陳教習”。她沒答應。搖搖她,她才懶慵慵地睜開眼睛。她沒看出是誰,開口便說:“我餓得很,走不動了。”話還沒有說完,眼睛早又閉起來了。紹慈見她的頭發散披在地上,臉上一點血色也沒有。穿一件薄呢長袍,也是破爛不堪的,皮鞋上滿沾著泥土,手上的傷痕還沒結疤。那可憐的模樣,實在難以形容。 紹慈到樹下把水壺的塞子拔掉,和了一壺乳粉,端來灌在她口里。過了兩三刻鐘,她的精神漸次恢復回來。在注目看著紹慈以后,她反驚慌起來。她不知道紹慈已經不是縣里的警察,以為他是來捉拿她。心頭一急,站起來,躡秧雞一樣,飛快地鉆進葦叢里。紹慈見她這樣慌張,也急得在后面嚷著,“別怕,別怕。”她哪里肯出來,越鉆越進去,連影兒也看不見了。紹慈發愣一會,才追進去,口里嚷著“救人,救人!”這話在邦秀耳里,便是“揪人,揪人!”她當然越發要藏得密些。 一會兒葦叢里的喊聲也停住了。邦秀從那邊躲躲藏藏地躡出來。當頭來了一個人,問她“方才喊救人的是您嗎?”她見是一個過路人,也就不害怕了。她說:“我沒聽見,我在這里頭解手來的。請問這里離前頭鎮上還有多遠?”那人說:“不遠了,還有七里多地。”她問了方向,道一聲“勞駕”,便急急邁步。那人還在那周圍找尋,沿著岸邊又找回去。 邦秀到大悲院門前,正趕上沒人在那里,她怕廟里有別人,便裝做叫化婆,嚷著“化一個啵”,契默認得她的聲音,趕緊出來,說:“快進來,沒有人在里頭。”她隨著契默到西院一間小屋子里。契默說:“你得改裝,不然逃不了。”他于是拿剃刀來把她的頭發刮得光光的,為她穿上僧袍,儼然是一個出家人模樣。 契默問她出獄的因由,她說是與一群獄卒串通,在天快亮的時候,私自放她逃走。她隨著一幫趕集的人們急急出了城,向著大悲院這條路上一氣走了二十多里。好幾天挨餓受刑的人,自然當不起跋涉,到了一個潭邊,再也不能動彈了。她怕人認出來,就到葦子里躲著歇歇,沒想到一躺下,就昏睡過去。又說,在道上遇見縣里的警察來追,她認得其中一個是紹慈,于是拼命鉆進葦子里,經過很久才逃脫出來。契默于是把早晨托紹慈到縣營救她的話告訴了一番,又教她歇歇,他去給她預備飯。 好幾點鐘在平靜的空氣中過去了,廟門口忽然來了一個人,提著一個筐子,上面有大悲院的記號,問當家和尚說:“這筐子是你們這里的嗎?”契默認得那是早晨給紹慈盛小羊羔的筐子,知道出了事,便說:“是這里的,早晨是紹老總借去使的,你在哪里把它撿起(www.lz13.cn)來的呢?”那人說:“他淹死啦!這是在柳樹底下撿的。我們也不知是誰,有人認得字,說是這里的。你去看看吧,官免不了要驗,你總得去回話。”契默說:“我自然得去看看。”他進去給邦秀說了,教她好好藏著,便同那人走了。 過了四五點鐘的工夫,已是黃昏時候,契默才回來。西院里昨晚談話的人們都已走了,只剩下邦秀一個人在那里。契默一進來,對著她搖搖頭說:“可惜,可惜!”邦秀問:“怎么樣了?”他說:“你道紹慈那巡警是什么人?他就是你的小朋友方少爺!”邦秀“呀”了一聲,站立起來。 契默從口袋掏出一本濕氣還沒去掉的小冊子,對她說:“我先把情形說完,再念這里頭的話給你聽。他大概是怕你投水,所以向水邊走。他不提防在葦叢里臍著一個深水坑,全身掉在里頭翻不過身來,就淹死了。我到那里,人們已經把他的尸身撈起來,可還放在原地。葦子里沒有道,也沒有站的地方,所以沒有圍著看熱鬧的人,只有七八個人遠遠站著。我到尸體跟前,見這本日記露出來,取下來看了一兩頁。知道記的是你和他的事情,趁著沒有人看見,便放在口袋里,等了許久,官還沒來。一會來了一個人說,驗官今天不來了,于是大家才散開。我在道上一面走,一面翻著看。” 他翻出一頁,指給邦秀說:“你看,這段說他在革命時候怎樣逃命,和怎樣改的姓。”邦秀細細地看了一遍以后,他又翻過一頁來,說:“這段說他上北方來找你沒找著。在流落到無可奈何的時候,才去當警察。” 她拿著那本日記細看了一遍,哭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停了許久,才抽抽噎噎地對契默說:“這都是想不到的事。在縣城里,我幾乎天天見著他,只恨二年來沒有同他說過一句話,他從前給我的東西,這次也被沒收了。” 契默也很傷感,同情的淚不覺滴下來,他勉強地說:“看開一點吧!這本就是他最后留給你的東西了。不,他還有一只小羊羔呢!”他才想起那只可憐的小動物,也許還在長潭邊的樹下,但也有被人拿去剝皮的可能。 許地山作品_許地山散文集 許地山:海角的孤星 許地山:歸途分頁:123
林海音:虎坊橋 常常想起虎坊大街上的那個老乞丐,也常想總有一天把他寫進我的小說里。他很臟、很胖。臟,是當然的,可是胖子做了乞丐,卻是在他以前和以后,我都沒有見過的事;覺得和他的身份很不襯,所以才有了不可磨滅的印象吧!常在冬天的早上看見他,穿著空心大棉襖坐在我家的門前,曬著早晨的太陽在拿虱子。他的唾沫比我們多一樣用處,就是食指放在舌頭上添一舔,沾了唾沫然后再去沾身上的虱子,把虱子夾在兩個大拇指的指甲蓋幾上擠一下,“貼”的一聲,虱子被擠破了。然后再沾唾沫,再拿虱子。聽說虱子都長了尾巴了,好不惡心! 他的身旁放著一個沒有蓋子的砂鍋,盛著乞討來的殘羹冷飯。不,飯是放在另一個地方,他還有一個黑臟油亮的帆布口袋,干的東西像飯、饅頭、餃子皮什么的,都裝進口袋里。他抱著一砂鍋的剩湯水,仰起頭來連扒帶喝的,就全吃下了肚。我每看見他在吃東西,就往家里跑,我實在想嘔吐了。 對了,他還有一個口袋。那里面裝的是什么?是白花花的大洋錢!他拿好了虱子,吃飽了剩飯,抱著砂鍋要走了,一站起身來,破棉褲腰里系著的這個口袋,往下一墜,洋錢在里面打滾兒的聲音丁當響。我好奇怪,拉著宋媽的衣襟,指著那發響的口袋問: “宋奶,他還有好多洋錢,哪兒來的?” “哼,你以為是偷來的、搶來的嗎?人家自個兒攢的。” “自個兒攢的?你說過,要飯的人當初都是有錢的多,好吃懶做才把家當花光了,只好要飯吃。” “是呀!可是要了飯就知道學好了,知道攢錢啦!”宋媽擺出凡事皆在的樣子回答我。 “既然是學好,為什么他不肯洗臉洗澡,拿大洋錢去做套新棉襖穿哪?” 宋媽沒回答我,我還要問: “他也還是不肯做事呀?” “你沒聽說嗎?要了三年飯,給皇上都不當。” 他雖然不肯做皇上,我想起來了,他倒也在那出大殯的行列里打執事賺錢呢!爛棉祆上面套著白喪褂子,從喪家走到墓地,不知道有多少里路,他又胖又老,還舉著旗呀傘呀的。而且,最要緊的是他腰里還掛著一袋于洋錢哪!這一身披掛,走那么遠的路,是多么的吃力呢!這就是他蕩光了家產又從頭學好的緣故嗎?我不懂,便要發問,大人們好像也不能答復得使我滿意,我就要在心里琢磨了。 家住在虎坊橋,這是一條多姿多彩的大街,每天從早到晚所看見的事事物物,使我常常琢磨的人物和事情可太多了。我的心靈,在那小小的年紀里,便充滿了對人世間現實生活的懷疑、同情、不平、感慨、興趣……種種的情緒。 如果說我后來在寫作上有怎樣的方向時,說不定是幼年在虎坊橋居住的幾年,給了我最初的對現實人生的觀察和體驗吧! 沒有一條街包含了人生世相有這么多方面;在我幼年居住在虎坊橋的幾年中,是正值北伐前后的年代。有一天下午,照例的,我們姊弟們洗了澡換了干凈的衣服,便跟著宋媽在大門口上看熱鬧了。這時來了兩個日本人,一個人拿著照像匣子,另一個拿著兩面小旗,是青天白日旗。紅黃藍白黑五色旗剛剛成了過去。小日本兒會說日本式中國話,拿旗子的走過來笑瞇瞇地對我說: “小妹妹的照像的好不好?” 我不知道這是怎么一回事,和妹妹直向后退縮。他又說: “沒有關系,照了像的我要大大的送給你的。”然后他看著我家的門牌號數,嘴里念念有詞。 我看看宋媽,宋媽說話了: “您這二位先生是——?” “噢,我們的是日本的報館的,沒有關系,我們大大的照了像。” 大概看那兩個人沒有惡意的樣子,宋媽便對我和妹妹說:“要給你們照就照吧!” 于是我和妹妹每人手上舉著一面青天白日旗,站在門前照了一張像,當時也不知道究竟是為什么要這樣照。等到爸爸回家時告訴了他,他不但沒有生氣,反而玩笑著說: “不好嘍,讓人照了像寄到日本去,不定是做什么用哪,怎么辦?” 爸爸雖然玩笑著說,我的心里卻是很害怕,擔憂著。直到有一天,爸爸拿回來一本畫報,里面全是日本字,翻開來有一頁里面,我和妹妹舉著旗子的照片,赫然在焉!爸爸講給我們聽,那上面說,中國街頭的兒童都舉著他們的新旗子。這是一本日本人印行的記我國北伐成功經過的畫冊。 對于北伐這件事,小小年紀的我,本是什么也不懂的,但是就因為住在虎坊橋這個地方,竟也無意中在腦子里印下了時代不同的感覺。北伐成功的前夕,好像曾有那么一陣緊張的日子,黃昏的虎坊橋大街上,忽然騷動起來了,聽說在選學生,而好客的爸爸,也常把家里多余的房子借給年輕的學生住,像“德先叔叔”(《城南舊事》小說里的人物)什么的,一定和那個將要迎接來的新時代有什么關系,他為了風聲的關系,便在我家有了時隱時現的情形。 虎坊橋在北京政府時代,是一條通往最繁華區的街道,無論到前門,到城南游藝園,到八大胡同,到天橋……都要經過這里。因此,很晚很晚,這里也還是不斷車馬行人。早上它也熱鬧,尤其到了要“出紅差”的日子,老早,街上就涌到各處來看“熱鬧”的人。出紅差就是要把犯人押到天橋那一帶去槍斃,槍斃人怎么能叫做看熱鬧呢?但是那時人們確是把這件事當做“熱鬧”來看的。他們跟在載犯人的車后面,和車上的犯人互相呼應的叫喊著,不像是要去送死,卻像是一群朋友歡送的行列。他們沒有悲憫這個將死的壯漢,反而是犯人喊一聲:“過了十八年又是一條好漢!”群眾就跟著喊一聲:“好!”就像是舞台上的演員唱一句,下面喊一聲好一樣。每逢早上街上涌來了人群,我們就知道有什么事了,好奇的心理也鼓動著我,躲在門洞的石墩上張望著。碰到這時侯,母親要極力不使我們去看這種“熱鬧”,但是一年到頭常常有,無論如何,我是看過不少了,心里也存下了許多對人與人間的疑問:為什么臨死的人了,還能喊那些話?為什么大家要給他喊好?人群中有他的親友嗎?他們也喊好嗎? 同樣的情形,大的出喪,這里也幾乎是必經的街道,因為有錢有勢的人家死了人要出大殯,是所謂“死后哀榮”吧,所以必須選擇一些大街來繞行,做一次最后的煊赫!沿街的商店有的在馬路沿擺上了祭桌,披麻帶孝的孝子步行到這里,叩個頭道個謝,便使這家商店感到無上的光榮似的。而看出大殯的群眾,并無哀悼的意思,也是抱著看熱鬧的心情,流露出對死后有這樣哀榮,有無限羨慕的意思在。而在那長長數里的行列中,有時會看見那胖子老乞丐的。他默默的走著,面部沒有表情,他的心中有沒有在想些什么?如果他在年輕時不蕩盡了那些家產,他死后何嘗不可以有這份哀榮,他會不會這么想? 欺騙的玩意兒,我也在這條街上看到了。穿著藍布大褂的那個瘦高個子,是賣假當票的。因為常常停留在我家的門前,便和宋奶很熟,并不避諱他是干什么的。宋媽真奇怪,眼看著他在欺騙那些鄉下人,她也不當回事,好像是在看一場游戲似的。當有一天我知道他是怎么回事時,便忍不住了,我繃著臉瞪著眼,手插著腰,氣勢洶洶地站在門口。賣假當票的竟說: “大小姐,我們講生意的時候,您可別說什么呀!” “不可以!”我氣到極點,發出了不平之鳴,“欺騙人是不可以的!” 我的不平的性格,好像一直到今天都還一樣的存在著。其實,對所謂是非的看法,從前和現在,我也不盡相同。總之是人世相看多了,總不會不無所感。 也有最美麗的事情在虎坊橋,那便是春天的花事。常常我放學回來了,爸爸在買花,整擔的花挑到院子里來,爸爸在和賣花的講價錢,爸原來只是要買一盆麥冬草或文竹什么的,結果一擔子花都留下了。賣花的拿了錢并不掉頭走,他會留下來幫著爸爸往花池或花盆里種植,也一面和爸爸談著花的故事。我受了勤勉的爸爸的影響,也幫著搬盆移土和澆水。 我早晨起來,喜歡看墻根下紫色的喇叭花展開了她的容顏,還有一排向日葵跟著日頭轉,黃昏的花池里,玉簪花清幽地排在那里,等著你去摘取。 虎坊橋的童年生活是豐富的,大黑門里的這個小女孩是喜歡思索的,許是這些,無形中導致了她走上以寫作為快樂的路吧! 1961年7月 林海音作品_林海音散文與小說 林海音:擠老米 林海音:蔡家老屋分頁:123
ACC711CEV55CE
文化用紙產業節稅方式
暫繳稅額怎麼計算 台中大里報稅諮詢 台中會計師務所哪間最專業
限會員,要發表迴響,請先登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