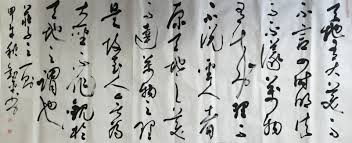
莊子南華經卷七下 -外篇第二十二 知北游
知北游於玄水之上,登隱(上分下廾)之丘,而適遭無為謂焉。知謂無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闋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
,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為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今已為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也死之徙,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徙,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為謂,無為謂不應我,非不應我,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 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為巨,未離其內;秋豪為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沉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舜問乎丞:「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子孫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齊戒,疏(上艸下瀹) 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跡,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肢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為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喑醷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果蓏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弢,墮其天(上失下衣)。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眾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 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也,每下愈況。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遍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游乎無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為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閎,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為盈虛非盈虛,彼為衰殺非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也。」
(女可)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女可)荷甘日中奓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嚗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弇堈吊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豪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 況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道,而非道也。」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 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大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游乎太虛。」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為無有矣,何從至此哉!」
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末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游。 」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狶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上敕下韭)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皋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 。悲夫,世人直謂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語譯
這位先生姓智,名慧,外號小聰明,是土生土長的中 原人。 智先生要學道,遂去北方遠遊,尋師訪友。 為什麼 要選擇北方? 因為道是看不見的,道躲在幽暗處,而北方 正是幽暗之所在,北冥不是有半年長夜嗎。 對,要學道, 去北方。
智先生向北方愈走愈遠。 夜愈長了,北斗星愈高了。 走到一條黑河,名曰玄水,唯見墨波黯黯。 玄水北岸,一 座小山,名曰隱氛山,終年隱藏在氛霧裡,智先生爬上山 ,遇見無為謂先生。 無為謂也就是不用說。 這位先生忘言 已有多年了。
智先生問道于無為謂,說:「我有三個問題想請教你 。 怎樣思維,怎樣考慮,才能懂道? 如何處世,如何為人 ,才能合道? 什麼方向,什麼路線,才能得道? ”
無為謂不回答以上三個問題。 不是不願回答,而是忘 卻言論,不能回答,啊不,不是不能回答,而是不曉得該 怎樣回答才好。
智先生白問了,心頭焦急,轉身便走,遂去南方遠遊 ,繼續尋師訪友。 看來道不在幽暗處,或許在光明處,而 南方正是光明之所在,熱帶不是有陽光耀眼嗎。 對,要學 道,去南方。
智先生向南方愈走愈遠。 天愈熱了,棕櫚樹愈多了。 走到一條亮河,名曰白水,唯見銀波晃晃。 白水南岸,一 座大山,名曰狐闋山,峰壑看得非常清楚。 心頭藏有任何 狐疑,到此便會一掃而光,故名。 智先生爬上山,老遠老 遠就望見了誑倔先生,竟看透了他的五臟六腑,真是太明 白了。 誑倔也就是不實而武斷,這位先生據說樣樣皆懂。
智先生問道于誑倔,仍提出那三個問題。
誑倔說:「嘻! 我懂。 聽我回答你。 」剛擺出傳道的 架子,怎麼就啞口啦,誑倔急得臉紅,直拍前額。 似乎已 經想好的答案,此時只剩一片空白,再也想不出來。 真是 怪事!
智先生又白問了,遂去西方昆倉山的仙宮拜見黃帝, 又提出那三個問題。
黃帝回答說:「非思維,非考慮,才能懂道。 不處世 ,不為人,才能合道。 無方向,無路線,才能得道。 ”
智先生說:「你懂道,我現在也懂了。 看來唯有咱倆 懂,無為謂和誑倔都不懂呢,對嗎? ”
黃帝說:「不對。 無為謂真懂道。 誑倔作懂道狀。 我 和你終究是門外漢喲! 懂道者不談論,談論者不懂道。 這 就是為什麼聖人不重言教而重身教。 道非某種思想體系, 所以談不出,抓不住。 德非某種行為標準,所以做不出, 達不到。 仁有可能是裝模作樣的。 義有可能是傷天害理的 。 禮是演戲,集體的欺騙。 所以說,從我起的歷代君王, 失去道而提供德,失去德而提倡仁,失去仁而提倡義,失 去義而提倡禮──禮是害道的空花,搗亂的賊頭。 所以說 ,人要學道,就得打掉空花,天天打,進而打掉傷天害理 的義,進而打掉裝模作樣的仁,回到無為狀態。 無為,不 去製造社會問題,什麼事情都好辦啦。 當今社會失道已久 ,道被化為意識形態的禮儀,的義方,的仁政,看得見, 講得清,摸得著,要想找回正道,不感到困難嗎? 說容易 也容易,如果有偉大人物出現,扭轉社會的趨勢。 ”
黃帝又說:「生是死的後輩,死是生的前輩。 倒過來 說也通,生是死的前輩,死是生的後輩。 生死到底誰在前 誰在後,誰也說不清。 人的生命不過是陰陽二氣的結合。 結合了,我們說這是生。 散離了,我們說這是死。 如果死 生互為後輩,而後輩又無窮,我們面對生閉環,還怕什 麼。 萬物的生命皆是陰陽二氣的結合,這是萬物的同一性 ,亦即共性。 萬物與人一樣,把自己喜愛的,例如生,譽 為神奇,同時把自己厭惡的,例如死,詆為臭腐。 所謂臭 腐到頭來又轉化為神奇,所謂神奇到頭來又轉化為臭腐, 正如生閉環。 所以說,遍天下的生命現象,無論怎樣紛 繁,就其本質而言,不過是陰陽合成的一氣罷了。 聖人齊 物,看重同一。 ”
智先生說:「我問道于無為謂,無為謂不回答我。 不 是不能回答我,而是不曉得該怎樣回答我。 我同道于誑倔 ,誑倔剛做出傳道的樣子,就閉嘴不告訴我啦。 不是不願 告訴我,而是剛要告訴就忘了已經想好的答案。 我問道于 你,你回答了我。 你懂道,怎麼說是門外漢? ”
黃帝說:「無為謂真懂道,因為他不曉得該怎樣談論 道。 誑倔作懂道狀,因為他畢竟忘記了談論道。 我和你終 究是門外漢,因為我們曉得用智,談得頭頭是道。 ”
智先生後來又遇見誑倔,向他轉述了黃帝的言論。 誑 倔很欣賞黃帝的口才。
天地變化,昭示浩蕩的美德,而不使用語言。 四季循 環,出示明確的時令,而不發表談話。 萬物盛衰,默示完 整的原理,而不附加解釋。 聖人本著天地的美德,洞察萬 物的原理,只做不說。 所以,超聖的至人連做也免了,讓 萬物自己去做。 大聖人雖然也做一做,但不發明新的主義 。 聖人,大聖人,至人,都以天地的美德為觀摹的物件。
看那神靈,微妙之至,是他參與了一切變化過程。 萬 物盛衰,死的死,生的生,千姿百態,仿佛天成,誰認識 自己的根,那微妙的神靈。 萬物紛紛芸芸,各有一本厚厚 的演變史,長久的生存,誰管他神靈活神靈。 這並不妨礙 神靈的存在。 空間那樣廣大,還得受他管轄。 秋毫那樣細 小,也得靠他監造。 有他參與變化,萬物方能有盛衰的過 程,棄舊圖新。 有他參與變化,陰陽方能有離合的過程, 送死迎生。 有他參與變化,四季方能有迴圈的過程,寒盡 回春。 他黯然存在,似乎已經逃亡,他顯然靈驗,卻又不 肯亮相。 可憐我們這些生物,全是他在天天牧養,到死也 不認識他,那微妙的神靈,偉大的放牛郎。 他就是道,他 就是我們的總根。 你懂得這點,就有資格觀摹自然,洞察 萬物的原理了。
齧缺先生多智,曾經是有名的辯論狂,後來意識到自 己的錯誤,改正了。 齧缺的老師王倪,王倪的老師蒲衣, 都是修道的隱士。
齧缺問道于老老師蒲衣。 蒲衣說:「整頓你的操行, 清掃你的視聽,自有元氣附你身。 收斂你的智慧,洗滌你 的胸襟,自有靈氣入你心。 天地將以美德充實你,使你完 備。 自然將以妙道啟發你,讓你皈依。 到那時你將有天真 的眼眸,純潔幼稚如初生的牛犢,不再拖住別人辯論,再 三追問何故,何故。 」第三個何故尚未說出口,蒲衣閉嘴 ,因為齧缺視聽俱息,胸襟已空,睡著了。
蒲衣非常滿意,一躍而起,邊走邊唱:「鎖閉感官, 身似枯樹��眠。 停止意念,心似寒燼無煙。 放棄了真才實 學,不守成見,懶與他人爭辯。 當面睡一個美美的黑甜, 諸事少管。 如此好修養,豈可等閒看! ”
舜爺坐天下,什麼都有了。 一日聽完彙報,作了指示 ,感到滿意,叫百官坐下來陪他論道。 一位丞官發言不錯 。 舜問他:「我能擁有道嗎? ”
丞說:「你連自己的身體都不能擁有,還能擁有道嗎 ! ”
舜說:「我的身體不歸我所有,歸誰呢? ”
丞說:「你的身體是陰陽給你塑造的外形,不歸你所 有。 你的生命是陰陽給你譜寫的歌曲,不歸你所有。 你的 本性是陰陽給你點染的色彩,不歸你所有。 你的子孫是陰 陽給你蛻變的新我,不歸你所有。 你是乘客,不曉得哪一 站是終點。 你是房客,不曉得哪一天要搬家。 你是食客, 不曉得哪一味最可口。 總之你是客,主權不屬你。 車掌喊 你下,你就得下。 房東要你搬,你就得搬。 宴主請你嘗, 你就得嘗。 一陰一陽,二氣運動,道在其中,怎麼可能歸 我們所有呀! ”
孔子壯年時去洛陽,第一次見老聃。 老聃那時才是中 央圖書館館長,工作很忙。 孔子高談儒家的仁義學說,挨 了老聃一頓好洗刷。 回到驛館,痛加反省。 幾天後又去看 老聃,請教修道。
孔子說:「今天你休假,敢請談談道。 ”
老聃說:「你得持齋守戒,來一番心靈的大掃除,把 你的精神洗乾淨,把你的所謂真才實學一棍子打個粉碎, 方可修道。 道,盲然深邃,不知從何談起。 我只能給你談 一個輪廓。 ”
老聃又說:「宇宙之初,冥冥的大黑暗炸裂,昭昭的 大光明誕生。 一切有條有理的結構,來自無名無狀的渾沌 。 陰陽二氣合成內神,陰陽二精合成外形,乃有生命。 生 命有形道無形,無形生有形。 有形的萬物授形給後代。 有 形生有形,所謂以形相生。 形既穩定,各生各的,有條不 紊。 所以獸形九竅,頭七竅,尾二竅,皆是胎生。 所以鳥 形八竅,頭七竅,尾一竅,皆是卵生。 道無形,看不清, 證不明。 說是來了,為什麼不留腳印? 說是去了,到哪裡 才有止境? 說要尋道去吧,哪有住宅哪有門? 如果全方位 路徑無限多,豈不等於沒有路徑,叫人怎樣去尋? 那些順 道的人,四肢變得強勁,思想變得豁達,靈耳聰,靈眼明 ,用心而不勞心,有靈活的應變能力,無死板的奮鬥綱領 。 天不得不高懸,地不得不橫陳,太陽月亮不得不運行, 動物植物不得不昌盛,這就是道喲! ”
老聃又說:「博學不是真知,辯才不是善德。 這些小 玩藝,聖人早就戒掉了。 聖人務虛道,不追求實學,因為 實學有限,虛道無限。 聖人腹藏無限,任你輸入不見遞增 ,任你輸出不見遞減,深深若大海,巍巍若高山,經常維 持著恒量的迴圈。 那是一座思想庫,萬物來取用,始終用 不完。 以聖人的虛道做尺規,測量那些儒派人士所推崇的 博學啦辯才啦,便能看清他們的實學原來是歪道喲! 回頭 看看虛道,供應萬物取用,庫存始終不空,這才是正道喲 ! ”
老聃又說:「存活在中國的人類,其稟性陰不陰,陽 不陽,居住在天之下,地之上,如你如我如他,暫且裝作 人樣。 都要回老家,存活不久長。 從老家那一頭看現在, 所謂人生,活一口氣罷了。 有人氣短,有人氣長,差距微 不足道,僅在數量。 轉瞬的快活,匆匆的時光,談什麼桀 紂乃暴君,堯舜乃聖王! 種瓜得瓜,栽果得果,瓜果互異 。 草本的瓜,木本的果,形態雖有差別,但是作為植物, 仍能找到共同的原理。 人比瓜果更複雜些,多一重社會性 ,所以地位有高有低,好比牙齡大小不一。 凡人嫌貧愛富 ,聖人不因貧富而憂喜。 順境要去了,他不挽留。 逆境要 來了,他不逃避。 說他有德,因為他能調整自己,適應順 逆的境地。 說他有道,因為他能更新自己,回應變革的原 理。 至道至德,遠古酋長所以開創世紀。 有道有德,炎黃 堯舜所以相繼崛起。 ”
老聃最後說:「也算頂天立地,人啊,你的一生,好 比透過縫隙看奔跑的白駒,一晃成了過去! 勢不可當,昂 昂然新秀登場。 時不再來,淒淒然老朽下臺。 變變變,胎 兒出頭露了臉。 變變變,衰翁入棺成了殮。 變生變死,都 是那個變,生物為之哀號,人類為之悲歎。 快放下貪生的 包袱,快解開怕死的疙瘩,讓靈魂飄向天涯,讓肉體埋入 地下,你終於回老家。 當初你投生,無形變成有形。 現在 你返本,有形變回無形。 無形,有形,無形。 否定,肯定 ,否定。 這是常識,非道友也首肯,用不著討論。 討論什 麼辯證不辯證,老生常談罷了,可聽可不聽。 你若決心修 道,就不必去研究所謂學問。 人既得道,不再多言,誇誇 其談,離道很遠。 記住,能夠公開討論的往往不是問題的 關鍵。 守我沉默,勝他雄辯。 傳道哪能作報告。 聽報告不 如睡大覺。 關閉眼竅耳竅,內視內聽,才有可能得道。 ”
東郭先生拖住莊子論道。 莊子莫可奈何,有問必答。 如果不是東郭先生廚下已經備了午飯待客,莊子早就拔腿 走了。
東郭先生說,「你所說的道,到底在哪裡? ”
莊子說:「哪裡都在。 ”
東郭先生說:「不確指,可不行。 ”
莊子說:「在螻蛄,在螞蟻。 ”
東郭先生說:「怎麼這樣低下喲! ”
慶子說:「在旱稗,在水稗。 ”
東郭先生說:「怎麼更低下了喲! ”
莊子說:「在瓦,在磚。 ”
東郭先生說:「動物降到植物,植物降到無生物,怎 麼愈來愈低下喲! ”
莊子說:「在屎,在尿。 ”
東郭先生覺得噁心,賭氣不再問了。
莊子說:「道嘛,哪裡都在。 我不是已經回答了嗎? 可你問個不停,問又問不到點子上。 我不得不用穢物搪塞 你,抱歉。 不過,你再三說低下,我不敢苟同。 請證之于 奴僕詢問屠夫怎樣挑選肥豬。 屠夫的回答從豬頭說到豬胯 ,愈低下,愈明白。 觀察屎尿都能發現道呢,何況觀察人 生,觀察萬物,觀察宇宙。 你不要只抓住某一物,因為道 嘛哪裡都在,沒有一物能脫離道。 反過來說,道也不能脫 離物,所以論道也不能脫離物講空話。 整體的,普遍的, 共同的,三詞形容同一物件,道。 ”
莊子又說:「讓我陪你去神游非現實的玄宮,試從整 體論道,愈論愈遠,以至於無窮吧。 讓我陪你無為吧,恬 淡而靜止吧,寂寞而虛空吧,調和而悠閒吧。 我的胸懷廣 大,無牽無掛,哪裡都不去,但游心于造化。 那是形而上 的自由王國,去呢來呢無地名可查。 我已多次去玩,尚未 找到終點。 大知之士彷徨于非現實的空間,投身造化的循 環,在自由王國裡找到無限。 ”
莊子最後說:「道支配物,與物打成一片。 道不與物 劃清界限。 萬物皆以自己為中心而分出彼此來,是萬物自 己在互劃界限,與道何干。 不必分彼此的,倒去互劃界限 。 互劃了界限又怎樣? 從道的角度看,萬物皆是受支配者 ,不分彼此,完全可以等量齊觀,根本不必互劃界限。 道 與物打成一片,道永恆,物短暫。 富足了是盈滿;物自盈 滿,道不盈滿。 貧窮了是虛歉;物自虛歉,道不虛歉。 興 起了是獲得;物自獲得,道不獲得。 沒落是損失;物自 損失,道不損失。 開始了是起頭;物自起頭,道不起頭。 告終了是收尾;物自收尾,道不收尾。 成功了是聚積;物 自聚積,道不聚積。 失敗了是潰散;物自潰散,道不潰散 。 盈滿,虛歉,獲得,損失,起頭,收尾,聚積,潰散, 道是萬物幕後的導演,永恆的導演。 ”
婀荷甘先生和神農先生同學道于老龍吉先生。 老龍吉 不講道,只給學生點撥幾句,使其自悟。 世俗無知,說他 們是狂人口吐狂言。
一天早晨,神農掩門,兩肘擱在炕桌,閉目游心于非 現實的國度。 這是日課,要做一整天呢。 正午,婀荷甘推 開門沖進來說:「老龍死啦! 」神農大驚,跳下炕床,扶 杖要走。 隨即想到死不足驚,砰的一聲拋掉手杖,笑著說 :「仙啊,你曉得我為人鄙陋,學道懶散,所以一死了之 ,丟下我不管。 去了去了,我的老師。 你不再點撥我以狂 言,就這樣死了麼,我的老師? ”
老龍吉的道友龠(讀‘月’)剛先生前來弔喪,聽見神 農這樣說,便發表感想說:「一人得道,天下君子紛紛跑 來投靠,說要聽他講道。 吾友老龍吉距離得道尚遠,連毫 毛尖端的萬分之一也未得呢,他都曉得少說狂言,早些死 去。 何況是那些得道的大師,他們怎肯公開講道呢! 道嘛 ,看不見形,聽不見聲。 有人講道,高談闊論,是他頭腦 渾沌,眼睛發黑暈。 能講清的不是道,是道講不清。 ”
能講清的不是道? 太清先生不相信,於是去問無窮先 生:「道,你知吧? ”
無窮說:「我不知。 ”
太清又去問無為先生。 無為說:「我知。 ”
太清說:「道,就你所知,也有條款吧? ”
無為說:「有。 ”
太清說:「有哪些條款? ”
無為說:「就我所知,道能使物富貴,道能使物貧賤 ;道能使物聚積,道能使物潰散。 諸如此類的說法,在我 看來,皆是道的條款。 ”
太清喜得同志,把這些話轉告無始先生,證明道是能 講清的。 太清又說:「如果我的轉述不錯,請你仲裁。 道 ,無窮先生說不知,無為先生說知。 他們兩位,誰是誰非 ? ”
無始說:「說不知的深厚,說知的淺薄。 說不知的是 內行,說知的是外行。 ”
太清仰天一歎,說:「怪哉! 不知的反而知了嗎? 知 的倒不知了嗎? 世界上竟然有不知的知,真是天曉得喲! ”
無始說:「道是聽不見的,聽見的不是道。 道是看不 見的,看見的不是道。 道是講不清的,講清的不是道。 懂 嗎,能使萬物具形的,自己一定不具形。 道不具形,道是 抽象概念。 道這個詞的意思是道路,而道路是具象概念, 可見名不副實。 ”
無始最後說:「有人來問道,誰回答了,誰不知道。 問道者聽了不知道者的回答,也不會加深對道的瞭解。 道 不能問,問不能答。 不能問的問了,是買空。 不能答的答 了,是賣空。 以賣空對買空,空對空,這樣的人嘛,外不 能勘破宇宙的奧秘,內不能反省生命的本源,怎能寄跡于 昆侖仙山,怎能游心于太虛妙境。 ”
光耀問無有:「你是有呢,還是無有? ”
無有無有任何回答。
光耀問不出結果來,只好閉嘴瞪眼,然後審視無有的 體形和顏面。 看去看來,渺渺然,空空然,無有無形無面 。 費時一整天。 要看看不見,要聽聽不見。 光耀頗不耐煩 ,揮去一拳,絕對虛無,不著邊邊。
光耀自思自歎:「絕啦! 誰能操到這樣高的境界呀! 想我光耀苦修苦練,總算操成了存在著的虛無一一看我, 明亮亮的存在著;摸我,虛無。 但我操不到無有同志的虛 無的虛無,絕對虛無。 我經多年努力,剛剛取得虛無的身 份,隨即戴上存在的帽子,就象數學的零,仍被視為一個 數位,存在於正一之後,負一之前,並非絕對虛無。 我該 怎樣爭取摘掉帽子,就象無有同志那樣,做一個貨真價實 的絕對虛無呢? ”
無有仍然無有任何回答。
國防部有軍械作坊,招納能工巧匠,製造各種武器。 作坊有個八十老翁,捶打軍用腰帶帶鉤,工藝絕佳,絲絲 入扣。 國防部長稱讚他:「你手藝真巧喲。 有道嗎? ”
他說:「我有行為守則。 二十歲那年起,捶打帶鉤便 是我的唯一愛好。 除了帶鉤,任何東西我都視而不見。 與 帶鉤無關的東西,決不研究。 捶打帶鉤六十年了,我能一 直有用,可見有用來自無用,有來自無。 一個手藝人能得 益于無,何況那些修道者比無更無,絕對虛無,當然更能 得益啦。 ”
孔子的學生冉求,亦即冉有,是魯國貴族季孫氏的家 臣。 冉求想知道開天闢地以前是什麼狀態,苦思一夜,莫 名其妙,所以特來請教孔子。
冉求問:「宇宙誕生以前,空間和時間的狀態可知不 可知呢? ”
孔子說:「可知。 古今一回事嘛。 ”
冉求問不下去,便告辭了。 第二天又來,想問個明白 ,說:「昨天我問宇宙誕生以前是否可知,老師回答可知 ,說古今一回事。 當時我覺得腦子開竅了。 回去想一夜, 今晨又覺得糊塗了。 這是為什麼呢? ”
孔子說:「昨天腦子開竅,因為先憑直覺把握住了。 今晨糊塗,因為你又用思維去探索,是不是這樣的? 宇宙 ,古是從前的今,今是將來的古,所以無古無今,古今一 回事嘛。 宇宙,既沒有誕生之日,也沒有死亡之時,所以 無始無終,永恆存在。 沒有子,沒有孫,倒有曾孫了,行 嗎? 沒有宇宙,倒有空間(宇)時間(宙)的狀態了,行 嗎? ”
冉求語塞,無言以對。
孔子說:「完啦,答不出來啦。 死是自然發生的,不 是因為現在生了所以將來必死。 生是自然發生的,不是因 為現在死了所以將來必生。 死與生,生與死,其間並無因 果關係。 死生都是有待的嗎? 不,死生都是自然發生的, 各自獨立的。 再說說宇宙吧。 宇宙歷史無窮,來路不見起 點,去路不見終點,能有物先宇宙而存在嗎? 不能。 能創 造宇宙萬物的只能是非物,不可能是物。 非物者,道也, 任何一物都不可能先宇宙而出現。 順著道,才有萬物出現 。 萬物順著道出現了,生生不已,無窮無盡。 聖人學道, 所以愛人,無限愛,永遠愛。 ”
顏回常常咀嚼孔子的訓話,吃透精神,才好實踐。 想 起孔子講過:「不推拒,不迎合。 」也就是奉行不幹涉主 義。 覺得很有道理。 可是,怎樣落實呢,還不太清楚。 于 是去問孔子。
孔子說:「古人有理想而內心穩定,作風卻很靈活, 常與外界適應。 今人無信仰而內心動搖,作風卻很固執, 常與外界衝突。 作風靈活多變,常與外界適應,並不妨礙 古人堅守理想,一成不變。 作風多變,他們心安;理想不 變,他們理得。 他們就這樣心安理得的與外界慢慢磨,而 內心穩定,決不動搖。 遠古大酋長(豕希)韋氏棲息在天然 的牧場,向外界開放。 軒轅黃帝遊玩在人工的花園,四面 有牆。 國王舜爺住在深宮,衛兵站崗。 商湯王,周武王, 躲在密室,層層設防。 一代不如一代,怎能與外界適應呢 。 等而下之,那些君子,例如儒墨兩派的大師,我是你非 ,互相傾軋,也就不足怪了。 等而又下之,當今一般社會 人士,我活你死,彼此衝突,更談不上與外界適應了。 聖 人常與外界適應,不損害任何人,任何人也無法損害他。 只有那些無所損害的人,投身社會運動,與人相推相拒相 迎相合,才可能既堅守理想又適應外界。 你我凡人沒有那 個本領,還是不推不拒不迎不合為妙。 ”
孔子答覆了顏回的提問,興猶未盡,乃仰天歎息說: 「鬱鬱的山林喲! 蔥蔥的丘野喲! 你們與我非親非故,想 起你們,我就欣欣然的快樂喲! 快樂不過片刻,悲哀跟著 來了。 哀樂要來,由不得我,我哪能抵擋。 哀樂要去,由 不得我,我哪能挽留。 想起就傷心,我們這些凡人好比旅 館房間,只配接客,形形色色的房客,包括快樂和悲哀, 想來就要來,想去就要去,由不得我們。 我們活一輩子, 只認識那些投宿的房客,不認識那些趕路的過客;只能做 那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不能做那些力不能及的事情。 我們 無知,無法認識世界;我們無能,無法扭轉乾坤。 我們所 有的凡人,沒有一個能逃脫如此可悲的困境。 誰拼命掙扎 ,想逃脫大家都逃不脫的困境,豈不可悲複可悲嗎? 所以 我要說,最正確的言論就是不發表任何言論,最正確的措 施就是不採取任何措施。 這就是為什麼要奉行不幹涉主義 了。 至於什麼普及知識,小兒科罷了。 ”
研討:
外、雜篇來源駁雜,秦漢以來,多數仍認為與內篇同屬莊子作品。宋代蘇軾指出其中有四篇,應非莊子所作。清代王夫之論析外、雜篇思想與內篇不同,不是莊子之書。至今,一般認為外雜篇,應是莊子後學及道家相關學者所作,經長期積累,由漢朝人所編匯,附於內篇之後。外雜篇之編纂,反映漢朝人對莊子思想與道家體系的理解。《史記》中司馬談〈論六家要旨〉所論道家,與今日學者所論,差異很大,即可見其中梗概。《莊子》外、雜篇,篇目雖雜,大體包括述莊、黃老、無君等主要內容。
* 首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