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征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是台中中區新鮮人職涯規劃最佳稅務後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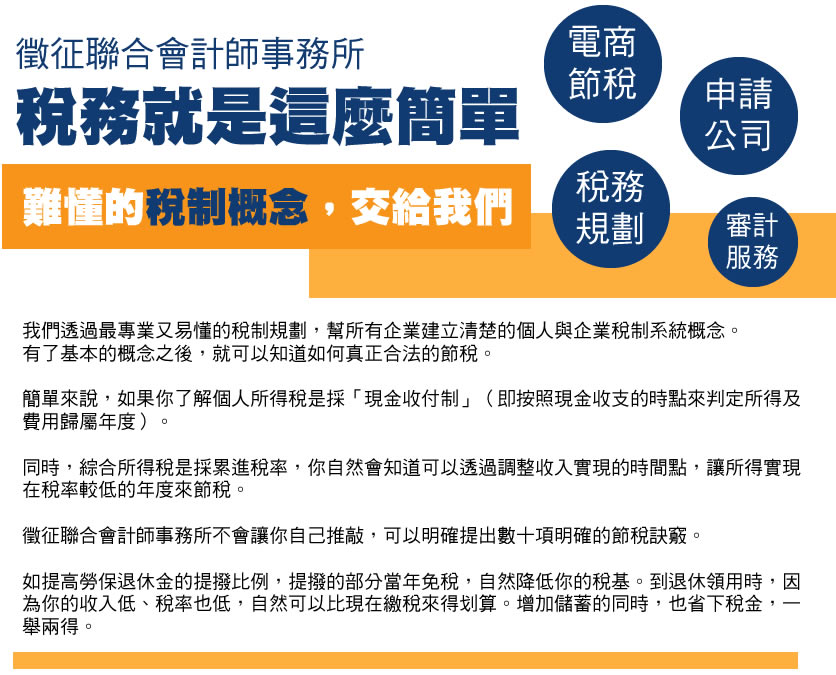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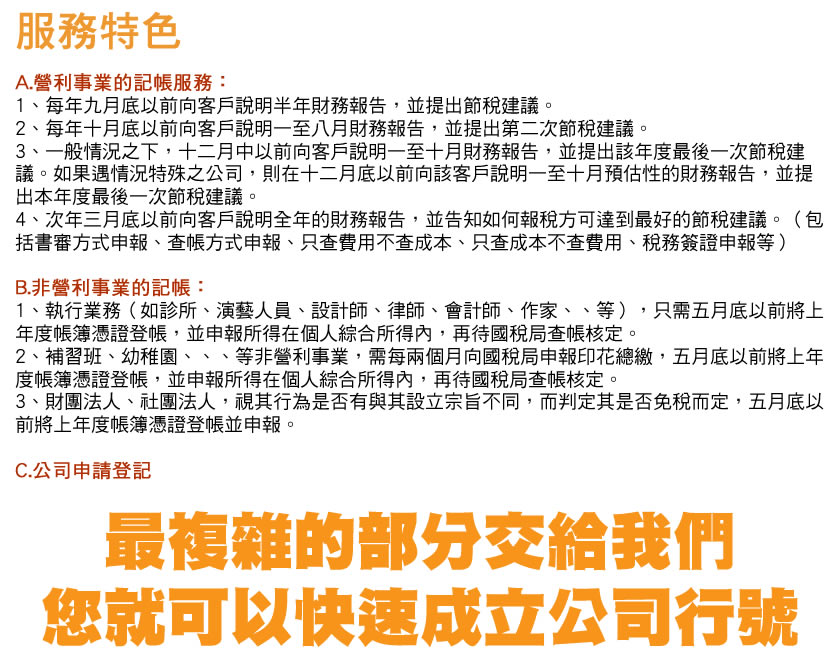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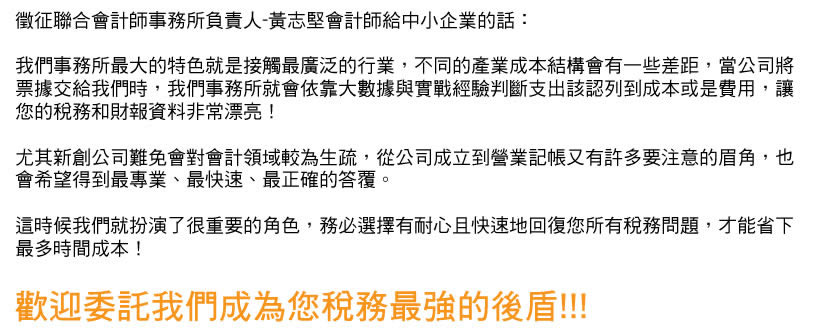
台中大里確信會計服務推薦, 台中北屯稅務政策與爭議, 台中大里學校稅務諮詢
朋友感言(一) “朋友”二字,是個神圣的字眼,生活的經歷中,每每證明了這一點。 朋友,讓人有地方傾訴心中的話語,不論是痛苦、幸福還是羞于見人的心靈;朋友,讓人在最困難的時候想起他,他會義無反顧的幫助你,因而,賦予你一顆感恩的心;朋友是一面鏡子,他照出了你的丑陋和罪過,因而,使你深思和升華自我;朋友的手是干凈的,他送給你的花是香的真的,你會因為擁有這樣的朋友而脫胎換骨、獲得新生。朋友不在多,擁有朋友的人是生活中的幸運者。 朋友感言(二) 我在琢磨我是無知者無畏還是知之而敢為……回想起來某些事真是汗…… 有時覺得誰都不了解我,只要是人都有復雜的感情和思想,不要去低估任何一個人的感受。而我最不擅于解釋,人也就是因為感受太敏感,思想太復雜,會產生很多預測不到的結論,我何必去解釋,知我者為知己,誤解者既乃不善我人品者。知己是要珍惜的,懷疑我人品的我更不必多言。偶是個兩極分化,善惡異常分明之人,此為天生。朋友亦追求,多多益善。 大學里有個朋友,同為感性,是甚。欣賞他對朋友的把握。似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偶畢業時,他卻突然很熱情,問他,朋友是放在心里的,感性是要用理性來控制和把握的,不可濫,但又放在心里。很感動的!工作后,只要是特殊的日子都能收到他的問候,閑聊幾句感覺非常棒。,很輕松。有時真的物以類聚,同類人說話都不用很累,很有默契。這樣的朋友是放在心里的。 同學的朋友感情是最深的吧。還是要看自己把握,承認把握得不是很好的。有不打不相識的朋友,饅頭是個不錯的人,說的不錯是指人品,很善良。以前我總認為她總是在我發難的時候出現,只是奇怪我們老說不到一塊,心里卻還想著對方。有誤會我喜歡逃避,她總要化解,讓我明白了誤會的可怕也知道了解釋的重要。這樣的朋友當然也是放在心里的。 有玩耍的朋友,不是談心的對象。當然在一起是很開心的,但是當你傷心的時候卻不會去找他們。似乎這樣的朋友只能看見美好的一面。這樣的朋友也是少不了的,淺淺的。 還有玩了很久很久感情很深的朋友,當有一天發現自己一直是那樣掏心,比任何一個朋友都掏心,而人家把我當朋友但是卻可以人格分離,懷疑我的人品卻跟我兄弟相稱,傷心了累了,感覺變質了。朋友并不因為能力而在一起,卻一定是要信任真心的,一定是想起來很溫暖的。就像哭累了的孩子躺到自己的床上可以安心地睡著…… 朋友們都在忙自己的事,我們都開始老嘍。 朋友感言(三) 在這個世界上,很多事物都在改變,朋友情誼和利益聯系越來越密切,因此,人人都提防起來了,心里筑起高高的墻,如果有人給你以示真誠,就馬上懷疑對方是不是有利可圖,在網上,朋友這個詞變得純粹一些,因為人內心有渴望,于是朋友在這個時候更象朋友,功利總算變得淡泊了一點,于是總算找到不是任何事都用收益和成本來計算的理由,放任自己的感覺,用心去感覺——朋友。 我在網上認識的朋友多為聊天室認識的,而且集中在一段時期,非常奇特,那時候瘋迷了聊天,天天沒事就貓在那里,笑笑鬧鬧認識許多朋友,感覺甚是愜意,當然,真正成為朋友,這講究機緣,合適的時候說上合適的話題,洋洋灑灑,心與心靠近,不是人人相處都可以的,奇特之處就在此了,真正的朋友能和你一起分擔憂愁,不開心時,在你的身邊,聽你絮絮叨叨,沒有想獲得什么,只是希望你變得快樂起來,沒什么能比這種殷殷的關切更讓人感動,獲得就是幸福! 在生活里,常常遇上煩心事,比如工作,比如生活,壓力就象空穴來風,四面八方,撲面而來,訴說成了一種必要,拿起手機,翻開電話薄發現沒人可說,就算可說者,也無法暢所欲言了,保留一些不發泄完,難言的別扭,于是,網絡成就了你發泄的需要,給你提供一個抒解的平台,如果有一天,一位朋友在隔天給你發來這樣的信息:你好了么?昨晚一夜沒睡好……接到的時候你除了感動什么也不必做,(www.lz13.cn)紛繁世界,居心叵測著多了去了,但你也不必懷疑每顆真心,畢竟,你并不是時時刻刻都值得別人算計的,于是你心安理得的獲得吧,在適當的時候懂得獲得是一個聰明的人。 時間一天一天,一月一月,一年一年,有一天,你自己都忘了自己是什么時候來到這世界上了,當然,曾幾何時,因為你的生日,桌上擺滿了玫瑰,堆滿了禮品,吃飯,KTV,生日宴,無一不有,那是多么的風光,但是歲月,讓人學會健忘,多年以后,就快沒人記得你生日的時候,就在這個快已經忘了的時刻,朋友為你發來生日祝福,輕輕的一句:你的生日快到了,祝你幸福!什么也不必多說,感激之情溢滿心間,那是久違的甘露,滋潤著干枯的心田,于是發現,功利被拋出好遠,原來人間還有這樣的真情!于是你發現,原來自己并不是那么麻木,原來感動就在那么一瞬間。 朋友,就是寒冷時為你燃起的那爐火,網絡就象一個社會,構成簡單的人生,也有險山惡水,也遍地猜忌和險灘,也有時候會把你丟到寒冷的冬季里,朋友就是此時為你燃起的那爐火,為你融去冷冷的冰,為你擋住風雨,為你劈開荊棘,為你撥開慘云蒙霧,看到溫暖的陽光,原來人生好美。 所謂生活的本質就是精神的去處,網絡可算是人的精神去處之一了,當有人對你說,你將成為他一生的牽掛,于是麻木的心動了一下,雖然早就看透諾言的保質期限,也不必去細思這話的真假,是真言,要感動,有人為你至此。是謊言,更要感激,大千世界,你只是一介凡人,長相也一般,沒有什么值得人可覬覦的,有人為你費盡心思,讓你期待一生到底有多長,于是你只要交付自己的真誠,得到的回報是一個觀察人生的新視角,對人性美的一瞥,上班繁忙之余,偶而想起,美美的一笑,原來獲得真的很幸福。 感謝,這些讓我看到人性美的朋友,帶給我陽光,帶給我甘露,也帶給我善良的勇氣,心中充滿祝福,祝他(她)們一切都好。 每日感言 我的教育感言 成功感言分頁:123
《我的童年》 文/季羨林 我的童年回憶起自己的童年來,眼前沒有紅,沒有綠,是一片灰黃。 七十多年前的中國,剛剛推翻了清代的統治,神州大地,一片混亂,一片黑暗。我最早的關于政治的回憶,就是“朝廷”二字,當時的鄉下人管當皇帝叫坐朝廷,于是“朝廷”二字就成了皇帝的別名。我總以為朝廷這種東西似乎不是人,而是有極大權力的玩意兒。鄉下人一提到它,好像都肅然起敬。我當然更是如此。總之,當時皇威猶在,舊習未除,是大清帝國的繼續,毫無萬象更新之象。 我就是在這新舊交替的時刻,于1911年8月6日,生于山東省清平縣(現改臨清市)的一個小村莊——官莊。當時全中國的經濟形勢是南方富而山東(也包括北方其它省份)窮。專就山東論,是東部富而西部窮。我們縣在山東西部又是最窮的縣,我們村在窮縣中是最窮的村,而我們家在全村中又是最窮的家。 我們家據說并不是一向如此。在我誕生前似乎也曾有過比較好的日子。可是我降生時祖父、祖母都已去世。我父親的親兄弟共有三人,最小的一個(大排行是第十一,我們把他叫十一叔)送給了別人,改了姓。我父親同另外的一個弟弟(九叔)孤苦伶仃,相依為命,房無一間,地無一壟,兩個無父無母的孤兒,活下去是什么滋味,活著是多么困難。概可想見:他們的堂伯父是一個舉人,是方圓幾十里最有學問的人物,做官做到一個什么縣的教渝,業算是最大的官:他曾養育過我父親和叔父,據說待他們很不錯-可是家庭大,人多是非多;他們倆有幾次餓得到棗林里去揀落到地上的千棗充饑-最后還足被迫棄家(其實已經沒了家)出走,兄弟倆逃到濟南去謀生:文化大革命中我自己“跳出來”反對那一位臭名昭著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作者,惹得她大發雌威,兩次派人到我老家官莊去調查,一心一意要把我“打成”地主:老家的人告訴那幾個“革命”小將,說如果開訴苦大會,季羨林是官莊的第一名訴苦者,他連貧農都不夠。 我父親和叔父到了濟南以后,人地生疏,拉過洋車,扛過大件,當過警察,賣過苦力。叔父最終站住了腳。于是兄弟倆一商量,讓我父親回老家,叔父一個人留在濟南掙錢,寄錢回家,供我的父親過日子。 我出生以后,家境仍然是異常艱苦:一年吃白面的次數有限,平常只能吃紅高梁面餅子;沒有錢買鹽,把鹽堿地上的土掃起來,在鍋堅煮水,崦咸菜,什么香油,根本見不到,一年到底,就吃這種咸菜:舉人的太太,我管她叫奶奶,她很喜歡我。我三叫歲的時候,每天一睜眼,抬腿就往村里跑(我們家在付外),跑到奶奶跟前,只見地把手一卷,卷到肥大的袖子里面,手再伸出來的時候,就會有半個白面饅頭拿在手中,遞給我?我吃起來,仿佛是龍膽風髓一般,我不知道天下還有比白面饅頭更好吃的東西。這白面饅頭是她的兩個兒子(每家有幾十畝地)特別孝敬她的、她喜歡我這個孫子,每天總省下半個,留給我吃:在長達幾年的時間內,這是我每天最高的享受,最大的愉快。 大概到了四五歲的時候,對門住的寧大嬸和寧大姑,每到夏秋收割莊稼的時候,總帶我走出去老遠到別人割過的地里去抬麥子或者豆子、谷子:一天辛勤之余,可以揀到一小籃麥穗或者谷穗、晚上回家,把籃子遞給母親,看樣子她是非常歡喜的-有一年夏天,大概我拾的麥子比較多,她把麥粒磨成面粉,貼了一鍋死面餅子:我大概是吃出味道來了,吃完了飯以后,我又偷了一塊吃,讓母親看到了,趕著我要打:我當時是赤條條渾身一絲不掛,我逃到房后,往水坑里一跳。母親沒有法子下來捉我,我就站在水中把剩下的白面餅子盡情地享受了。 現在寫這些事情還有什么意義呢?這些芝麻綠豆般的小事是不折不扣的身邊瑣事,使我終生受用不盡。它有時候能激勵我前進,有時候能鼓舞我振作。我一直到今天對日常生活要求不高,對吃喝從不計較,難道同我小時候的這一些經歷沒有關系嗎?我看到一些獨生子女的父母那樣溺愛子女?也頗不以為然。兒童是祖國的花朵,花朵當然要愛護;但愛護要得法,否則無異是坑害子女。 不記得是從什么時候起我開始學著認字,大概也總在四歲到六歲之間。我的老師是馬景功先生:現在我無論如何也記不起有什么類似私塾之類的場所,也記不起有什么《百家姓》、《千字文》之類的書籍。我那一個家徒四壁的家就沒有一本書,連帶字的什么紙條子也沒有見過。反正我總是認了幾個字,否則哪里來的老師呢?馬景功先生的存在是不能懷疑的。 雖然沒有私塾,但是小伙伴是有的:我記得最清楚的有兩個:一個叫楊狗。我前幾年回家,才知道他的大名,他現在還活著,一字不識;另一個叫啞巴小(意思是啞巴的兒子),我到現在也沒有弄清楚他姓甚名誰。我們三個天天在一起玩,洑水,打棗,捉知了,摸蝦,不見不散,一天也不間斷。后來聽說啞巴小當了山大王,練就了一身躥房越脊的驚人本領,能用手指抓住大廟的椽子,渾身懸空,圍繞大殿走一周。有一次被捉住,是十冬臘月,赤身露體,澆上涼水,被捆起來,倒掛一夜,仍然能活著。據說他從來不到宮莊來作案,“兔子不吃窩邊草”,這是綠林英雄的義氣。后來終于被捉殺掉。我每次想到這樣一個光著屁股游玩的小伙伴竟成為這樣一個“英雄”,就頗有驕傲之意。 我在故鄉只呆了六年,我能回憶起來的事情還多得很,但是我不想再寫下去了。已經到了同我那一個一片灰黃的故鄉告別的時候了。 我六歲那一年,是在春節前夕,公歷可能已經是1917年,我離開父母,離開故鄉,是叔父把我接到濟南去的。叔父此時大概日子已經可以了。他兄弟倆只有我一個男孩子,想把我培養成人,將來能光大門楣,只有到濟南去一條路。這可以說是我一生中最關鍵的一個轉折點,否則我今天仍然會在故鄉種地(如果我能活著的話)。這當然算是一件好事:但是好事也會有成為壞事的時候。“文化大革命”中間,我曾有幾次想到:如果我叔父不把我從故鄉接到濟南的話,我總能過一個渾渾噩噩但卻舒舒服服的日子,哪能被“革命家”打倒在地,身上踏上一千只腳還要永世不得翻身呢?嗚呼,世事多變,人生易老,真叫做沒有法子! 到了濟南以后,過了一段難過的日子;一個六七歲的孩子離開母親,他心里會是什么滋味,非有親身經歷者,實難體會:我曾有幾次從夢里哭著醒來、盡管此時不但能吃上白面饅頭,而且還能吃上肉;但是我寧愿再啃紅高梁餅子就苦咸菜。這種愿望當然只是一個幻想。我毫無辦法,久而久之,也就習以為常了。 叔父望子成龍,對我的教育十分關心。先安排我在一個私墊里學習:老師是一個白胡子老頭,面色嚴峻,令人見而生畏。每天入學,先向孔子牌位行禮,然后才是“趙錢孫李”。大約就在同時,叔父又把我送到一師附小去念書,這個地方在舊城墻里面,街名叫升官街,看上去很堂皇,實際上“官”者“棺”也,整條街都是做棺材的。此時“五四”運動大概已經起來了。校長是一師校長兼任,他是山東得風氣之先的人物,在一個小學生眼里,他是一個大人物,輕易見不到面。想不到在十幾年以后,我大學畢業到濟南高中去教書的時候,我們倆競成了同事,他是歷史教員。我執弟子禮甚恭,他則再三遜謝。我當時覺得,人生真是變幻莫測啊! 因為校長是維新人物,我們的國文教材就改用了白話。教科書里面有一段課文,叫做《阿拉伯的駱駝》。故事是大家熟知的,但當時對我卻是陌生而又新鮮,我讀起來感到非常有趣味,簡直是愛不釋手。然而這篇文章卻惹了禍:有一天,叔父翻看我的課本,我只看到他驀地勃然變色,“駱駝怎么能說人活呢?”他憤憤然了:“這個學校不能念下去了,要轉學!” 于是我轉了學:轉學手續比現在要簡單得多,只經過一次口試就行了。而且口試也非常簡單,只出了幾個字叫我們認,我記得字中間有一個“騾”字。我認出來了,于是定為高一。另一個比我大兩歲的親戚沒有認出來,于是定為初三。為了一個字,我沾了一年的便宜,這也算是軼事吧! 這個學校靠近南圩子墻,校園很空闊,樹木很多。花草茂密,景色算是秀麗的。在用木架子支撐起來的一座柴門上面,懸著一塊木匾,上面刻著四個大字:“循規蹈矩”。我當時并不懂這四個字的涵義,只覺得筆畫多得好玩而已。我就天天從這個木匾下出出進進,上學,游戲。當時立匾者的用心到了后來我才了解的意思,覺得他是非我族類。 我雖然對正課不感興趣,但是也有我非常感興趣的東西,那就是看小說。我叔父是古板人,把小說叫做“閑書”,閑書是不許我看的。在家里的時候,我書桌下面有一個盛白面的大缸,上面蓋著一個用高梁桿編成的“蓋墊”(濟南話):我坐在桌旁,桌上擺著《四書》,我看的卻是《彭公案》、《濟公傳》,《西游記》、《三國演義》等等舊小說。《紅僂夢》大概太深,我看不懂其中的奧妙,黛王整天哭哭啼啼,為我所不喜,因此看不下去。其余的書都是看得津津有味。冷不防叔父走了進來,我就連忙掀起蓋墊。把閑書往里一丟,嘴巴里念起“子曰”、“詩云”來。 到了學校里,用不著防備什么,一放學,就是我的天下。我往往躲到假山背后,或者一個蓋房子的工地上,拿出閑書,狼吞虎咽似的大看起來。常常是忘記了時間,忘記了吃飯,有時候到了天黑,才摸回家去。我對小說中的綠林好漢非常熟悉,他們的姓名背得滾瓜爛熟,連他們用的兵器也如數家珍,比教科書熟悉多了。自己當然也希望成為那樣的英雄。有一回,一個小朋友朋友告訴我,把右手五個指頭往大米缸里猛戳,一而再,再而二,一直到幾百次,上千次。練上一段時間以后,再換上砂粒,用手猛戳,最終可以練成鐵砂掌,五指一戳,能夠戳斷樹木。我頗想有一個鐵砂掌,信以為真,猛練起來,結果把指頭戳破廠,鮮血直流,知道自己與鐵砂掌無緣,遂停止不練。 學習英文,也是從這個小學開始的:當時對我來說,外語是一種非常神奇的東西,我認為,方塊字是天經地義,不用方塊字,只彎彎曲曲像蚯蚓爬過的痕跡一樣,居然能發出音來,還能有意思,簡直是不可思議。越是神秘的東西,便越有吸引力。英文對于我就有極大的吸引力:我萬沒有想到望之如海市蜃樓般。 綜觀我的童年,從一片灰黃開始,到了正誼算是到達了一片濃綠的境界——我進步了。但這只是從表面上來看,從生活的內容上來看,依然是一片灰黃。即使到了濟南,我的生活也難找出什么有聲有色的東西。我從來沒有什么玩具,自己把細鐵條弄成一個圈,再弄個鉤一推,就能跑起來,自己就非常高興了。貧困、單調、死板,固執,是我當時生活的寫照。接受外面信息,僅憑五官。什么電視機、收錄機,連影都沒有。我小時連電影也沒有看過,其余概可想見了。 今天的兒童有福了。他們有多少花樣翻新的玩具呀!他們有多少兒童樂園、兒童活動中心呀!他們餓了吃面包,渴了喝這可樂、那可樂,還有牛奶、冰激凌。電影看厭了,看電視。廣播聽厭了,聽收錄機。信息從天空、海外,越過高山大川,紛紛蜂擁而來:他們才真是“兒童不出門,便知天下事”。可是他們偏偏不知道舊社會,就拿我來說,如果不認真回憶,我對舊社會的情景也逐漸淡漠,有時竟淡如云煙了。 今天我把自己的童年盡可能真實地描繪出來,不管還多么不全面,不管怎樣掛一漏萬,也不管我的筆墨多么拙笨,就是上面寫出來的那一些,我們今天的兒童讀了,不是也可以從中得到一點啟發、從中悟出一些有用的東西來嗎? 1986年6月6日 季羨林:成功 季羨林:月是故鄉明 季羨林:不完滿才是人生分頁:123
朱自清:我是揚州人 有些國語教科書里選得有我的文章,注解里或說我是浙江紹興人,或說我是江蘇江都人——就是揚州人。有人疑心江蘇江都人是錯了,特地老遠的寫信托人來問我。我說兩個籍貫都不算錯,但是若打官話,我得算浙江紹興人。浙江紹興是我的祖籍或原籍,我從進小學就填的這個籍貫;直到現在,在學校里服務快三十年了,還是報的這個籍貫。不過紹興我只去過兩回,每回只住了一天;而我家里除先母外,沒一個人會說紹興話。 我家是從先祖才到江蘇東海做小官。東海就是海州,現在是隴海路的終點。我就生在海州。四歲的時候先父又到邵伯鎮做小官,將我們接到那里。海州的情形我全不記得了,只對海州話還有親熱感,因為父親的揚州話里夾著不少海州口音。在邵伯住了差不多兩年,是住在萬壽宮里。萬壽宮的院子很大,很靜;門口就是運河。河坎很高,我常向河里扔瓦片玩兒。邵伯有個鐵牛灣,那兒有一條鐵牛鎮壓著。父親的當差常抱我去看它,騎它,撫摩它。鎮里的情形我也差不多忘記了。只記住在鎮里一家人家的私塾里讀過書,在那里認識了一個好朋友叫江家振。我常到他家玩兒,傍晚和他坐在他家荒園里一根橫倒的枯樹干上說著話,依依不舍,不想回家。這是我第一個好朋友,可惜他未成年就死了;記得他瘦得很,也許是肺病罷? 六歲那一年父親將全家搬到揚州。后來又迎養先祖父和先祖母。父親曾到江西做過幾年官,我和二弟也曾去過江西一年;但是老家一直在揚州住著。我在揚州讀初等小學,沒畢業;讀高等小學,畢了業;讀中學,也畢了業。我的英文得力于高等小學里一位黃先生,他已經過世了。還有陳春台先生,他現在是北平著名的數學教師。這兩位先生講解英文真清楚,啟發了我學習的興趣;只恨我始終沒有將英文學好,愧對這兩位老師。還有一位戴子秋先生,也早過世了,我的國文是跟他老人家學著做通了的,那是辛亥革命之后在他家夜塾里的時候。中學畢業,我是十八歲,那年就考進了北京大學預科,從此就不常在揚州了。 就在十八歲那年冬天,父親母親給我在揚州完了婚。內人武鐘謙女士是杭州籍,其實也是在揚州長成的。她從不曾去過杭州;后來同我去是第一次。她后來因為肺病死在揚州,我曾為她寫過一篇《給亡婦》。我和她結婚的時候,祖父已死了好幾年了。結婚后一年祖母也死了。他們兩老都葬在揚州,我家于是有祖塋在揚州了。后來亡婦也葬在這祖塋里。母親在抗戰前,兩年過去,父親在勝利前四個月過去,遺憾的是我都不在揚州;他們也葬在那祖塋里。這中間叫我痛心的是死了第二個女兒!她性情好,愛讀書,做事負責任,待朋友最好。已經成人了,不知什么病,一天半就完了!她也葬在祖塋里。我有九個孩子。除第二個女兒外,還有一個男孩不到一歲就死在揚州;其余亡妻生的四個孩子都曾在揚州老家住過多少年。這個老家直到今年夏初才解散了,但是還留著一位老年的庶母在那里。 我家跟揚州的關系,大概夠得上古人說的“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了。現在亡妻生的四個孩子都已自稱為揚州人了;我比起他們更算是在揚州長成的,天然更該算是揚州人了。但是從前一直馬馬虎虎的騎在墻上,并且自稱浙江人的時候還多些,又為了什么呢?這一半因為報的是浙江籍,求其一致;一半也還有些別的道理。這些道理第一樁就是籍貫是無所謂的。那時要做一個世界人,連國籍都覺得狹小,不用說省籍和縣籍了。那時在大學里覺得同鄉會最沒有意思。我同住的和我來往的自然差不多都是揚州人,自己卻因為浙江籍,不去參加江蘇或揚州同鄉會。可是雖然是浙江紹興籍,卻又沒跟一個道地浙江人來往,因此也就沒人拉我去開浙江同鄉會,更不用說紹興同鄉會了。這也許是兩棲或騎墻的好處罷?然而出了學校以后到底常常會到道地紹興人了。我既然不會說紹興話,并且除了花雕和蘭亭外幾乎不知道紹興的別的情形,于是乎往往只好自己承認是假紹興人。那雖然一半是玩笑,可也有點兒窘的。 還有一樁道理就是我有些討厭揚州人;我討厭揚州人的小氣和虛氣。小是眼光如豆,虛是虛張聲勢,小氣無須舉例。虛氣例如已故的揚州某中央委員,坐包車在街上走,除拉車的外,又跟上四個人在車子邊推著跑著。我曾經寫過一篇短文,指出揚州人這些毛病。后來要將這篇文收入散文集《你我》里,商務印書館不肯,怕再鬧出“閑話揚州”的案子。這當然也因為他們總以為我是浙江人,而浙江人罵揚州人是會得罪揚州人的。但是我也并不抹煞揚州的好處,曾經寫過一篇《揚州的夏日》,還有在《看花》里也提起揚州福緣庵的桃花。再說現在年紀大些了,覺得小氣和虛氣都可以算是地方氣,絕不止是揚州人如此。從前自己常答應人說自己是紹興人,一半又因為紹興人有些戇氣,而揚州人似乎太聰明。其實揚州人也未嘗沒戇氣,我的朋友任中敏(二北)先生,辦了這么多年漢民中學,不管人家理會不理會,難道還不夠“戇”的!紹興人固然有戇氣,但是也許還有別的氣我討厭的,不過我不深知罷了。這也許是阿Q的想法罷?然而我對于揚州的確漸漸親熱起來了。 揚州真像有些人說的,不折不扣是個有名的地方。不用遠說,李斗《揚州畫舫錄》里的揚州就夠羨慕的。可是現在衰落了,經濟上是一日千丈的衰落了,只看那些沒精打采的鹽商家就知道。揚州人在上海被稱為江北老,這名字總而言之表示低等的人。江北老在上海是受欺負的,他們于是學些不三不四的上海話來冒充上海人。到了這地步他們可竟會忘其所以的欺負起那些新來的江北老了。這就養成了揚州人的自卑心理。抗戰以來許多揚州人來到西南,大半都自稱為上海人,就靠著那一點不三不四的上海話;甚至連這一點都沒有,也還自稱為上海人。其實揚州人在本地也有他們的驕傲的。他們稱徐州以北的人為侉子,那些人說的是侉話。他們笑鎮江人說話土氣,南京人說話大舌頭,盡管這兩個地方都在江南。英語他們稱為蠻話,說這種話的當然是蠻子了。然而這些話只好關著門在家里說,到上海一看,立刻就會矮上半截,縮起舌頭不敢嘖一聲了。揚州真是衰落得可以啊! 我也是一個江北老,一大堆揚州口音就是招牌,但是我卻不愿做上海人;上海人太狡猾了。況且上海對我太生疏,生疏的程度跟紹興對我也差不多;因為我知道上海雖然也許比知道紹興多些,但是紹興究竟是我的祖籍,上海是和我水米無干的。然而年紀大起來了,世界人到底做不成,我要一個故鄉。俞平伯先生有一行詩,說“把故鄉掉了”。其實他掉了故鄉又找到了一個故鄉;他詩文里提到蘇州那一股親熱,是可羨慕的,蘇州就算是他的故鄉了。他在蘇州度過他的童年,所以提起來一點一滴都親親熱熱的,童年的記憶最單純最真切,影響最深最久;種種悲歡離合,回想起來最有意思。“青燈有味是兒時”,其實不止青燈,兒時的一切都是有味的。這樣看,在那兒度過童年,就算那兒是故鄉,大概差不多罷?這樣看,就只有揚州可以算是我的故鄉了。何況我的家又是“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呢?所以揚州好也罷,歹也罷,我總該算是揚州人的。 1946年9月25日作 朱自清作品_朱自清散文集 朱自清:威尼斯 朱自清:說話分頁:123
ACC711CEV55CE
台中潭子家族企業稅務會計服務推薦
照明產業節稅方式 台中北屯首次公開募股(IPO) 事務所年度服務過程項目有那些
限會員,要發表迴響,請先登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