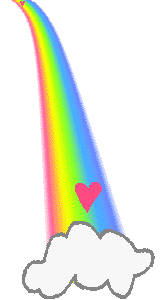你脫光了沒有? -- 泡沫生涯(四)
2008/01/28 07:07
瀏覽1,278
迴響2
推薦14
引用0
【第四回】難定奪聞暮鼓晨鐘 逢盛會看雀鳥成凰
回到土桑後不久, 殺手幫的史無生和賣冰箱的C公司相繼來電給 offer. 我和北橋妻斟酌禱告了半天, 著實難以取捨 (天平座的北橋妻只會東搖西擺, 自亂陣腳). 後來我想起一樁往事, 助我做了決定.
當年在馬里蘭大學唸書的時候, 我的指導教授見我一家四口嗷嗷待哺, 便在寒暑假替我兜攬外快, 替另一位電機系J教授測量高速電路板的數據. 工作輕鬆, J教授出手也大方, 我拿錢的時候不免露出「下次有這種好事可以再找我」的貪色. J教授見貌辨色, 知我涉世未深, 好吃易飽, 便跟我聊了聊. 他問我何時畢業, 然後給了我一句忠告: 「找第一個工作的時候, 便要思考下一個工作在那裡. 留意你未來的老闆、同事, 因為你的下一份工作跟他們大有關係」. 他的意思並非要我騎驢找馬, 隨時準備跳槽; 而是提醒我不要只看到一份工作立即的可觸可及的好處, 還要看得遠一點, 留意附加價值 – 尤其是專業人際網路的建立.
為泡沫思潮左右的我, 一心盤算著去那家公司可以賺得更多更快; J教授的話不經意的適時浮現心頭, 如暮鼓晨鐘, 讓我冷靜了下來. 大餅人人會畫, 大錢不是人人賺得到的. 或許該認真考慮他當年的忠告? S公司的殺手幫, 看來人人身懷絕技, 跟著他們混混, 或許比跟休掰博士賣冰箱高明吧? 公司會垮; 但認識些高明人, 多長點眼光見識, 卻是自家本錢、誰也搶不走的. 既下了決定, 便辭去工作. 全家趁著換工作的空檔, 返台探親. 回美之後, 我暫別了妻兒, 隻身前往波士頓.
到了S公司, 加入眾好漢的行列. 殘冬的積雪未消, 公司裡頭卻熱乎的緊. 一群三四少壯的工程師在史老大的帶領下忙得很有勁頭. 那是個「事求人」的時代, 所有的光纖公司都在搶人, 三天兩頭就有新面孔報到. 流行的笑話是: 只要會拼 Optics 這個字, 就可以找到事. 剛報到不久, 席不暇暖, 就與大夥赴巴爾的摩 (Baltimore) 參加2000年的光纖通訊會議 (OFC – Optical Fiber Communication Conference). 史老大的手下傾巢而出, 但分乘兩班飛機 (以免萬一出了意外, 一鍋砸了). 我和其他工程師滿懷興奮的到達機場, 遇到潘大可; 他依然一臉愁容, 彷彿要去參加喪禮 (幾年後事實證明, 潘老的表情確有先知預言的本事).
OFC2000 在光纖通訊發展史上佔有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地位 – 不是因其參與者之眾, 而是因其參與者之雜. 那是個極度樂觀的一窩蜂時代: 所有人 (公司, 投資人, 銀行家, 分析師, 小工程師) 都怕錯過了光纖這般車. 小公司秀出個點子, 就被大公司用駭人聽聞的天價 (幾十億美元) 搶購而去 – 雖然買的多是無法產品化的點子. 大公司當然也不是笨蛋, 他們打的是「以股換股」的算盤, 做的是用招牌抬高股價的買賣, 謀的是短線殺出的策略. OFC2000 就在這樣的氣氛中開幕了. 老天, 那看來絕不像個學術會議的現場. 近兩萬人趕集似的摩肩接踵, 人聲雜沓; 銀行家、華爾街的分析師、投機客夾在學者、工程師和展示人員之間推擠著, 用他們不懂的名詞探問下一個投資的熱點. 光學這一行本來就很小, 能來的人都來了, 參加這場作夢也想不到的、麻雀變鳳凰的嘉年華會.
說是嘉年華會, 毫不誇張. OFC2000 有三多: 人多, 派對多, 玩具多, 幾家大戶製造商在會場外租了場地, 連續三晚擺出流水席, 只要亮出會議名牌, 就可白吃白喝. Lucent (或是 Nortel?) 還安排了魔術表演, 並送每人一副魔術紙牌. 我與新同事穿梭於各家派對大打秋風, 浸泡於啤酒的泡沫中, 不亦樂乎. 參展的公司多備有各式小禮品 – T-shirt, 手提袋, 原子筆, 太陽眼鏡, 發光的Yo-Yo 球; 我想到兩個寶貝兒子, 不禁多抓了幾個. 最誇張的是, 我憑著一張名片, 竟換來了價值500元的Palm Pilot. 回波士頓的飛機上, 與一棕髮白皙新英格蘭美女為鄰. 原來她任職於波士頓的投資銀行, 也去了OFC. 她問我光產業的前景, 以及對光開關這前瞻技術的看法. 諸君請記了, 「光開關 optical switch」是光泡沫中發狂的涎沫 (foam of the optical bubble). 事實上, HP就根據噴墨印表機的原理推出了「泡沫開關 the bubble switch」, 真可謂一語成讖. 我當時那有什麼資格談產業前景, 但美女在側, 不能洩氣; 於是定定神, 把這幾天聽來的牙慧與幻想, 用乾坤大挪移神功施展出來, 成為自己的創見. 新英格蘭美女顯然以為我是專家, 跟我交換名片, 客氣的說日後還有討教之處. 我醺然自喜, 飛機在夕陽中飛越雲山, 不知今夕何夕也.
且休岔題. 話說光有光譜, S公司的大型計畫也以顏色區分, 有紅、橙、黃三旗; 史老大下轄紅黃兩旗. 我們這批光纖工程師又粗分為元件 (component)、傳輸 (transmission) 兩部. 我隸屬正黃旗元件部. (By the way, 懂光的是正旗, 不懂的是副旗. 為此, 那些做電路設計的硬體工程師提到我們就切齒有恨). 我做什麼呢? 一言以蔽之, 買辦 - 買買東西辦辦事 – 是也. 買者, 評估新技術, 開規格, 找供應商,被人招待看球、請吃飯. 辦者, 要證明買的東西可以派上用場 (所以也得懂傳輸, 能動手做軟硬體系統整合). 開規格給人做有一種頤指氣使的爽勁, 是一向埋頭苦幹做元件的我意想不到的. 你做不來嗎? 沒關係, 找下一家. 拿翹不願降價嗎? 走著瞧. 買辦頭子是司暴客; 他和他的打手, 以譏刺粗暴的言語自雄, F-word 三句話不離口, 對供應商的那股氣焰, 讓我嘆為觀止. 「形勢比人強」, 憑著號稱上億美金的採購預算, 不擺架子都不行. 妙的是, 供應商被司暴客罵得愈兇, 愈有錢賺, 還大喊: I want you to yell at me! Please yell at me!
搞傳輸的又是什麼來頭呢? AT&T Bell Lab光纖通信部主任厲鼎毅博士 (現已退休) 曾經自我解嘲說:「那是一群做不成一流物理學家、改做非線性光學的人」. 非線性光學是一行極冷門的學問, 誰知朝陽也有眷顧冷宮的一天. 因著高功率光放大器技術的成熟, 以及特殊色散補償(dispersion compensation)光纖的普及, 光訊號可一傳幾千公里; 加上80個波長的光同時在光纖中跑, 自身與彼此的非線性干擾就熱鬧起來了. 正黃旗的招牌是「高容量超長距 – high capacity ultra long haul」, 搞傳輸的人自然如魚得水. 工程師最喜歡的是難解但有解的好問題; 無解的和易解的, 都讓工程師沒事可做. 非線性光纖傳輸屬於好問題: 做海底光纜系統的, 用它的好處賺錢; 做高容量超長距傳輸系統的, 用它的壞處賺錢 (傳輸部的長老潘大可的名言為: The best way to use fiber nonlinearity is to avoid it. 我銘記於心, 奉為圭臬).
同事中確有茂才異等之士, 亦不乏溫和遜抑之宗師, 我身處其中, 一則以喜, 一則以惕礪自勉. 容下回述之.
回到土桑後不久, 殺手幫的史無生和賣冰箱的C公司相繼來電給 offer. 我和北橋妻斟酌禱告了半天, 著實難以取捨 (天平座的北橋妻只會東搖西擺, 自亂陣腳). 後來我想起一樁往事, 助我做了決定.
當年在馬里蘭大學唸書的時候, 我的指導教授見我一家四口嗷嗷待哺, 便在寒暑假替我兜攬外快, 替另一位電機系J教授測量高速電路板的數據. 工作輕鬆, J教授出手也大方, 我拿錢的時候不免露出「下次有這種好事可以再找我」的貪色. J教授見貌辨色, 知我涉世未深, 好吃易飽, 便跟我聊了聊. 他問我何時畢業, 然後給了我一句忠告: 「找第一個工作的時候, 便要思考下一個工作在那裡. 留意你未來的老闆、同事, 因為你的下一份工作跟他們大有關係」. 他的意思並非要我騎驢找馬, 隨時準備跳槽; 而是提醒我不要只看到一份工作立即的可觸可及的好處, 還要看得遠一點, 留意附加價值 – 尤其是專業人際網路的建立.
為泡沫思潮左右的我, 一心盤算著去那家公司可以賺得更多更快; J教授的話不經意的適時浮現心頭, 如暮鼓晨鐘, 讓我冷靜了下來. 大餅人人會畫, 大錢不是人人賺得到的. 或許該認真考慮他當年的忠告? S公司的殺手幫, 看來人人身懷絕技, 跟著他們混混, 或許比跟休掰博士賣冰箱高明吧? 公司會垮; 但認識些高明人, 多長點眼光見識, 卻是自家本錢、誰也搶不走的. 既下了決定, 便辭去工作. 全家趁著換工作的空檔, 返台探親. 回美之後, 我暫別了妻兒, 隻身前往波士頓.
到了S公司, 加入眾好漢的行列. 殘冬的積雪未消, 公司裡頭卻熱乎的緊. 一群三四少壯的工程師在史老大的帶領下忙得很有勁頭. 那是個「事求人」的時代, 所有的光纖公司都在搶人, 三天兩頭就有新面孔報到. 流行的笑話是: 只要會拼 Optics 這個字, 就可以找到事. 剛報到不久, 席不暇暖, 就與大夥赴巴爾的摩 (Baltimore) 參加2000年的光纖通訊會議 (OFC – Optical Fiber Communication Conference). 史老大的手下傾巢而出, 但分乘兩班飛機 (以免萬一出了意外, 一鍋砸了). 我和其他工程師滿懷興奮的到達機場, 遇到潘大可; 他依然一臉愁容, 彷彿要去參加喪禮 (幾年後事實證明, 潘老的表情確有先知預言的本事).
OFC2000 在光纖通訊發展史上佔有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地位 – 不是因其參與者之眾, 而是因其參與者之雜. 那是個極度樂觀的一窩蜂時代: 所有人 (公司, 投資人, 銀行家, 分析師, 小工程師) 都怕錯過了光纖這般車. 小公司秀出個點子, 就被大公司用駭人聽聞的天價 (幾十億美元) 搶購而去 – 雖然買的多是無法產品化的點子. 大公司當然也不是笨蛋, 他們打的是「以股換股」的算盤, 做的是用招牌抬高股價的買賣, 謀的是短線殺出的策略. OFC2000 就在這樣的氣氛中開幕了. 老天, 那看來絕不像個學術會議的現場. 近兩萬人趕集似的摩肩接踵, 人聲雜沓; 銀行家、華爾街的分析師、投機客夾在學者、工程師和展示人員之間推擠著, 用他們不懂的名詞探問下一個投資的熱點. 光學這一行本來就很小, 能來的人都來了, 參加這場作夢也想不到的、麻雀變鳳凰的嘉年華會.
說是嘉年華會, 毫不誇張. OFC2000 有三多: 人多, 派對多, 玩具多, 幾家大戶製造商在會場外租了場地, 連續三晚擺出流水席, 只要亮出會議名牌, 就可白吃白喝. Lucent (或是 Nortel?) 還安排了魔術表演, 並送每人一副魔術紙牌. 我與新同事穿梭於各家派對大打秋風, 浸泡於啤酒的泡沫中, 不亦樂乎. 參展的公司多備有各式小禮品 – T-shirt, 手提袋, 原子筆, 太陽眼鏡, 發光的Yo-Yo 球; 我想到兩個寶貝兒子, 不禁多抓了幾個. 最誇張的是, 我憑著一張名片, 竟換來了價值500元的Palm Pilot. 回波士頓的飛機上, 與一棕髮白皙新英格蘭美女為鄰. 原來她任職於波士頓的投資銀行, 也去了OFC. 她問我光產業的前景, 以及對光開關這前瞻技術的看法. 諸君請記了, 「光開關 optical switch」是光泡沫中發狂的涎沫 (foam of the optical bubble). 事實上, HP就根據噴墨印表機的原理推出了「泡沫開關 the bubble switch」, 真可謂一語成讖. 我當時那有什麼資格談產業前景, 但美女在側, 不能洩氣; 於是定定神, 把這幾天聽來的牙慧與幻想, 用乾坤大挪移神功施展出來, 成為自己的創見. 新英格蘭美女顯然以為我是專家, 跟我交換名片, 客氣的說日後還有討教之處. 我醺然自喜, 飛機在夕陽中飛越雲山, 不知今夕何夕也.
且休岔題. 話說光有光譜, S公司的大型計畫也以顏色區分, 有紅、橙、黃三旗; 史老大下轄紅黃兩旗. 我們這批光纖工程師又粗分為元件 (component)、傳輸 (transmission) 兩部. 我隸屬正黃旗元件部. (By the way, 懂光的是正旗, 不懂的是副旗. 為此, 那些做電路設計的硬體工程師提到我們就切齒有恨). 我做什麼呢? 一言以蔽之, 買辦 - 買買東西辦辦事 – 是也. 買者, 評估新技術, 開規格, 找供應商,被人招待看球、請吃飯. 辦者, 要證明買的東西可以派上用場 (所以也得懂傳輸, 能動手做軟硬體系統整合). 開規格給人做有一種頤指氣使的爽勁, 是一向埋頭苦幹做元件的我意想不到的. 你做不來嗎? 沒關係, 找下一家. 拿翹不願降價嗎? 走著瞧. 買辦頭子是司暴客; 他和他的打手, 以譏刺粗暴的言語自雄, F-word 三句話不離口, 對供應商的那股氣焰, 讓我嘆為觀止. 「形勢比人強」, 憑著號稱上億美金的採購預算, 不擺架子都不行. 妙的是, 供應商被司暴客罵得愈兇, 愈有錢賺, 還大喊: I want you to yell at me! Please yell at me!
搞傳輸的又是什麼來頭呢? AT&T Bell Lab光纖通信部主任厲鼎毅博士 (現已退休) 曾經自我解嘲說:「那是一群做不成一流物理學家、改做非線性光學的人」. 非線性光學是一行極冷門的學問, 誰知朝陽也有眷顧冷宮的一天. 因著高功率光放大器技術的成熟, 以及特殊色散補償(dispersion compensation)光纖的普及, 光訊號可一傳幾千公里; 加上80個波長的光同時在光纖中跑, 自身與彼此的非線性干擾就熱鬧起來了. 正黃旗的招牌是「高容量超長距 – high capacity ultra long haul」, 搞傳輸的人自然如魚得水. 工程師最喜歡的是難解但有解的好問題; 無解的和易解的, 都讓工程師沒事可做. 非線性光纖傳輸屬於好問題: 做海底光纜系統的, 用它的好處賺錢; 做高容量超長距傳輸系統的, 用它的壞處賺錢 (傳輸部的長老潘大可的名言為: The best way to use fiber nonlinearity is to avoid it. 我銘記於心, 奉為圭臬).
同事中確有茂才異等之士, 亦不乏溫和遜抑之宗師, 我身處其中, 一則以喜, 一則以惕礪自勉. 容下回述之.
你可能會有興趣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