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日本最早被歸為綜合誌的是《西洋雜誌》,以及由福澤諭吉,森有禮等海外歸國知識份子在1874年創刊的《明六雜誌》。但現在如果要談日本綜合誌,絕不能漏掉日本綜合誌的龍頭《文藝春秋》。

就如先前提到過,菊池寬之所以創辦這本雜誌,無非是想讓自己,及其他有識之士有一個能夠暢所欲言,抒發己見的空間。發行《文藝春秋》的文藝春秋社,如上文中提到的,是在大正十二年,也就是西元1923年由菊池寬所創立。目前發行的雜誌除了以前述的《文藝春秋》為主軸之外,還有《週刊文春》、《ALL讀物》、《文學界》、《諸君!》、《別冊文藝春秋》、《Sports Graphic
Number》、《CREA》、《Comic Bingo》、及去年六月才創刊的《Kapitan》。
除此之外,還有發行各式各樣的書籍,文庫本,全集及錄影帶,前一陣子造成話題的《麥迪遜之橋》,也是文藝春秋社的力作。另外並且以財團法人「日本文學振興會」的主辦者名義,設立了「芥川龍之介賞」「直木三十五賞」「菊池寬賞」「大宅壯一Nonfiction賞」「松本清張賞」等,可以說對日本的活字文化有不小的貢獻,每年芥川、直木賞的新受賞者總是會受到很大的注目,在這麼多的文學獎當中,為什麼這兩個獎項會特別受到大眾媒體,即文學愛好者的注目呢?文藝評論家小田切進曾經舉出了五點理由:
1.從雜誌(含單行本)中所發表的作品來發掘新人,是個很特殊的作法。
2.名稱採用芥川龍之介還有直木三十五兩位作家的名字。
3.評審委員都是一些赫赫有名的人物。
4.評審過程是公平且認真的。
5.授賞後,也會努力栽培受賞者。

要針對第二點所做的說明就是,昭和九年直木過世,而在這七年前,芥川龍之介自殺身亡,菊池寬為了悼念這兩位亡友而創立了新的文學賞,這是在昭和十年的事。在日本從戰前一直持續到現在的可以說只有這兩個獎項。曾經有哪些人得過呢?要舉台灣讀者熟悉的名字,那就是以《太陽的季節》踏入文壇,石原裕次郎的哥哥,石原慎太郎。還有前幾年剛得到諾貝爾獎的大江健三郎,深受年輕讀者喜愛的村上龍及宮本輝。直木賞有過世不久的國民作家司馬遼太郎,以鬼平犯科帳走紅的池波正太郎,失樂園的作者渡邊淳一,要說目前仍然人氣絕頂的有林真理子,山田詠美,伊集院靜,大澤在昌等人,這些人也都是直木賞的受賞者。
說了這麼多,那最令人好奇的賞金是多少呢?從最早的500日圓開始,目前的賞金,兩賞都是正賞一支懷錶,副賞日幣100萬。從通貨膨脹率看來,倒還是蠻合理的啦。至於以創辦人菊池寬為名的菊池寬賞則稍有不同,不是文學獎,而是專門頒給一些在各界有顯著功績的人士,就曾經有代表日本參加奧運馬拉松得到銅牌的有森裕子獲頒過這個獎項。
說到芥川賞,今年的芥川賞還有著一段小插曲,今年芥川賞的受賞人柳美里,由於是在日韓系人士的關係,在要舉辦新書簽名會的前夕,竟然收到右翼團體所寄發的恐嚇信,揚言要放置炸彈,最後不得不取消既定行程,雖說在文學的領域上,文學界顯然已經不介意芥川賞這個大賞為外裔人士所領走,但對激進的右翼人士來說,似乎是種侮辱般地不能忍受。從某些角度來說,日本畢竟還是個封閉,無法外容的國家,或許長久以來與韓國之間複雜的民族情感是原因之一,因為試想,如果今天得獎者是個法國人或美國人,情形或許就會另當別論。更何況得獎者的作品是以日文來創作的。

要談《文藝春秋》,首先必須先從它的厚度談起,整整多達五百多頁的內容,密密麻麻地擠滿了細小,精闢的文字。很難想像,這麼厚的一本《文藝春秋》,編輯部員,連編輯長竟然只有12人,其中有9位男性,3位女性,12位當中,有6位是20代的年輕人,很難想像這樣一本讀者多為中高年層,被定位為代表日本的綜合雜誌中堅月刊,或有人稱國民雜誌,竟然是由一群平均年齡層如此低的編輯們所創造出來的。話說回來,在日本出版界有這麼一個說法,如果想跑政治線,那麼所有學傳播的大學畢業生們最想進的出版社,就是文藝春秋社,所以文藝春秋社裡頭可以說是人才濟濟,其中又以最具有反骨精神,早稻田大學出身的校友佔大多數。
每個月有數十萬本發行量的《文藝春秋》,真的有人從封面到最後一頁地,將它看完過嗎?
《書的雜誌》創辦人椎名誠受到當時日本一位探險家,植村直己搭著狗拉的雪橇抵達北極的啟發,挑起了鬥志,決定也向這個史上無人的紀錄挑戰,「讀破」《文藝春秋》!實際閱讀時數是多少我不清楚,不過據說花了他四天的時間,還以「《文藝春秋》10月號464頁單獨完全讀破」為題,在《書的雜誌》第10號上,以探險性文章譬喻式寫法,發表了一篇文章,刊登在該期的日本雜誌特集當中。
「穿過了文春名物『同級生交歡』之後,很快地我又經過了國鐵工會的意見廣告「國鐵是非常低能源的運輸機構」,終於來到了本文的第一頁。這第一頁沒有圖片,什麼都沒有,可以說是一片荒涼,但我也總算是到達了最初的目標地點了。稍微有少許的安全感。可是出乎我意料之外地,原本以為很簡單就可以穿過的『圖片地帶76頁』,我花了一個小時以上才將它讀完。不禁讓我感到些微的焦急。」
由此可知,《文藝春秋》對許多年輕人來說,的確是一本望之卻步的大部頭雜誌。曾經努力地想要找出一本台灣能夠與之相對應的雜誌來比喻,但就內容的量來說,確實還是許多雜誌望及項背的。

《文藝春秋》除了文章多之外,還有一個特色是廣告多,雖然它比起那些廣告佔了整本雜誌一半頁數的女性雜誌要收斂許多了,但對於這麼一本讀者層定位在知識分子階級(另一個詞有人說是中產階級),又頗受好評,發行量也頗龐大的雜誌,廣告客戶豈會輕易放過,更現實一點地說,雜誌社豈又捨得。
《文藝春秋》這本雜誌曾經刊登過幾次間接改變歷史,影響時代潮流的報導。最著名的,莫過於昭和49年,西元1974年,由立花隆所寫的一篇「田中角榮研究──其金脈與人脈」,這一期的田中(醜聞)特集。10月10日發售的這一本特別號,在發售不久之後就銷售一空,在神田的古書街,甚至賣到5,000日幣的價格,發售後一個多月,田中總理被迫下台。或許這就是之後立花隆成為《文藝春秋》寵兒的原因之一吧。1998年3月,文藝春秋社甚至出版了《立花隆的一切》一書,厚達五百多頁,一出版即成為暢銷書之一,不管是哪一家書店,幾乎都高高地一疊堆在平台上宣傳促銷。
立花隆生於1940年,東京大學文學部畢業後進入文藝春秋社,被分派到《週刊文春》,在進入文藝春秋社的第四年,立花隆辭去了工作,再度進入東京大學文學部哲學科攻讀碩士。之後陸續在各雜誌中發表評論時事的文章,1974年這篇「田中角榮研究──其金脈與人脈」便是其最著名的一篇研究報導,這幾年其評論家的身分已被神化至有「知識的巨人」之別稱。在這一本文藝春秋社所出的《立花隆的一切》當中,以彩色特集介紹了立花的事務所,藏書高達三萬多冊的「貓大樓」。整棟大樓外觀為一隻黑貓,由立花隆的好友,舞台美術家妹尾河童,也就是《少年H》的作者所設計。除此之外,書中還有許多對立花隆工作伙伴的徹底深度訪談,專家所寫的作品解說,活動完全年譜,全著作清單,不只如此,還刊登了立花在《週刊文春》的職員記者時代所寫的報導,離職之後的一些文章,當然這本書中所刊載的內容無一不是對立花隆的推崇與讚頌之作。對於一向標榜報導公正的文藝春秋社來說,出版了這樣一本猛捧瞎捧一位「紀實作家」與「記者」身分的人,可以說是史無前例的,當然也因此受到了不少質疑。不過書賣得好,或許可以證明讀者縱使感到懷疑,還是不免對這位據說大腦細胞的活動力異於常人的立花隆有著抑制不了的好奇心吧。
如果要說「田中角榮研究──其金脈與人脈」是《文藝春秋》引以為傲的「功」的話,那在1998年與芥川賞發表的三月特別號同時登出的「少年A供述調書」的公開,就是文藝春秋社繼《Marco Polo》出問題停刊以來,再次於出版界引起對新聞倫理廣泛探討的一大事件。《文藝春秋》3月號的「少年A犯罪全貌當中,除了一頁由編集部所寫的前言,接著由立花隆所著一篇以「正常與異常之間」為題的15頁解說報導,主要的少年A也就是(酒鬼薔薇聖斗)的供述調書約有50頁。少年A,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是去年在日本所發生一件殘暴的斷頭殺人事件的未成年犯的代稱,因為他只有14歲,所以所有的日本媒體均以少年A來稱呼他。這份在非公開的審判程序下由檢事所做出的供述調書,先不追究是由何處流出。供述調書中所記錄,由少年A所描述的犯案過程內容十分悽慘。為此,日本最高裁判所以違反少年法為由,對文藝春秋社提出《文藝春秋》三月號停止發售的要求,沒想到《文藝春秋》不但拒絕此要求,還針對最高裁判所所發出的抗議書,回了一封公開質問信。想當然事件也就被吵大了,當然有人為《文藝春秋》維持新聞自由的堅定立場喝采,也有人為《文藝春秋》不顧內容紀錄之殘酷,暴露殺害狀況細節及不尊重隱私權而苛責。其實在這之前,去年就有《FOCUS》因為揭載少年A的照片引起了很大的轟動,《文藝春秋》面對前車之鑑,還是依然堅持走自己的路,或許是面對越來越多他誌的競爭壓力之下,不得不採取的手段。

這是一本左開右翻的雜誌,採直式排版,版面大約是《講義》雜誌的大小,頁數如先前提到的大約每期都維持在500頁上下,目次部分固定採折頁拉開的方式,翻開之後大約會有二至三頁的彩頁廣告。雖說日本現今的雜誌市場,會採取定期購讀的讀者不多,但只要堅信一個法則,那就是「製作越多的受歡迎專欄,邀請受歡迎的作家固定執筆」,那麼讀者訂閱的機會也就會自然增多。另外值得注意的一點就是,《文藝春秋》也利用不少得到上述獎項的作家,固定幫《文藝春秋》製作一些大專題的報導,譬如說上次秘魯大使館人質挾持事件時,請到國家關係專家深田佑介親自赴秘魯,對整個事件做深度的採訪報導,還有在比爾蓋茲訪日時,請到執筆常客立花隆與比爾蓋茲對談「電腦是否有辦法超越人類?」,也曾派出記者陪伴豬瀨直樹追蹤了半年日本行政改革相關議題。
《文藝春秋》就是這麼一本雜誌,而其實也是很多雜誌編輯的概念,是早在菊池寬擔任文藝春秋社的社長時,就遺留下來的。曾經有人稱讚菊池寬是天才企畫家,《文藝春秋》許多被稱為名案的好企畫,幾乎都是由菊池寬提案再加以延伸出來的,而《文藝春秋》之所以有辦法從發行3,000本的創刊號開始,成長到實際賣出數十萬冊的超級刊物,除了菊池寬創刊初期,一些和現實結合,具大眾化特色的編輯方式之外,歷代的總編輯,永井龍男、池島信平、田川博一、田中健五等人一直將傳統延續下來,也是能守住霸業的原因之一。而讀者群比《文藝春秋》更知識分子層的「諸君!」,就是在池島信平擔任社長所創刊的。池島信平本身是記者出身,出版史專家鹽澤實信還曾經寫過一本書叫「雜誌記者池島信平」來描述他這個人的一些事蹟。
翻開現在的《文藝春秋》,所能見到的第一個固定的專欄,就是「人是什麼?」,這個專欄每期都會邀請各行各業的一些菁英,如電影評論家、棒球評論家、數學家、爵士樂手,談一些自己的人生觀。只有一頁的內容,很簡潔。下面印著「大正大學」,我想這應該是與廣告主結合的專欄吧,就是由廣告主付費買版面,可是刊登的內容由雜誌社或外包單位設計,與一般傳統直接點題的廣告有較大的區別。
再越過幾頁的廣告,《文藝春秋》的廣告,如先前所說的,設定的消費者對象都是經濟能力不低的中產階級,所以其中包括了東京帝國飯店,高級相機,名牌皮件等,還有許多日本上班族不可缺少的胃藥,解酒藥廣告,這在台灣來說倒是比較少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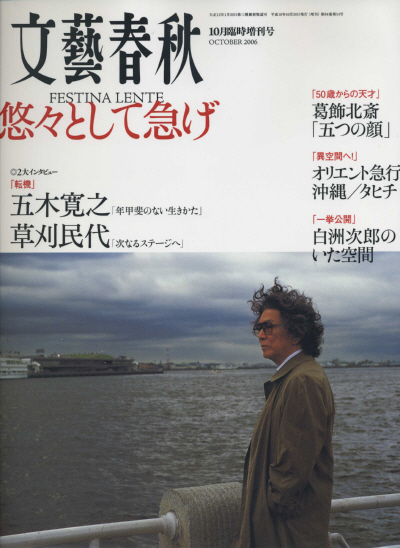
再之後,就是目前《文藝春秋》的名專欄之一「日本之顏」,這個專欄是每期挑選日本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如政治家、銀行家、企業家、作家、趨勢觀察家、漫畫家。以黑白相片為主,記錄一些他們平常的活動,包括工作上的一面,家居的一面,與朋友相聚時的一面等等,並對經歷的事蹟以兩三行文字,有所著墨,介紹。因為是以整面圖片大幅介紹,所以這個專欄大約有八頁的內容。
接著,就是我個人最喜歡的「作家的書齋」。國內的讀者大概沒有這個習慣,在日本,「名人的書齋」其實是很受注目的,可以解釋為偷窺欲吧,那些創造出流芳萬世的不朽作品作家,是在一個什麼樣的環境下,將作品醞釀出來的呢?有人說,要從環境推測人的個性,有的人從廚房來看,有的人從洗手間來看,在日本很多人喜歡從書櫃與書齋來看。尤其是那些在文學史上留下名著的作家們的書齋,更是讓人有一窺究竟的衝動。在這個單元裡,《文藝春秋》介紹了很多文學巨匠的書齋,包括了川端康成、司馬遼太郎、安部公房等人的書齋。
再來一個比較固定的單元則是「PEOPLE」,每期「PEOPLE」這個單元都會有一個固定的主題,譬如說1998年1月號主題是「亞洲電影新世紀」,就分別以兩頁的黑白照片,及四分之一篇幅的文章介紹了亞洲各地新崛起的導演,有日本的北野武,中國大陸的謝晉,香港的陳可辛,即將擔任村上龍作品電影化導演的庵野秀明,剛得到世界性電影大獎的市川準。

另外還有一些專欄單元例如「我的月間日記」就曾經刊登過喬治.歐亞曼尼的日記,描述在米蘭的生活還有在日本期間的一些活動感想,「同級生交歡」則是一個非常長壽的單元,每期找一些高中時期的校友,現今多為五、六十歲,有地位有權勢的人士,一起來談談以前的生活,彼此各自的發展,生活情況,偶爾以對談的形態出現。
除了這些之外,便大都依據每期發生的新聞,做一連串的探討,當然其中包羅萬象,政治,經濟,體育,藝能議題都有,至於文學作品的連載,如歷史小說等,像司馬遼太郎,便是之前《文藝春秋》的台柱。
已經是七十多年老舖的《文藝春秋》,面對著時代歷史小說的一些巨匠,司馬遼太郎、藤澤周平、池波正太郎等這些支持《文藝春秋》一路走過來的作家們一一過世,目前活躍的只剩女作家平岩弓枝,忠實的讀者也年齡漸漸地成長,想要開發新讀者,如何找尋年輕,優秀的執筆者,將是它今後所面對的最大課題吧。



※村上春樹的訪問稿
「挪威的森林之秘密」。
所謂寫實主義小說,並不是就把現實的事情真實地寫下來。事情是否真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能使人在閱讀的時候感到很自然。寫的東西也許其實不是自然的,但是如果能讓人讀起來覺得很自然,就是寫實主義。反過來說,雖然寫的是真實的東西,但是讀起來卻不自然,就不是寫實主義。這是我對寫實主義的定義。」村上認為,就《挪威的森林》而言,也正是如此。如果以很仔細的眼光去探究此書中的事物,或者是拿到那個時代底下去看,會發現充滿不真實或不自然的地方。但是,除非真的是很拘謹的人,要不然讀起來大體上應該會覺得相當自然。
「事情是否真實,並不是必要的;看起來自然才是重要的。就拿電影來說吧,」村上比喻說明;「科幻電影中的星星,都是在宇宙中一閃一閃的,星星究竟是怎樣,我們看不見。但是,閃耀的星星,在電影的宇宙中看起來卻是寫實的。我所謂的寫實主義便是這個意思。」
讀者對於書中的人物是否真正存在,常感到很好奇,但村上認為真實與寫實是不同的。例如令讀者感興趣的「突擊隊」聽收音機作早操一事,是確有其人其事(後來成為一名模特兒,但村上並未和其再有聯絡)。不過,據村上說明,實際的突擊隊是一個正直的人,而並非讀者所以為的那麼有趣。村上也接著說明,關於作品中人物,其實都是由作者所組合塑造的。「以這種意思來看,倒不如說我書中的人物,不論男女都是我自己。只有我自己不是我自己吧。」
訪談中,關於故事人物結局的生與死,村上也談了一些。「結局誰會活著誰會死去,我在寫的時候並不知道,完全是以寫實主義的方式寫著。」村上道:「說起來,《挪威的森林》這本書要讓誰活著或要讓誰死去都是非常困難的,最後應該是怎麼樣就是怎麼樣。然而,在寫的途中有時還是會困擾,會考慮究竟這樣作好不好。但是這些困擾,在那個時候認為應該是怎麼樣,就會照那樣作結。當然,這只是對我自己而言,別人說不定認為不是這樣吧。」(2006.2.12文藝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