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小型出版社開拓小眾市場
2007/09/12 01:27
瀏覽570
迴響0
推薦1
引用0

對於小型出版社來講,在競爭激烈的出版業立足並非易事。除了有雄心壯志之外,小型出版社的經營者必須學會迴避和大型出版集團的直接競爭,在夾縫中求得生存空間。無論是經營模式,還是圖書的選擇,獨闢蹊徑開拓新空間,憑特色吸引小眾讀者,才是小型出版社經營的成功之道。
波莫納(Pomona)圖書公司是位於約克郡的一家小型出版社。公司負責人馬克‧霍迪桑表示,經營小型出版社最大的樂趣在於,他能夠享受「一本書從最初的書稿到出版上市的過程」。霍迪桑對未來充滿信心:「我並不滿足於一本書只賣出500本,我希望能賣出2萬本,甚至更多。」和那些大型出版集團相比,小型出版社也許並沒有那麼大的批發送貨量, 但是,它們卻希望把每一本書都送到每一個需要它的讀者手中。儘管規模有限,但波莫納圖書公司並沒有因此降低圖書的品質。霍迪桑說:「我們不會經由便宜的紙張或者粗糙的封面設計來節省成本。以前,我特別喜歡買企鵝集團出版的圖書,是它們的忠實讀者。我希望也能建立一個波莫納的忠實讀者群,讓他們喜歡我們出版的每一本圖書。」
目前,波莫納圖書公司再版許多經典暢銷書,如巴里‧赫因的《注視與微笑》、克蘭西‧辛格諾的系列作品,以及亨特‧大衛關於足球的圖書。霍迪桑表示,目前,他們正準備推出湯姆‧帕米爾的作品《姍姍來遲》(Long Overdue),這本書主要介紹世界各地的圖書館。作者講述了他在英國、美國等各大圖書館的經歷和體驗。霍迪桑認為這本書極有可能成為新一季的暢銷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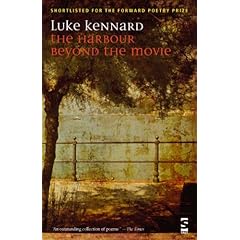
一些小型出版社為了盈利,還出版圖書之外的其他產品,Caseroom出版社便是代表之一。除了出版傳統的圖書之外,Caseroom還出版紀念冊和藝術畫冊。它曾出版過一本名為《一切向北》(All Points North)的紀念冊。這本紀念冊是蘇格蘭詩歌圖書館為了紀念一次和其他國家的成功合作而推出的,當時,蘇格蘭詩歌圖書館的合作夥伴來自芬蘭、冰島、愛沙尼亞、拉脫維亞、挪威等國。而這本紀念冊主要收錄了這些國家的詩歌,均用各國母語寫成。儘管大多數讀者都看不懂這些詩歌,但是對於一些業界人士來說,這樣的紀念冊頗具收藏價值。



面向明天的經營戰略
文 / 彼得‧杜拉克
如今,最有可能發生的假定是獨特事件,它會徹底地改變結構。
獨特事件無法「規劃」。然而,它們是可以預見的,或者更確切地說,你可以準備利用它們。你可以準備面向明天的戰略,來預見哪些領域裡可能出現最重大的變革,來使企業或公共服務機構能夠利用意料之外和無法預見的事件。規劃試圖根據今天的趨勢來優化明天,而戰略旨在利用明天的新機會。
任何組織都需要在戰略上思考它們在做什麼、應該在做什麼。它們需要想清楚客戶為了什麼掏錢給它們。什麼是「我們」為客戶創造的「價值」?這個應該得到強調的問題,對非營利的公共服務機構(不管是醫院還是大學,是貿易協會還是紅十字會)就像對企業一樣重要。每一個組織都需要想清楚自身的優點是什麼。這些優點適合於其特定業務嗎?夠用嗎?是被用在它們能夠產生成果的地方了嗎?在當前以及今後的幾年裡,適合於這一特定業務的「市場」到底是什麼?
通常,企業認為以「中庸」為目標的戰略最舒服、風險最低而且足夠有利可圖──非營利的公共服務機構甚至更是如此。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在很多的市場中,你只有處在兩個極端才能成功:要麼是作為少數的市場領導者之一,可以設定標準;要麼是作為一個專家,雖然只能提供範圍很窄的產品或服務,但卻在知識、服務和適應特定需求方面具有突出的優勢,因而能夠獨樹一幟。處在中間的位置幾乎都不理想甚至無法生存。
就在過去的幾年裡,憑著「巨大的銷量和市場滲透本身就格外有利可圖」的理論,波士頓諮詢集團(Boston Consulting Group)已經引起了大眾的廣泛注意。這並不完全符合事實。真正有利可圖的,要麼是在一個廣泛市場中成為領導者,要麼是成為搶先佔據一個狹窄的「利基市場」的專家。「市場領導地位」的含義不是銷量的問題,而是行業或市場結構的問題,會因市場的不同而變化很大。
在極少數的世界性汽車企業中,每一家實質上都涵蓋了整個業務範圍。如果你們是其中的一家,那麼你們就能夠在全球的汽車行業中生存。但如果你們在美國是老三,那麼你們就不能再生存下 了,就像克萊斯勒曾經嘗試過的那樣──儘管克萊斯勒當時也有巨大的銷量。然而,成為這個市場中的一個專家,佔據某個特定的「利基市場」來生產特定的產品,比如說吉普車或勞斯萊斯,這不僅是可行的,而且的確是有利可圖的。克萊斯勒打算保持的那種中間位置,今後將再也不能站得住腳了。那些只想在區域市場中成為領導者的企業,正日益被排擠到市場的邊緣。
圖書出版領域同樣也非常不同。圖書出版不是一個「世界市場」的業務,即使這僅僅是因為語言障礙。儘管因為出版社需要有可用的發行系統,所以規模太小可能會導致非常不利的地位,但是規模或銷量並不能帶來很高的額外回報。圖書出版要依靠編輯與若干作者的私交,然而沒有哪一位編輯能同時與非常多的作者打交道。這給圖書出版限定了一個最小經濟規模,但是並沒有給大型的出版社帶來多大的優勢。超過了最小規模之後,大型的出版社甚至可能非常不利,因為較大的規模可能會損害出版社對其首要客戶即作者的吸引力。但是在出版行業裡也有「專家」,也就是那些推出了大量學術專著的出版社。它們出版的每一本書都明確地面向世界範圍內的專業讀者,印量只有幾百本,當然發行支出也最低──例如,德國的史普林格(Springer)、荷蘭的愛思維爾(Elsevier)和美國的西景(Westview)就都是這樣的出版社。
公共服務機構可能同樣會發現它們也面臨著新的規模規範。例如在美國,作為「專家」的小型教派學院已經在最近這10年裡表現得非常有優勢。它們可以成功地把自身限定於狹窄的課程範圍,可以把自身的資源集中於8-10門學科,可以在這些學科的範圍內提供小學院的優勢,給學生們一種「在家」的感覺。學生們和全體教師都互相認識;他們給人一種紀律嚴明的感覺,他們中間洋溢著強烈的集體精神,以及致力於宗教、道德和學術的基本原則的獻身精神。在規模尺度的另一端是非常巨大並且正在穩定成長的最小規模──如今,對傳統的本科院校來說,這個最小規模可能保持在大約2,500名學生。因此,像奧伯林(Oberlin)、波莫納(Pomona)和卡爾頓(Carleton)等一些典型的「優秀」本科院校,它們是否真的能夠繼續生存下去就越來越值得懷疑了。對於這類院校來說,因為它們無法像小型的教派學院那樣選擇非常狹窄的課程範圍,所以龐大的規模加上進入研究生院校的途徑可能就成了生存的前提(作為進入研究生院校的途徑,它們讓畢業生有機會在語言、數學、表演藝術、形象藝術和科學等領域裡進行更集中、更深入的學習和研究)。但是,在美國的高等教育中可能也存在一個最佳規模的上限。如果學生人數超過8,000-10,000人,規模經濟就會變得越來越不經濟。一般管理費用要比學生註冊人數成長得快,至於說比收入那就更快了。換句話說,在美國的高等教育結構中,「市場領導地位」是一個品質概念,數量則主要是最小規模和最佳規模方面的限制條件。
同樣的原則也適用於醫院。如今,美國醫院的最小經濟規模可能是大約200張床位。但是,在醫院領域裡也有一個最佳規模的上限,大約是800張床位──如果超過這個上限,一家醫院就只會變得更昂貴而不是更有效。
因此,「行業領導地位」是品質以及向優勢領域集中的問題,而不僅僅是規模的問題。正如教派學院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樣,對於佔據著一個「利基市場」的真正的「專家」來說,幾乎每一個領域裡都會有其生存的空間。
在製藥行業裡,有一家典型的「專家」企業一直系統地尋找那些特殊的產品──它們沒有太多的科技成份,但卻能讓這家小企業在一個小得令大企業看不上眼的領域裡佔據領導地位。這家企業的第一個產品是一種酶,它能夠略微地加快眼科醫生施行白內障手術的速度,並且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手術失敗的風險。該企業的科學貢獻非常小──無非就是延長了這種酶的保存期限。但是這種產品一經上市,市場中就再也沒有其他競爭對手的立足之地了。假如已經有大型的製藥企業進入這一市場,那該企業所能做的也只有拚命降價了。
無論是市場領導地位,還是我們所謂的「收費站」專業化,兩種戰略都能成功。沒有立足之地的是處在中間的戰略。試圖把兩者結合起來的戰略幾乎肯定不會達到目的。這兩個領域要求不同的行為,提供不同的回報,適合於不同的脾性。然而,把很多單獨的小生境結合在一家企業裡,讓其中的每一個都針對特定的市場,面向特定的專業化,預先佔據各自獨立的「收費站」位置,這卻是可行的,而且往往是有利的。
任何一家企業都需要了解自身的優點並據此制定自己的戰略。我們做什麼做得好?我們在哪些領域裡表現出色?大多數的企業和公共服務機構都認為,在每一個領域裡都成為「領導者」是可能的。但是組織的優點總是特定的、獨特的。一家企業只會因優點而得到回報,不會因缺點而讓客戶掏腰包。因此,企業首先要問的問題就是:「我們的特定優點是什麼?」然後要問的是:「它們是合適的優點嗎?它們適合於明天的機會嗎?還是它們只適合於昨天的那些機會?是否在我們利用這些優點的領域裡已經不再有機會,或者從來就沒有過?最終,我們必須要獲得哪些更多的優點?要想利用那些由人口特徵、知識和科技以及世界經濟的變化所導致的變革、機會和環境的動盪,我們必須補充哪些執行能力?」
在認真思考自身戰略的過程中,一家企業需要同時研究專一化和多樣化。我們知道什麼樣的組織可以創造出成果。從長遠來看最賺錢的企業,是那些找到了恰當產品的單一產品企業,也就是像IBM或通用汽車那樣的企業。從長遠來看最不賺錢的企業,是那些選擇了不當產品的單一產品企業──典型的例子就是發達國家中的傳統鋼鐵行業。然而,那些圍繞著統一性尤其是市場統一性的核心進行多樣化經營的企業,會像選對了產品的單一產品企業一樣賺錢和成功。在美國,強生公司(Johnson & Johnson)就是多樣化經營的典型──他們的業務範圍非常廣泛,從生產標準的日用品紗布,到提供高級的節育產品。但是,所有這些產品都是衛生保健消費品,都透過相同的分銷管道進入相同的市場。
從長遠來看,集團企業,也就是那些無論在市場還是在科技方面都沒有一個統一核心的多樣化企業,會像那些選錯了產品的單一產品企業一樣不賺錢。做一個「聰明的投資者」,在數量非常有限的不同業務領域裡都佔據支配地位,這當然是可能的,而且也肯定是有利可圖的。一個這樣的例子就是英國培生集團(English Pearson Group),其旗下有很多控股公司:多家報紙和雜誌出版社、一家大型商業銀行、一家建築公司等。德國的佛里克集團(Flick)也是一個這樣的例子,其在德國和美國的控股企業共有6家;英國的湯瑪斯泰靈集團(Thomas Tilling)或者匹茲堡的美洲梅隆集團(American Mellons)也都是這種情況。這些投資者要集中於少數的企業,以便能夠照顧到其中的每一家。他們要在這些企業裡擁有足夠多的股份,以便獲得否決權。他們要致力於自己的投資。他們要參與重大決策,要確保他們的企業全面而徹底地思考他們的政策、目標和戰略。他們要確保這些企業擁有第一流的管理。但是,這些企業並不是由他們來管理,而是由自主的職業經理人來管理。
但是,如果一個「集團企業」僅僅是一個企業集合,處在一個管理層的領導之下,有著很多類型非常不同的企業,但卻沒有一個統一性的核心,那麼就不能指望其會長期得到出色的成果和績效,尤其是在動盪時期。
困難是可以預見的,或遲或早而已。對企業的熟悉和理解也非常重要;要實現這種熟悉和理解,不僅要靠財務分析,而且還需要一個人的直覺。這種直覺的形成要靠他在一個相對狹窄的領域內的經驗,靠某個行業、某種科技或某個市場的定性特徵對他的長期薰陶。
然而,每一種「恰當」產品都遲早會變成「不當」產品。每一種產品都遲早會變成一種「日用品」。每一種產品都會變老並最終被淘汰。沒有哪一種產品能在三、四十年後仍是一種「恰當的」產品。很顯然,IBM就處在其產品正漸漸變成「不當」產品的關頭。甚至連美國電話公司(American Telephone Company)也正處在這樣的時刻,儘管其一直精明地管理著自身的壟斷地位。因此,一家企業必須多樣化。
因此,一個關鍵性的戰略決定就是何時以及怎樣多樣化。當一種產品或產品線還是恰當產品的時候,過早多樣化的決定可能會危及一家企業的領導地位。但是,太遲了又會危及企業的生存。
你可能會有興趣的文章:



